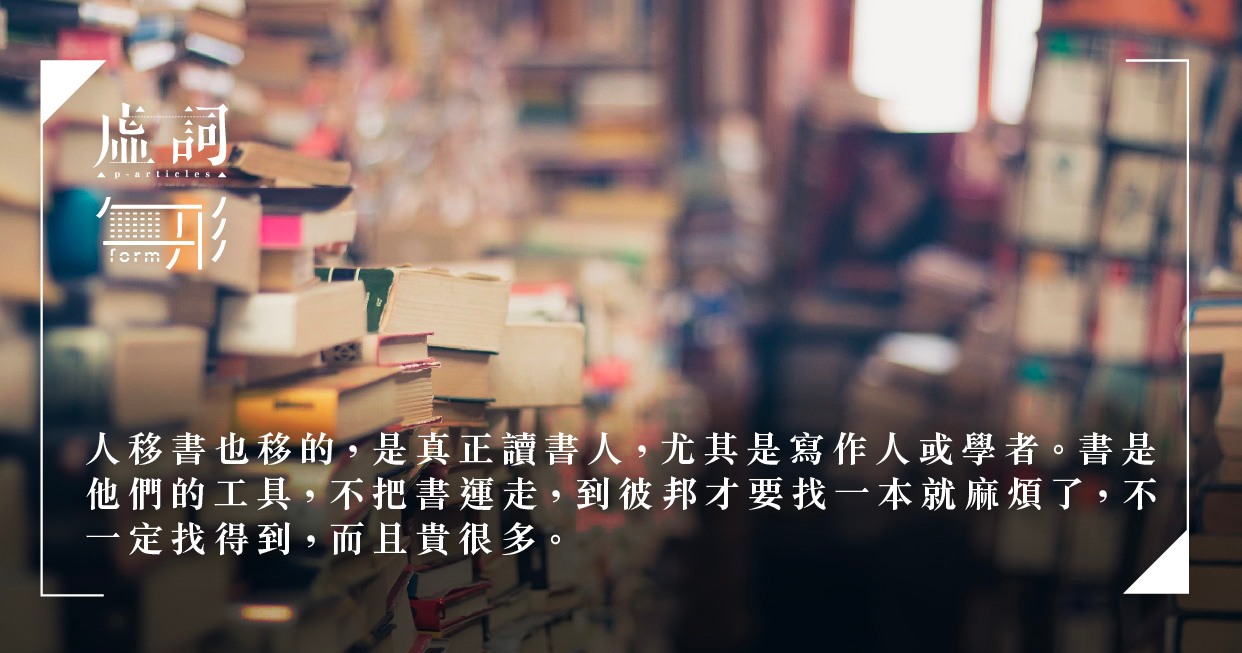【無形・書來也書去】人移,書移不移
一位視藏書為命根的朋友移民加拿大,臨上機前卻將藏書賣了給我,命根子都不要了。他在葵涌租工廠大廈來放書,我書店的倉位已爆滿,只好繼續租用他的藏書庫存放那批用數十年心血找來的寶貝。
按理加拿大的住宅比香港寛敞,他住的是獨立屋,放得下那批舊書,這比起在香港要找一本書,就要跑一趟工廠大廈好得多,但他寧可用空間弄一個家庭影院,也要忘情割愛,放棄萬計藏書。
他解釋說:數十年來,開書店的人是瘋子,買舊書的是傻子。文化大革命焚書,他就拿港幣去實用、神州、新亞諸店,和用美金英磅買書的西方圖書館角力。
現在西方圖書館不來香港,直接上大陸買書了,傻子們只好內鬥,一本董橋翻譯的《再見延安》,搶到萬多近二萬港元。不傻的人很好奇,想知道此書的內容。蘇賡哲卻告訴她,應該好奇的不是書的內容,而是書的價錢。於是這位將要移民的朋友恍然大悟,數十年來收書數萬冊,其實不是為了書的內容,不是為一個「讀」字,而是為個「搶」字。半生的樂趣,不是讀書,而是搶買書。甚麼移了民無事做,最好是讀書,其實是自己騙自己。最過癮是有白雪仙、霍英東這些校友的「敦梅學校」校長莫儉溥去世,他從灣仔「三益書店」搶書,搶到井欄樹三益的貨倉。好了,現在要移民加拿大,不論溫哥華、多倫多,甚至滿地可,都沒有香港這類「搶書樂」的舊書店,我在多倫多的「懷鄉書房」,硬撐了十五年,就是沒有搶書客而關門的。所以,將藏書運去加拿大,沒有甚麼意義。以前,傻子們提起某聽聞過而沒機會一睹的書,他可以急急跑去工廠大廈將書找出來,貼在臉書上大喝一聲「老子有」。去了加拿大,就沒有這種以書驕人的樂趣了。因此人移書不移,完全可以理解。
當然,這是比較極端的書迷。他迷的不是書的內容,而是搶購的氛圍。另一些「人移書不移」的例子,則是我經常說的,買書不是為了讀書,而是為了「逛書店」這個工餘的療癒節目,他們逛書店的心境和女士們逛百貨公司時裝店沒有分別,目的就在逛。就像在深圳書城開過舊書店「尚書吧」的才女掃紅所說,逛過了,坐在西洋菜街「大家樂」喝杯凍咖啡,翻翻逛來的戰利品,真是人間一樂。但移民異邦,就要和這樂趣說再見了,那就不如棄之於港算了。
人移書也移的,是真正讀書人,尤其是寫作人或學者。書是他們的工具,不把書運走,到彼邦才要找一本就麻煩了,不一定找得到,而且貴很多。
最近,移民英國而又將藏書一起運走的楊穎宇博士,辦了個私人藏書及資料的「香海書樓」。這相信在各國香港移民社區中都是首創。讓書在異地發光發熱,是功德事業。我以前在多倫多的書店,擺明是一盤生意,還是長期有義工幫手,「香海書樓」應該更不愁人手。一般西方大學的圖書館都有中文書刊,而且比香港的大學圖書館大方,非學生也可共享所藏,但總不如楊博士的書樓富於港味。
今日,移民不論移不移書,環境總是和平安定的。所以我很佩服在1949年世變中,竟有不少人在戰火紛飛中,將藏書從大陸運到台灣去。我認識台北文海出版社的李老板,他是「十萬青年十萬軍」時入伍的。當年托著一桿槍隨大隊去台灣,最記得大雨中渾身盡濕的宋美齡在基隆碼頭給了他一個麵包。復員後他經營出版社,專門翻印古舊書,原板多來自大難中猶挾書渡海的人,事業上了高峰,我未來加拿大前,他隨便一部近代史叢書就賣三數十萬港元。倘若戰亂來時,大家都人逃書不逃,就沒有那麼多書可翻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