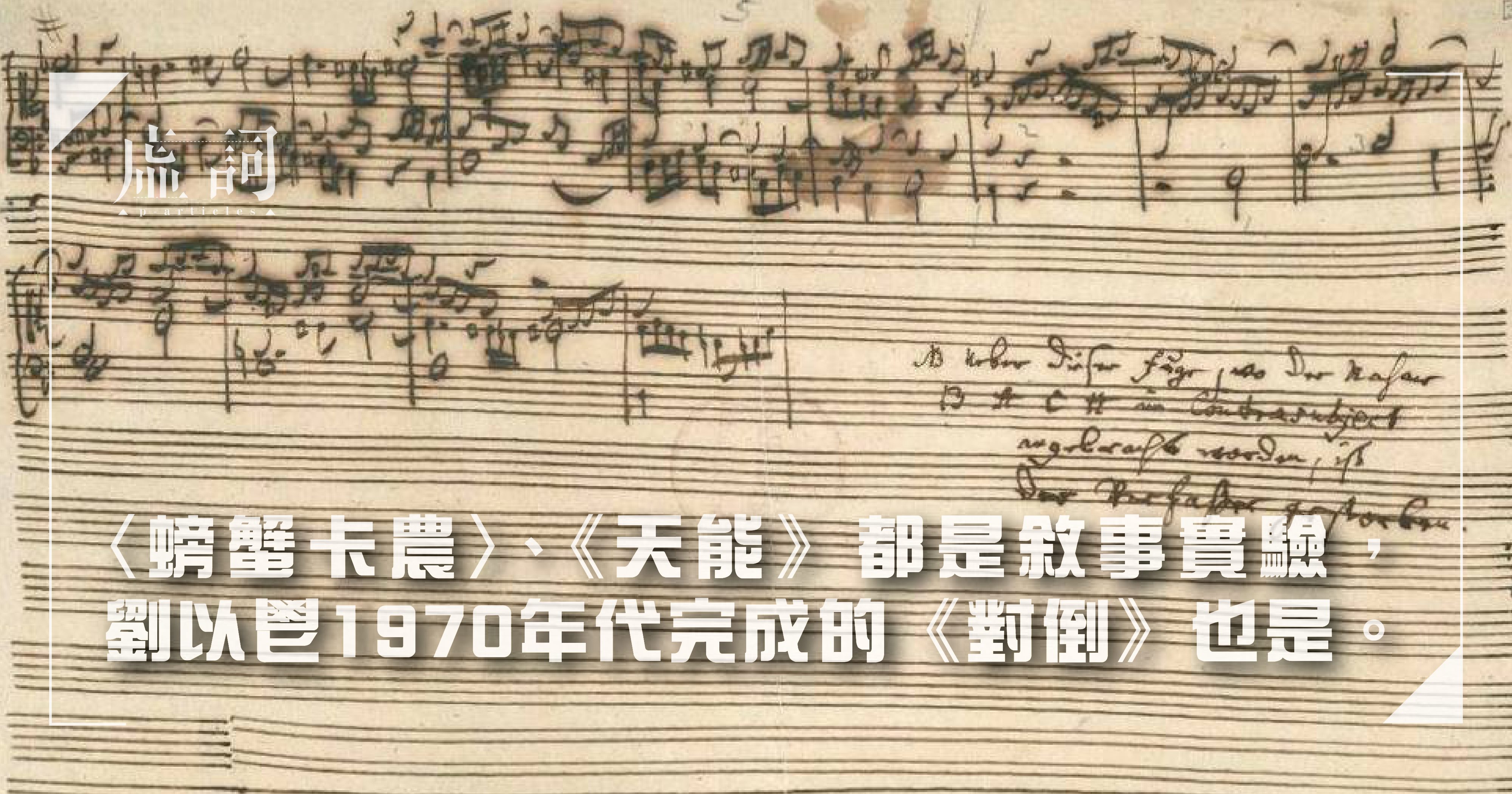豆芽字、爬格子、賦格與詩篇
下著綿綿細雨的星期六下午,收到夏宇詩集《背脊之軸》,翻開那些文字印痕,一筆一畫光影迷離,光線與觸感的意義,被這本詩集無限放大。讀到其中一頁,「在一團亂織物中/奮力拉出/一個莫比斯環」,感覺我們迴旋複沓的日子就這樣被詩人說破了——一種誤讀。
莫比斯環。克里斯托弗·諾蘭《Tenet 天能》。巴哈〈螃蟹卡農〉。
如果你說巴哈是穿越時空回到巴洛克時代的AI,我會願意相信,他是那麼不可思議,他在他那孤獨的音樂實驗室裡設計了那麼多那麼奇妙的程序,探索各種排列組合,留給後世一部部「賦格的藝術」般聖經等級的作品。〈螃蟹卡農〉不過是其中一個小小創意,五線譜子雙軌運行,它們是一對鏡像顛倒的旋律,雙聲部同時演奏,琴師的手為螃蟹,一左一右,琴鍵兩端橫向行進,相逢,交錯,離去。諾蘭在《天能》裡繼續玩時空概念,多拐了幾個彎,基礎仍是鏡像對倒,可惜我們都是視覺動物,輕易就被電影的線性敘事搞得暈頭轉向,在音樂,正反敘事雙軌並行,交織和弦,提供抽象的解答。
螃蟹卡農式,有點像回文修辭,一種文字遊戲,回文詩,比如王安石〈碧蕪〉:「碧蕪平野曠,黃菊晚村深;客倦留甘飲,身閑累苦吟。」反過來就是「吟苦累閑身,飲甘留倦客;深村晚菊黃,曠野平蕪碧。」
又比如戴望舒〈煩憂〉,選擇回句不回文,直敘和倒敘一氣呵成,「你」就是「我的煩憂」,但「我不敢說出你的名字」,詩句迴旋時疊加,鑄成核心,是起點也是終點,煩憂啊煩憂,滾雪球,無限輾壓。
電影裡,諾蘭借助科幻,憑空設計出一系列沒來由的旋轉門,不作太多解釋,感覺比哆啦A夢還偷懶。當然諾蘭的實驗還是必要的,他在乎的是影視敘事的創意,觀眾千萬不要把《天能》當成硬科幻來剝繭抽絲。
〈螃蟹卡農〉、《天能》都是敘事實驗,劉以鬯1970年代完成的《對倒》也是。劉以鬯在1972年投標買下一對「慈壽九分銀對倒舊票」。那是一對為紀念慈禧太后大壽發行但不小心印刷失誤形成對倒的珍貴郵票。某天搭電車經過香港彌敦道,劉以鬯靈光一閃,於是有了這個關於兩個南轅北轍之人在旺角電影院交錯的故事。中年男人淳于白在彌敦道一頭,年輕少女翁亞幸在彌敦道另一頭,一個是想念老上海的男人,一個是香港國際大都會成長的少女,一個活在過去,一個活在未來,機緣巧合,他們在電影院裡坐到一起,看了同一齣戲,可是這對陌生人,完全沒有擦出火花,零交流,甚至可能還多了一層不屑,冷落,疏離,完完全全反高潮,彷彿緣分的印刷機出了錯,離開電影院,漸行漸遠,又拉出更大更大的距離。
現實不就如此?劉以鬯的深刻,到了今天還可以共鳴。至於《天能》,或許未來大家不會記得男主角華盛頓的迷茫,不會記得這是諾蘭首次以黑人為主角的電影,而是著迷於俊美白人男二,那明知會犧牲卻仍忠誠地執行任務和使命的荊軻式浪漫。
不喜歡《天能》,一副宿命論的嘴臉。
雖然小說裡主人翁毫無緣分可言,但《對倒》卻激發王家衛拍出《花樣年華》,現實中何其美好的相遇。只是漸漸,梁朝偉和張曼玉就霸佔了我們的惆悵,淳于白同翁亞幸就更顯陌生了,我們這個視覺主導的世界。
我喜歡香港文學,從小就從金庸武俠吸收養分,當然還有香港電影和流行音樂,那自由不羈,華美與世俗並列,高雅與無厘頭雜糅,多少讓我思考不再那麼單一。我曾經有點原教旨主義,認為《西遊記》就應該是《西遊記》,改編影視也應該是六小齡童的版本,逢年過節電視台喜歡播一點周星馳,每到《大話西游》我就躲進房裡。長大一些才明白那無厘頭,除了笑料,還有幽深之處,像是靈與肉的問題,大聖回到凡間,至尊寶無從超脫,對著豬八戒的肉體愛紫霞仙子,每見一次就想吐。《大話西游》也玩時光倒流,拿著月光寶盒喊「波羅波羅蜜」,重置時光,要阻止悲劇,用力過猛的結果就回到更早以前。一切合情合理,因為我們深知那是怪力亂神之作,而不需要假扮科學,假借科幻的軀體還魂。
總覺得那個時代,香港文學與文化氛圍,有一點不甘寂寞的因子,這種浮躁卻擊中我的紅心,我想,很多時候創作,一開始都有點不甘寂寞。
談到巴哈,伊藤潤二有篇恐怖漫畫〈中古唱片〉就跟巴哈有關。創作期間,伊藤潤二住在名古屋,偶爾會去一家靠近車站的中古唱片行,他在店裡無意間找到一張純人聲合唱團The Swingle Singers的唱片。這支阿卡貝拉合唱團以模仿器樂作品聞名,唱過不少巴哈作品,加以爵士調味,非常迷人。我猜伊藤潤二聽到的是他們六七十年代錄製的專輯。以人聲模仿樂器,除了娛樂性,還有人聲獨特的柔軟,給人不同於器樂的感覺。在伊藤潤二的模仿與再現裡,人聲之中有鬼魅,也許是因為老唱片的音質比較舊了,所以在他詮釋下,巴哈對音樂的瘋狂實驗,衍生出一個關於沒來由的,關於人性貪欲的恐怖故事。怎麼會這樣?或許換個角度,對任何事物的著迷,到了某個程度,就會展現其恐怖的本質吧?也許伊藤潤二想說的是這一層道理。
模仿與再現,恰恰就是賦格的核心。
文人騷客也經常借賦格來做文章,喜歡陳育虹寫的〈蜻蜓賦格曲〉:「這密接疊置的技巧啊/世界縮小又擴大」,好像真的都如此,不是嗎?重讀金庸《笑傲江湖》的時候,暗忖裡頭的人物設計和劇情進展,也似沿著賦格的形式前進。那些表裡不一的人,一個個出現,顛覆1960年代華人世界的正義觀,金庸逆向思考每個人物,「君子劍」岳不群最最虛偽,令狐沖做大師兄的卻放蕩不羈,後來還成了尼姑的掌門,老頭子給瀕死的女兒取名字老不死,不戒和尚出家只因為他愛上了尼姑,認為只有和尚配得上尼姑,偏執得要命,人人聞之色變的東方不敗,出場畫面竟是躲在深閨裡刺繡,當然這裡有太多當年華人世界落後的性別觀念,卻無阻後來徐克逆向思考請林青霞飾演東方不敗,從此改變了這魔教教主的角色意涵。這部小說好看,或許正因為裡頭暗藏賦格式,潛移默化,給讀者閱讀的愉悅。
我的人生有一大半在合唱團裡度過,16歲開始,直到31歲工作因素必須暫時離開團體生活,但對合唱的喜愛卻遠未終結。我一直以為我距離文學很遠。中學畢業後才發現學生時代唱過的一些歌曲,那些陳徽崇老師的作品,其實是老師在1980年代拉著學生為馬來西亞詩人詩作譜曲的實驗。我們唱著潘雨桐〈星夜行程〉「風無定向」的時候,完全不懂這名來自東馬的詩人寫詩時的心境,也沒去深究李蒼〈風中口佔〉的「口佔」到底什麼意思,更別說何啟良那首用了許多佛典的〈刻背〉。我們像機器人一樣背誦詩詞,拼命唱準音打對拍子,演唱會結束,接受擠滿大禮堂觀眾捎來的例行掌聲,很慶幸完成了演出。這些後知後覺,有時候不知道該怪自己年輕時不夠努力沒有好奇心,還是怪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總覺有點遺憾。
詩與歌原是那麼親近,就在身旁,我們竟都錯過了。
練唱的時候,翻開合唱譜子,那些作曲家在開頭標記的關於速度的義大利語術語,總讓我迷醉:Largo(廣板)、Lento(慢板)、Adagio(柔板)、Andante(行板)、Moderato(中板)、Allegro(快板),都是O嘴的氣音結束,特別催情,好適合挪用到詩裡,像瘂弦的〈如歌的行板〉,誰不愛呢?
匆匆忙忙的人生啊,「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有這麼多那麼多的「必要」,但詩的最後卻告訴你「世界老這樣總這樣;——/觀音在遠遠的山上/罌粟在罌粟的田裡」,一個「——」打破了行板的語速,原來有那麼一個悠遠的東西,在「必要」之外,處於寧靜致遠的狀態,而這個狀態,必須在前面那些行色匆匆的「必要」之映襯之下才能成立。
世界亦也一快一慢雙軌並行,賦格式「增值卡農」,把主題放慢一倍,上下鏡像對倒,彷彿水中倒影。
The Swingle Singers借人聲演繹器樂,你是小提琴,我是倍低音,創造力無窮無盡,可以模仿自然生態蟲鳴獸吼鳥語猿啼,也可以假冒爵士鼓電吉他⋯⋯不過人聲卻有個致命的弱點:控制聲帶的肌肉並非隨心所欲之機制,半自主的肌群,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的。加之不同地方語言文化,決定了人的發聲習慣,要找到最圓潤通透像初生嬰兒那樣的赤子之聲,太困難了。每次上聲樂課就像在學習減法,要把我們的壞習慣消除,要找回初音。新馬華人扁嘴鴨的腔調,到了聲樂課,就更吃虧了。
這些經驗好像也可以放在寫作上,怎樣才算得上是理想的「聲音」?如果美聲/標準中文是一種指標,民謠唱腔/地方語言是一種指標,兩者可否兼容?有時候會問自己,馬來西亞華人應該寫怎樣的文字?像假牙那樣直白而風趣嗎?或是張貴興那華麗綿密源源不絕的原始動能?如果有一扇光譜,我的聲音應該處在哪裡?
這些我都沒有答案,只能繼續嘗試。
愛搞特立獨行的韓寒在2010年創刊《獨唱團》,反擊老共式集體主義,雖然只做了一期,卻達到他所要的宣傳效果,韓寒不愧是最懂行銷的作家。《獨唱團》收錄詩人/獨立歌手周雲蓬一篇散文,寫他一個盲人坐火車從沈陽到北京,從北京到雲南,四處賣唱流浪的日子。途中他邂逅一個姑娘,有點曖昧,最後無疾而終,言語間周雲蓬似乎有點後悔,好像當時如果更勇敢一點,兩人的緣分就不僅於此。
散文尾聲,周雲蓬提到海子。海子的〈九月〉後來被周雲蓬唱紅了,經那些電視選秀大賽歌者浮誇演繹,不少人誤以為作曲人就是周雲蓬本身,但其實原曲是張慧生寫的。張慧生跟海子一樣,年紀輕輕就自殺了,周雲蓬唱著他們的歌,感覺某些精神就這樣被保留下來。
「目擊眾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遠在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苦悶的日子,誰不渴望遼遠?
《笑傲江湖》在小說裡原是一部琴簫重奏曲的名字,衡山派劉正風與魔教長老曲洋超越派系鬥爭的純藝術與友情結晶,兩人臨死前把琴譜交託給令狐沖,一度被誤以為是暗藏絕密神功的《辟邪劍譜》,最後令狐沖和任盈盈這對神仙眷侶解決了江湖危機,金盆洗手,帶著曲譜,隱逸於琴簫和聲之中,也算是完成了劉正風和曲洋的心願吧。這大概也可以描述為正與邪對倒交錯的一個案例吧?
總覺得,能夠有一些什麼被留下來,是很動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