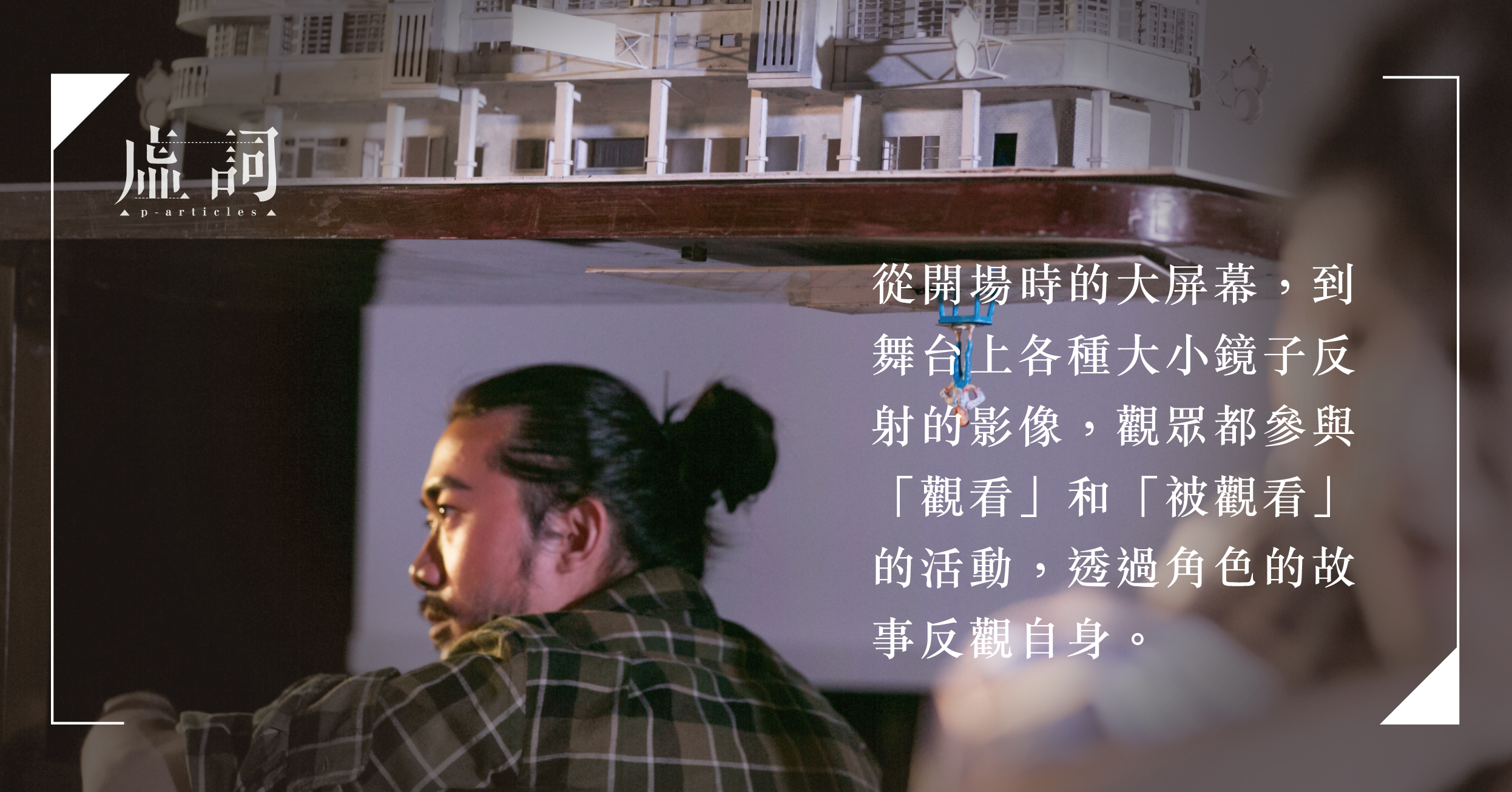「對倒」眼光看我城——淺評《對倒.時光》
「對倒」是集郵術語,指兩個相連而上下顛倒的郵票,劉以鬯先生以「對倒」作為小說形式,以雙線結構,交錯地敍述中年男子淳于白和少女亞杏的故事,呈現出七十年代香港的城市景觀;於九十年代,董啟章先生寫出〈對倒《對倒》〉,以一男一女的故事與《對倒》進行對話,二十年後,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創作的《對倒.時光》,結合了多個劉以鬯的小說文本與董啟章〈對倒《對倒》〉,與劉以鬯及董啟章的文本產生多重對話的關係。作為前進進二十周年的新劇目,《對倒.時光》以「我們的時間」為主題,從本土角度出發,透過四個人物的「對倒」,思考空間與時間之間的關係,從而對當下的香港及歷史進行詰問。
對倒與鏡像︰虛實間看穿荒誕現實
劉以鬯《對倒》中的淳于白與亞杏,一個外來者,一個本地人;一個邁向衰老之路,一個踏入花樣年華;一個回望過去,一個展望將來,兩相對照下,呈現出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的種種狀態,也折射出當時香港人對於身份、命運、未來的思考或想像。《對倒.時光》一劇不只聚焦淳于白和亞杏的「對倒」,在二人之外,加上黃思進和藍丹丹的故事線,這兩個年輕人,同樣是本地人和外來者的組合,但土生土長的黃思進因租金的關係搬到深圳居住,而藍丹丹則是想留在香港發展的「港漂」,此一男一女,跟七十年代的淳于白與亞杏,在時空上是「對倒」的關係,也是彼此的「鏡像」。
舞台上的多個鏡子,令這些錯綜複雜的「鏡像」關係視像化地呈現出來——淳于白與藍丹丹(外來者)、亞杏與黃思進(本地人)、淳于白與黃思進(男性)、亞杏與藍丹丹(女性),各個角色之間的對照相互交錯,產生出年代之間對於自我身份認同、社會價值、性別、命運等種種對話,在角色間的相互觀照下,亦能作自我觀照,帶領觀眾進入多重「對倒」與「鏡像」的空間。在此,觀眾也不能置身事外,從開場時的大屏幕,到舞台上各種大小鏡子反射的影像,觀眾都參與「觀看」和「被觀看」的活動,透過角色的故事反觀自身。演員與觀眾之間,虛實相交,現實生活下的香港社會,不也荒誕得像戲劇嗎?

亞杏(前)與藍丹丹對倒出不同時代下的女性面貌。
擬真與真實︰無法複製過去的矛盾
劇中多次出現「immersive」一字,這個字解作「身歷其境」。黃思進的前老闆書店店主想要開發「immersive街頭小劇場」的VR(即Virtual Reality,解作「虛擬實境」)遊戲,讓玩者帶上VR裝置後,遊走於不同時空的香港街道中,一邊遊覽、一邊浮出相關文學作品的字句。面對環境隨時間變遷,店長想做一點事情,想要保存地方色彩和質感。因為失去,所以留戀,透過不同方法重現過去,無論是「immersive」的VR劇場還是舊香港模型,旨在模擬過去的真實場景,即使多逼真,終究只是「模擬」而已。就如街道模型,可隨時轉換放置地點,深圳或旺角,供人觀賞,但它們只是虛假的街景而已,無法複製過去的時空,VR亦然,這些「擬真」的事物,彷彿是「過去」的幻影,讓人觀賞或擁抱——這到底是積極還是消極的態度?對於黃思進,這已不重要了,他帶著傘運的創傷,曾經的「身歷其境」讓他離開旺角,輾轉到深圳生活,沒有固定的工作,撇開他人的眼光,這無疑是面對社會變遷的另一種取態。
時間與空間︰一切只是被壓縮的平面?
劇中的舊香港建築模型豈止是懷舊的工具?它比演員們更早出現在觀眾眼前,置於圓形的平台上,平台上的縱橫交錯坑紋勾劃出街道平面圖。序場開始時,四位演員以敍事者的角色,一邊擺弄模型、一邊抽離地講述角色的故事,此時,兩個時空的四個角色同時出現,在街道圖上——時空的重疊和交錯成了此戲劇的結構。
景物和人物模型不只讓舞台上的敍述層次更豐富,更重要的是能帶出導演對「時間」和「空間」的思考。模型展示的是過去的事物,舊香港建築、書報攤、馬標,還有淳于白想念的南洋菜餚。當淳于白一邊敍述回憶,一邊把手指般大小的食物模型拿出來時,回憶像袖珍模型般封存起來,但隨著生命的流轉,它們將會在時間的長河中佔了多少位置?那些「身歷其境」時空、過去的歷史事件,或許只是發展史上的一個小點,就如香港這個城市空間,其實只是錯綜複雜的街道平面圖——從高空俯瞰下。
我們應如何看待我們的城市,如何看待城市的變幻?微觀或宏觀,進入或抽離,《對倒.時光》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城市及歷史,或許會有新的發現,從而對未來有更多想像。

當淳于白一邊敍述回憶,一邊把手指般大小的食物模型拿出來時,回憶像袖珍模型般封存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