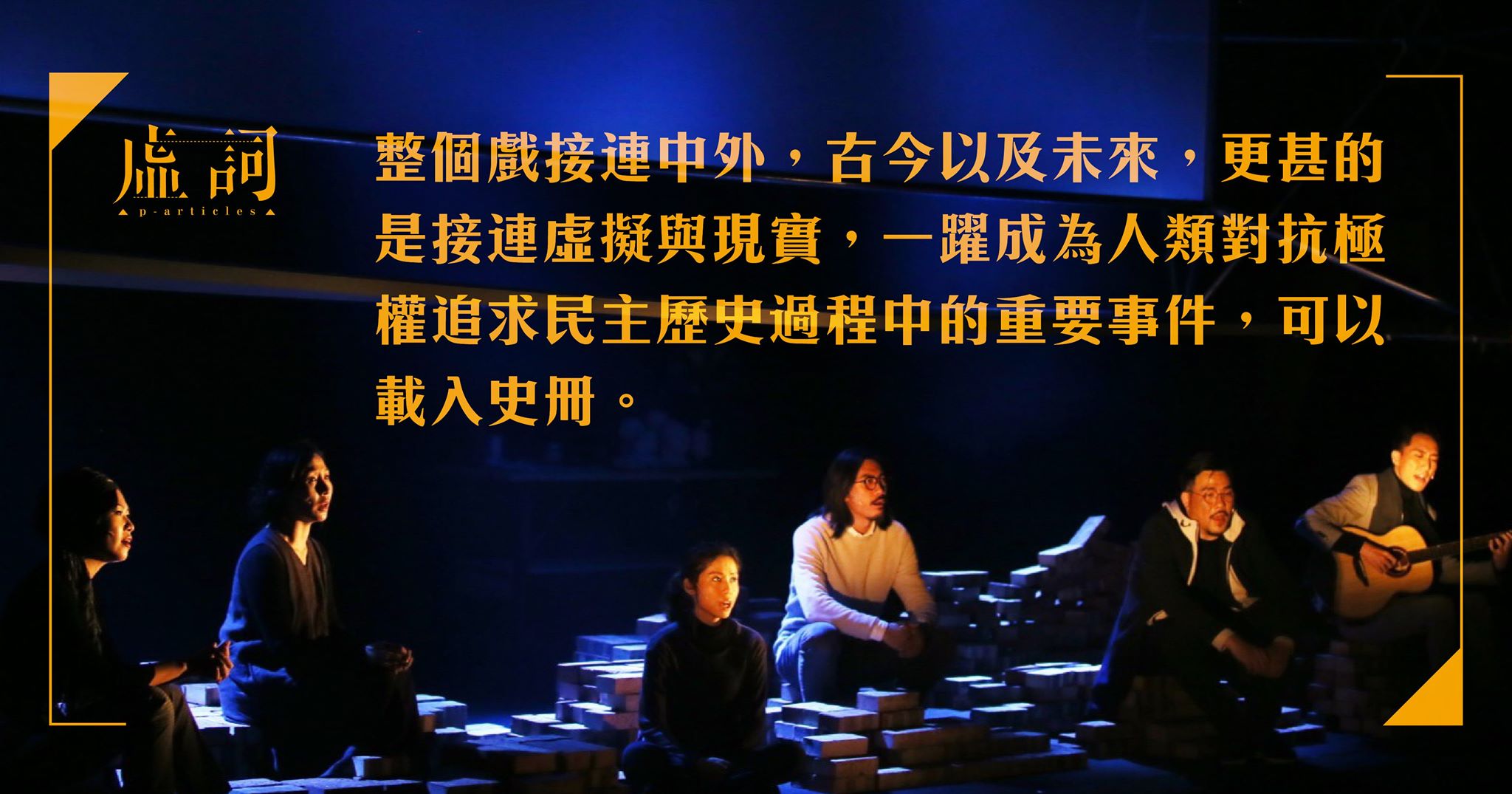回歸與搖滾:觀前進進《聽搖滾的北京猿人2021》
按:演出前遇到很久不見的陳曙曦導演,「怎麼很久沒見你寫東西了?」還順帶用一種責怪的語氣肯定了我的寫作能力。然後我便帶著一種我要寫劇評的心情進入劇場。甫一開場,我就知道,這戲,有得寫。但畢竟久不動筆,雖還未有宣稱遇到寫作瓶頸的資格,可懶惰確實讓筆頭生鏽。苦思之後,決定放棄苦思,不再組織經營,放筆蕩去,想到什麼寫什麼,並盜祖師奶奶張愛玲「解甲歸田式」筆法來遮羞。故以下全是隨手亂扔的盔甲碎片,讀者任意取讀,但如想窺得此戲真昧,還請禱告上蒼,向北祈求/抗爭(作者於2020年7月1日後將後一詞改為「請願」),讓此戲再再重演。
1. 頭盔
且讓我戴好頭盔,利申一番。文題「回歸與搖滾」,純粹是因為此戲上演的日期與香港回歸紀念日實在太近了,彷彿這場演出和這個日子有什麼關係似的。比如這兩個詞語搭配一些動詞實可組合成一些常見的關係模式,正面的比如「慶祝/紀念香港回歸二十三週年搖滾音樂會」;負面的比如「⋯⋯香港回歸二十三週年搖滾音樂會」(作者於2020年7月1日後刪去詞語若干)。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文不能為題目冠上這般關係明確的動詞,讀者可因應自己的喜好隨意想像。並且我看的場次在六月二十九日,一日之後國安法通過生效,而這個戲有一個宏大的歷史結構,這個結構的終點是2021年的「港猿革命」。現實與虛構本身就在這戲裡雜糅交錯,如今遇上這別有意義的時期,這個戲的演出本身便也充滿隱喻。但這個隱喻的作者不是編劇也不是導演,而是上帝。我不敢妄測神旨,只能留給讀者們發揮想像。因此事先聲明,本文不打算討論任何敏感議題,對任何敏感議題也沒有任何既定立場。本文想說的是,即便抽離眼下這個特殊時期,撇除任何意識形態的色彩,讓此戲處於真空的時空中,她也仍有很高的價值,最低限度,可說明香港本土劇場藝術水平極高。因此拙文如有幸與國安大人的貴目偶遇,還請大人放心,閱覽至此大可止目,安全至上是顛簸不破的真理。

2. 片甲一
儘管本文不打算討論敏感的議題,但看在眼下這個時局的份上,不得不說這齣戲的主題很敏感。開場便拉開了一條宏大的民主抗爭史的線索,血腥星期日、俄國革命、捷克革命、天鵝絨革命、八九天安門事件、一四年雨傘運動、一九年反送中運動、二一年港猿革命等,從過去到未來,從真實到虛擬。編劇甚至將二零二零年《聽搖滾的北京猿人》重演這一事件安插在這一條歷史線索中。導演更是推波助瀾,把此戲演出的年月日,時分秒精確的顯示在了舞台上的巨大螢幕上,時刻提醒著觀眾,此戲意義非凡,在座各位都是歷史的見證者,並且在開場與結尾都質問觀眾,離開劇場後,你們要去哪?(儘管演員的語氣並非質問,但全戲壓抑的氛圍,每個人物在各自的時代各自的處境中所做的掙扎與努力,都使得這個問題異常沉重,「你要去哪裡」,問的其實是,「你要站起來嗎?不願做奴隸的人民!」)彷彿此戲的上演本身引爆了(戲中的那場)二一年的「港猿革命」。這樣一來,整個戲接連中外,古今以及未來,更甚的是接連虛擬與現實,一躍成為人類對抗極權追求民主歷史過程中的重要事件,可以載入史冊(編劇已經主動將此戲塞入戲中的史冊了)。這樣的架構和視野是很不容易掌控的,要用什麼事件來連結古今中外這麼多線索?一不小心便會流於空洞,一大堆的主義與符號,不知所云;太過小心又會陷入歷史漩渦,囉囉唆唆又臭又長。因此不得不讚揚編劇胡境陽,能有這樣的視野本身已不簡單,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能富有創意的將這些看起來和戲名一樣「九唔搭八」的線索串連起來。又是遠古猿人、又是法國哲學家,又是美國雕塑家,還有來自俄國的演員的靈魂、香港的青年、北京的搖滾樂手,這一串看似散亂的人物,正是這個宏大歷史框架的具體支點,並且連那個無人扮演,只有雕塑的猿人Nelly也有動人的故事。

3. 片甲二
Nelly是一個只有十四歲的北京猿人,是雕塑家Lucile Swan的雕塑作品。Lucile在塑造這個作品時深入的探究了這個小北京猿人的故事。她發現,十四歲的Nelly是被他的同類殺死的。她無法接受自己所研究和雕塑的北京猿人竟會這樣殘殺同類,而幼小無辜的Nelly就死在了爭奪山洞的成年北京猿人手裡。這成了Lucile的夢魘,總是會在夢裏到了Nelly的山洞,眼看著猿人殺害了Nelly。這對Lucile而言幾乎如同一個母親目睹自己的女兒慘遭殺害,畢竟Nelly是她一手雕塑出來的。更可怕的是這個夢不斷重複,好像一個平行時空,Nelly在那裏不斷被殺害。Nelly的悲慘遭遇不是沒有寓意的,猿人是人類的祖先,這種貪婪的爭奪與殘忍的殺害如同基因一般根植在人類的本性之中。這正是全戲串連從古至今,由遠到近,各種血腥鎮壓事件的內在邏輯:極權的血腥暴力其來有自,遠從那殘殺14歲Nelly的北京猿人而來。但不要忘了,Nelly雖然死了,但她並非沒有反抗。Lucile對抗這個惡夢的其中一個辦法,也是想通過雕塑呈現Nelly的另一面,而非被死亡恐嚇籠罩的一面。她沒有明說這一面是怎麼樣的,但是我們可以想像,那絕對可以是面對壓迫與死亡的怒吼。這不也同樣是人類深入血液的基因嗎?劇中在香港挖掘出的北京猿人骸骨,上接的或許正是Nelly的這一基因,因而劇中的香港青年萬華才會爆發出全劇最具力量的台詞:「自己的骨頭/祖先自己掘」。此外,「北京猿人」的「北京」二字不必敢說,我甚至懷疑「14歲」也並非編劇隨意設定的,只要上網輸入「14歲」、「青年」這兩個關鍵詞,你能得到的搜索結果不少都和近年的社會運動有關。正是編劇這般的巧思和縝密才使得這樣一個宏大的結構不僅立得起來,並且鮮活實在,充滿血肉。

4. 片甲三
當然Nelly這段戲之所以動人,扮演Lucile的溫玉茹也當記一功。她的台詞真摯動人,絕不矯揉造作,隱隱的哭腔簡直是她的招牌。你彷彿能感受到她的情緒剛剛湧至眉頭,待要化作眼淚時,便又悄悄收了回去。或有一兩句確實留下淚來,那也是微微滲出不易察覺的,觀眾只能在台詞裡聽見淚水。發乎情感,止乎技巧,或許便是如此。很多人常以為能哭就是演技好,但我以為能哭、會哭,能不哭,是三個層次。能哭只是基本技能,會哭是哭得恰到好處。再上一層,能不哭或是最難的層次,在可以用眼淚煽動觀眾情緒的地方,演員反而壓抑並控制這種流淚的衝動,從而形成一種情感與理智的張力,這更為動人也更有力量。從欣賞演技的角度說,看演員怎麼讓自己不哭要比看演員哭更有意思。此外,說到台詞,扮演Lucile好友德日進的演員黃衍仁也很值得一說。黃衍仁更廣為人知的身分似乎是音樂人,此戲的音樂和主題曲《麵包與玫瑰》正是出自他手。他的歌聲真是動聽,或許也因為是歌者的緣故,他的氣息控制得很好,絕對是「靚聲」。擁有「靚聲」的人難免喜歡賣弄聲音,走火入魔的話說起台詞甚至拿腔拿調,有聲而無情。他飾演的德日進是一位神父也是考古學家,西裝筆挺,官仔骨骨,扮演這類形象絕對是賣弄聲線的大好機會,但他的台詞溫柔而有力,毫不做作。德日進在這個戲裡有重要的作用,他的Noosphere進化說是這個戲的一個理論原點,限於篇幅,這裡不能展開細說,簡而言之就是,人類終將進化到精神相通的境地,形成宇宙生命。這種相通超越時空,因而被殘害的猿人Nelly、經歷俄國革命的女演員妮娜、經歷八九民運的搖滾樂手張炬、參與抗爭運動的香港演員萬華、為文化部工作陷入對社會抗爭的思辨的攝影師阿照,才能無礙的在這戲裡穿梭,而彼此所經歷的苦難與作出的反抗也一併成為人類的共同記憶。不得不說德日進在整個劇本結構裡舉足輕重,然而黃衍仁的表演並不會讓這種份量氾濫,乃至於有一種自以為是的架勢,相反他恰到好處的表演使這一理論框架無聲無息的融合在整個故事中,不著痕跡。

5. 片甲四
Lucile和德日進這條線已經頗為動人,然而與當下更接近,更能引起觀眾共鳴的應是香港青年萬華和阿照的故事線。但已經囉嗦得夠多了,不能再展開。要提的是兩位演員的表現。江浩然扮演的萬華所爆發出的力量和她顯得有些弱小的身軀形成形成別具意義的張力。香港不正是一個小得在地圖上也找不著的小島嗎?但是這個小島的一點風吹草動,也足以使國際局勢風雲變色。更不用說當這個小島受到壓迫時,所產生的反抗會是多麼激烈。江浩然身上的力量一方面來自角色,一方面也來自這一兩年香港所經歷的種種。當然如何將這些積聚的力量張弛有度的在舞台上釋放出來,則需要很好的表演功底,而她顯然完全做到了。比如示威的場面和抗爭的前線,雖然沒有在舞台上重現,但是單靠她一人在舞台上奔跑、喘息、翻滾,還有那緊湊的台詞,你會感覺到彷彿劇場外便是催淚煙瀰漫的現場。這種台上沒有實境可以憑藉,完全靠意識虛擬的表演,稍有差池,便頗為滑稽,演員要有很強的信念,才足以引領觀眾,而江浩然的表演俐落準確,說服力十足。和她對手的是扮演攝影師阿照的梁天尺。這個角色的難度在於,儘管在思想上他和抗爭者同一陣線,然而他對抗爭運動本身不無懷疑,那麼如何在籠罩全戲的人類抗爭史框架中安放這樣的聲音呢?哪怕在日益撕裂的現實社會中,這樣的聲音也面對著不少非議。因此這種聲音一不小心便很容易被塑造成懦弱的形象,沒有力量。和沖勁十足的萬華相比,阿照很容易被蓋過去,成為一個無關重要的點綴。然而梁天尺的表演能夠使阿照的質疑擲地有聲,同樣具有力量。在萬華和阿照對質的一場戲中,阿照的質疑幾乎要讓萬華語塞,兩人力量相當。無怪乎有劇評人以為此戲是傘運之後最圓融的社運題材作品,我以為圓融之處正在於此戲能很好的安放不同的聲音,不隨意批判,引人深思。

6. 片甲五
必須停筆了,盔甲已然散了一地,揀拾的人恐怕也嫌太多太重。實際上可以談的還有很多,例如本戲前半部分改成的廣播劇、戲中的音樂、舞台的設計,尤其是導演設計的穿插在戲中的演員訪談,不獨是不斷抽離觀眾的情緒,同時打破戲劇與真實、歷史與當下的界線,饒富意義。這些等到此戲再再重演時再談吧。能不能重演呢?或許到了戲中的二零二一年就會知道了。到時香港或許已然重生,以回歸的面貌,或是以搖滾的面貌。
(劇照由前進進劇團提供,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