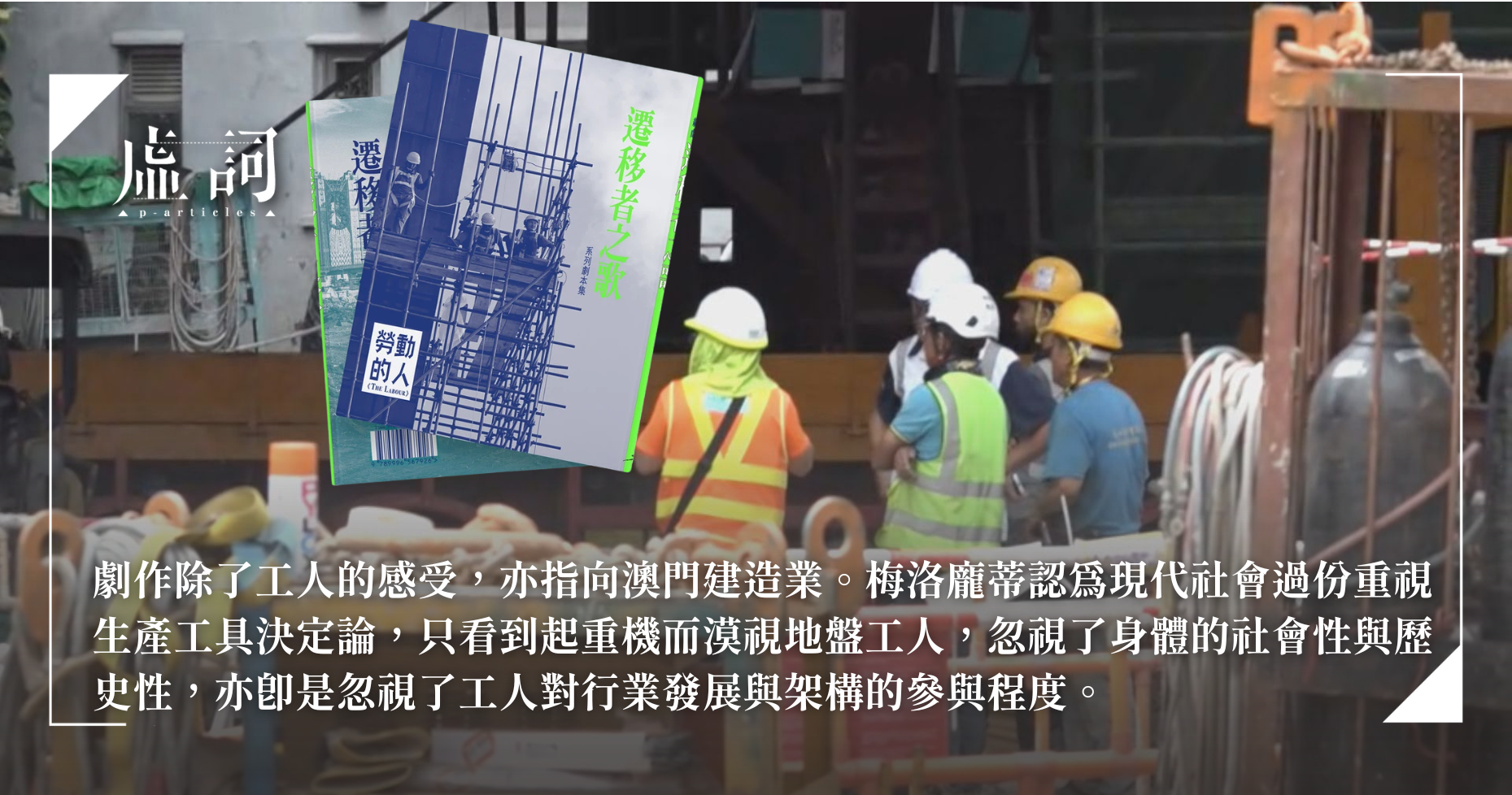《遷移者之歌》藝術的形體,勞動的身體
今天我還記得那在半空中搖搖曳曳的時光,很多年前隨朋友打建造工賺外快,在未完工的地盤裝上落地玻璃,完全信任那僭建於窗外的竹棚,不斷嘗試熟習不同裝修工具,而至今我還未完整看過那時親手造的建築物。這經驗未令我理解或同情建造工人,即使一起食飯,煲煙,但講話內容總是不著邊際。而因為大地盤,工人佔據住所附近幾個餐廳時,心裡一樣抱怨他們把餐廳逼得又臭又吵。
2023年,筆者在澳門藝術節碰到《消失的身影》,在這個多小時裡,接觸到工人們的聲音,我突然感到自己理解了多年前那些工地同事。遷移者之歌的編導莫倩婷,亦更長時間地擔當建造女工,但她是如何理解工人們,如何使工人們打開心扉地發聲?莫倩婷提到在排練室小休時,突然回到地盤工作的某天回憶,看到女工席地而睡,再緩緩坐起來,我想這可能是最能感受之處,每天身體的勞動姿態,更勝千言萬語,這大概是兩劇皆以紀錄形體劇場為定位的原因。紀錄片多著重面見訪談、相關片段呈現與歷史事實梳理,雖然角度手法數之不盡,但相對劇場還是較第三身客觀視覺,盡量少效果而不修剪地呈現真實;紀錄劇場則以現實為原材料,運用想像力發掘出與材料連結的劇場性,以藝術手法提煉現實的某一個面向。莫倩婷在兩劇作了多番嘗試,直接在劇場播放訪問錄音或生活片段並以形體回應,亦以形體為主呈現角色扮演甚或意象,以身體為連結核心,建構出整個舞台現象。書中收錄兩個劇本,除了對白文字外,亦有詳細清晰的舞台指示及導演手記,相當能夠還原演出實況。
如何在劇場了解勞動工人?
19年的《勞動的人》集中在移工彬哥的經驗上,並置80年代澳門建造業發展與彬哥生平,演員第三身敍述他入行及移工,亦加入他老闆與兒子的角度去看待彬哥,有錄像呈現其生活日常,當中著重他黑工的經歷,有第一身扮演他的苦況,亦有其他黑工被捉的部分,尾段來到現況,面對多年建造業工作積勞成疾,卻又無可奈何。由開場的工業意外新聞到尾場的沉默,整體氣氛相當沉重,那大海的意象和應彬哥轉行打魚的挫敗,亦指向三十年漂泊人生,彬哥自白有所後悔入行,但這些真實聲音總是唏噓多於控訴,演員的形體在其中唑亦是沉重而無奈的,亦能發現當中的動力與掙扎,這種掙扎在劇中,以合唱《我是一隻小小鳥》來寄意自由的嚮往,在其中演員有回應這些經驗,會想起自己父親,又或想到在學時工人佔據餐廳的情況,聽完彬哥的故事後,能對這些勞動者理解更多。
22年的《消失的身影》則集中疫情期間因再培訓政策下,不少失業人仕再進修並成為地盤工人的經歷。當中較著重地盤女工的身份與工作狀況,導演親身地盤工作後,與受訪者距離減少而得到更豐富而多元的訪談,有不同女工的聲音,有上一代移工與黑工的狀況,另外亦以女工兒子Gary作主要視角,觀察女工在當中的刻板印象,以及所積累的辛酸,當然性別議題只是起點,因其擔任勞動相對較少的工作,與垃圾工、沉箱、雜工等男女皆有,其身影較不明顯但辛勞及危險程度不相上下。對比《勞動的人》的沉重,《消失的身影》有更豐富多彩的劇場語言,例如演員不斷上落垃圾車建立西西弗斯的象徵;以大量舊衣服穿在身上比喻垃圾工作,對比穿西裝的上層人;其中一段以抖音Live播放Lofi hip hop的影片,演員不斷Rap,由自己家人講到工人性別印象及社會,後設地以表演員的心聲來審視整個作品,因而導演的視野亦更強烈,大膽地選擇富有時代性的流行符號,富生活感的意象呈現,今整個作品不止於紀錄,更有其論述框架。
勞動的身體
工人的生活感受,無論是由早到晚的艱苦,或幾十年日積月累的辛酸,都必然是身體知覺的,可是當他們描述被出來,無論工人口述還是間接描述,知覺感受已經不是原初的知覺本身,任何客觀觀察或科學知識都只會把我們拉得離工人更遠,但梅洛龐蒂認為身體才是人們表達意向的可見形式。所以知覺經驗的表達只能是主觀而動態的,每當我們嘗試回想及重構記憶,敍述視角改變,世界亦改變,「遷移系列」創作 的形體並不止於一種表演性或作為構建畫面的工具,更是莫倩婷通過地盤工作而得到的知覺體驗,與受訪工人的經驗相融後,嘗試令演員以形體方式呈現工人在當中的勞動身體,再現推垃圾車的如卵擊石,高空工作的危機四伏,逃離追捕的身不由己,垃圾工作的重擔隨身。這些形體是發生而非重現的,梅洛龐蒂在《知覺的世界》中認為現代藝術是一個可能表現方式,因為它不在確定,而是在不斷發問。劇中有工人討厭工作,亦有喜歡工作,加入上層人、兒子或老闆視角,男性觀看女性的刻板印象,演員對工人身份的反思,導演對地盤工作的體察,正是對議題的辯證與發問,並非要大家觀賞後更理解工人,反而更知道自己不理解後,自行發問。
劇作除了工人的感受,亦指向澳門建造業。梅洛龐蒂認為現代社會過份重視生產工具決定論,只看到起重機而漠視地盤工人,忽視了身體的社會性與歷史性,亦即是忽視了工人對行業發展與架構的參與程度。當中最明顯就是偷渡黑工,其身影完全在社會歷史之外,即使是正式工人,其在地盤中的身體依然會被失去應有的重視。地盤並非城市環境般有安全保障,但亦非自然環境那樣自己負責,地盤是人工被設計,卻因施工中而沒得到充份保障,身處沒有戰爭卻同樣危險的環境中,出現意外後甚至有可能被隱瞞,甚至連弔唁都被禁止,工人的生命因而變得危脆。這些被忽視的身影,正是導演想提出來重新置入公眾視野的願景,不單止澳門,而是香港甚至亞洲不同的經濟發展地區會出現的境況。看完劇本,我們未必就能從中完全理解工人,卻提醒我們遇到每一位工人,其實都需要我們更多的接觸,令他們能參與於社會中,令他們的身影能夠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