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一鏡過迷思更重要的疑問符碼——簡論《混沌少年時》的敘事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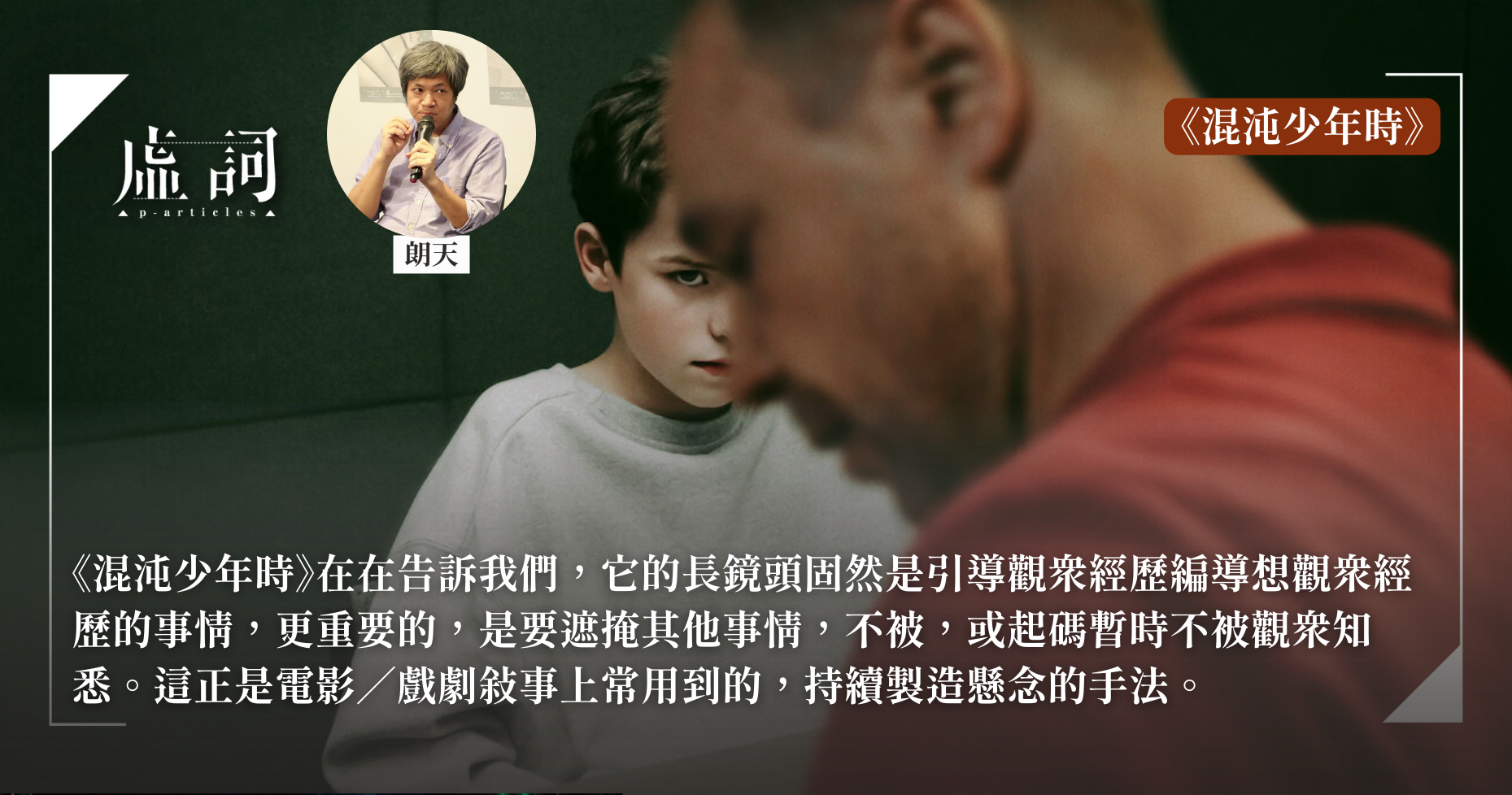
Template (47).png
特警清晨破門突襲民居,剛捱夜更回家的爸爸被殺個措手不及,全家陷入驚惶恐慌,但官方目標不是他。手持機槍如臨大敵的警員劍指樓上其中一間睡房躺在床上的小伙子。後者據稱十三歲,但看來還只是小孩子,不旋踵鏡頭拍攝到他跨下濕了好一片。
本來神色緊張的帶隊黑人警官到這時才稍為和緩下來,他找來孩子的父親,吩咐他替孩子梳洗整理一下,然後才正式把疑犯占美帶返警署。
以上是英劇《混沌少年時》(Adolescence)的開篇。特別點出尿褲子此細節,因為這正是編劇積索恩(Jack Thorne)和史提芬格拉咸(Steven Graham,同時飾演占美爸爸艾迪)精心經營的懸念起點。當大部分觀眾被那每集一鏡直落的敘事方式吸引住時,作為最重要的敘事符碼經營者,兩位編劇顯得很懂得控制觀眾的意識流向。
也許「神劇」的封號太濫,當一連四集,每集一小時的《混沌少年時》出來時,儘管口碑載道,心底實不敢抱太大期望。尤其領教過畢贛的《路邊野餐》(2015)及《地球最後的夜晚》(2018)裡那種炫技卻不乏「穿崩」的尷尬操作,所謂超長鏡頭、零剪接的調度迷思(myth),大概早已脫魅(disenchanted)殆盡。
有人說長鏡頭會令人覺得被拍攝的場景顯得更真實,因為現實是沒經剪接的,但真的嗎?事實是:現實生活裡被我們保留為印象的畫面同樣經過「天然」的剪接,我們眨眼和記憶發揮了剪接師的功能,當年愛森斯坦提出「垂直蒙太奇」(vertical montage)的說法時,更是考慮到場面調度也是某種廣義蒙太奇。單一鏡頭裡面的影像取捨,如何有效強化再現或記起時的感受和情緒,和剪接或蒙太奇一直以來的發展方向根本不謀而合。
在菲林時代,一鏡過之所以被視為某種神技,與其攝製難度大抵息息相關。當時一盒菲林長度以每秒廿四格的速度放映時歷時八至九分鐘,所以在不換菲林盒的情況下,最長的鏡頭都不能超越此長度,而要在這長度下進行調度,尤其遇上演員人數眾多,場景布置複雜時,稍為欠缺現場掌控能力都不易收到理想效果。
彼時,所謂全片一鏡直落是不可能的任務。不可能,也不必要。長鏡頭美學是要展現精准的導技,包括安排演員進出相關場景的走位、前後景配搭掩映、燈光變化/化裝/服裝細節,以及尤其重要的:演員演技特寫。超過八、九分鐘的調度聚焦,隨時出現諸如審美疲勞的反效果。
故此,歌頌零剪接完全是一種迷思,認為零剪接反映真實更乏理據。電影本就是一場夢,帶著強烈的操控性。絕大部份一鏡過畫面都沒能避開剪接,例如有時要彌補現場收音缺失的事後配音、加強情緒感染的配樂、必要音響的插入等等,只不過那些是一般觀眾不太注重的聲畫剪接而已。
數碼時代的鏡頭長度不再受限制,但很多所謂一鏡過畫面都是「假」的。即:並非真的在現場不關機地持續拍下影像,而是借助後期加工與數碼調整,令產品成果看起來是一鏡過的感覺。而由於鏡頭長度可以大大增加,為了令畫面活潑生動一點,對影機運動的要求也相應增加;加上數碼攝影機比較輕便,有些導演乘機賣弄奇巧或激烈的拍攝角度變化(如此更何來真實?),這方面《混沌少年時》除了首集開場一番操作,後段還算收歛,但其貫串全劇的長鏡頭使用及密集影機運動,並非為了說服觀眾事情真會如此發生。
恰好相反,無論是第一集的警署初步詰問或第二集的校園調查,都明顯為了遷就一小時長鏡頭的設定,而把相關事件高度壓縮了。現實上警方處理案件的手續程序,會否真的如此簡潔、有效率;進入學校訪問老師、學生,會否真的如此巧合,角色的情緒衝突,會否如此密集地爆發,這樣充滿戲劇性,走火警的過程又是否真的實時......諸如此類的問題,應該不難回答。有話劇觀賞經驗的觀眾自然從中嗅出濃厚的劇場手法,所不同的只是,一般話劇觀眾只會身處台下,欣賞台上各種演出安排,像《混沌少年時》這樣的影視作品,就能以影機帶動觀眾進入敘事世界,尾隨特定角色,透過他們的視點和遭遇,推進劇情,也有機會感他們所感,思他們所思。
在長鏡頭下,功能大大提升的影機運動,以強烈的引導性讓觀眾即時投入角色身處的時空,從他們的位置體會箇中處境。影機進入屋裡,觀眾也進入屋裡;影機移到車上,觀眾也如置身車廂,近距離注視被捕的占美。觀眾就坐在或站在角色的旁邊或身後,這樣,他們看到聽到特定角色或角色們所看到聽到的,也同時看不到聽不到在角色位置看不到聽不到的。
所以當第一集角色們在鏡頭前交錯而過,影機只尾隨其中一人進入某房間,原本跟隨的角色留在室外,他/她的遭遇觀眾便不得而知了。第二集當黑人警官路克和兒子在空課室內聊天,「學習」網絡語言含義時,外面發生甚麼事,我們也無從曉得。《混沌少年時》在在告訴我們,它的長鏡頭固然是引導觀眾經歷編導想觀眾經歷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要遮掩其他事情,不被,或起碼暫時不被觀眾知悉。
這正是電影/戲劇敘事上常用到的,持續製造懸念的手法。
尤其是強調每一集都要有「吊胃口位」(hook)的電視連續劇敘事公式。所謂「一鏡到底」的手法,其效應正是用整集的篇幅,形構一個巨大的懸念,吸引觀眾追看下去。
《混沌少年時》第一集的懸念由一開始的尿褲開始。尿褲,加上飾演占美的演員奧雲谷巴(Owen Cooper )討好的外型,比角色年齡還年輕的舉止相貌,觀眾直覺上傾向警察可能搞錯了甚麼,抓錯了人。拘捕行動之後的一連串影機運動和場面調度,除了交代案情和主角家庭連結(主要是看起來不錯的父子關係),也有效製造了反上反的雙重懸念——第一重反轉:當警探展示天眼監控影像,推翻了觀眾起初覺得占美極可能是無辜的直覺推斷;然後再用占美的堅持立場,勾起「為甚麼」他可以這樣的疑問。好了,即使真的是他做的,他的動機呢?是否還案中有案?
第二集的調查基本上是行兇動機調查。表面情節是尋找兇器,逐步揭發的是占美身為網絡霸凌受害者。於是,反上反再反一轉:原來他真的有苦衷的!隸屬外貌協會的觀眾更有機會主觀上準備為其開脫:說不定之後會有新劇情新證據,證明他確然被冤枉了。
第二集引發廣泛討論的「有害的男子氣慨」(toxic masculinity),在第三集巧妙地得到具體展現,並且在充份配合全劇敘事需要的情況下,為觀眾帶來了一場精彩的語言角力。那裡,影機一反前兩集的高頻移動,集中在密室空間關注心理學家和疑犯的對話。編劇回歸話劇的念白經營,逐步揭開占美的「真容」。兩位演員的細緻演技,配合凝煉的鏡頭,協助我們深入占美犯案前後的心理變遷。是的,我們當然可以繼續同情他,他仍是受害人,制度和文化暴力始終是背後的「大壞蛋」,但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無論從倫理或法理角度,個人的最後選擇令他責無旁貸。更可怕的是:面對指控和事實,占美充份展示了何謂厭女,何謂推卸,何謂有意無意地徹底利用制度(包括家庭)賦予他的機會,一句話,濫用別人的信任,盡情剝削有利他的所有援助。
第三集那片咬了一口的三文治,再度顯示編導如何懂得使用關鍵道具。心理學家最後碰它一下也感到嘔心,基本上解答了之前引發的行兇動機疑問,但隨即產生新的懸念:外人尚且如此,占美的家人又將如何?全部第四集正是對此的終極回應。
《混沌少年時》完全符合典型的三幕劇敘事結構,第一幕以行動基礎(Action based)的敘事高開,來到父親看到天眼錄影結束,進入第二幕。拘留中心會客室的對話角力是當然高潮,之後進入第三幕中後段的「和解」和「善後」,對應第四集裡占美一家人的後創傷自處。
此劇合模卻不落俗套的地方並非那主角轉換(由占美到艾迪)的技倆,也不在不斷反上反卻不致失控的扭橋嘗試。老實說,假如沒有第四集對人性的深刻描畫,它的水平也只達到執行度高的通俗劇而已。編導讓觀眾得睹艾迪在自己生日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壓力之後,安排占美突來一通電話,毫無同理心地宣告他將選擇對判刑有利的認罪訴訟,拍來平淡如水,卻如重錘一擊,讓僅餘的自欺堅持也碎落一地。如此慘烈的背叛,固然再一次肯斷十三歲少年可以怎樣邪惡,還令片末艾迪進入占美房間,對著玩具熊喊的那一句「對不起」,顯得何以撕心裂肺。一刻前夫妻倆還在回溯他們究竟何時開始,不經意養成一個小惡魔。都不重要了,因為萬大事都關於自己,無論如何自己都有做不好父親的責任,而今天所面對的,就是他所要承受的惡果。一聲對象缺席的道歉,同時是懺悔,對自己,也對上帝(假如有的話)作出的懺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