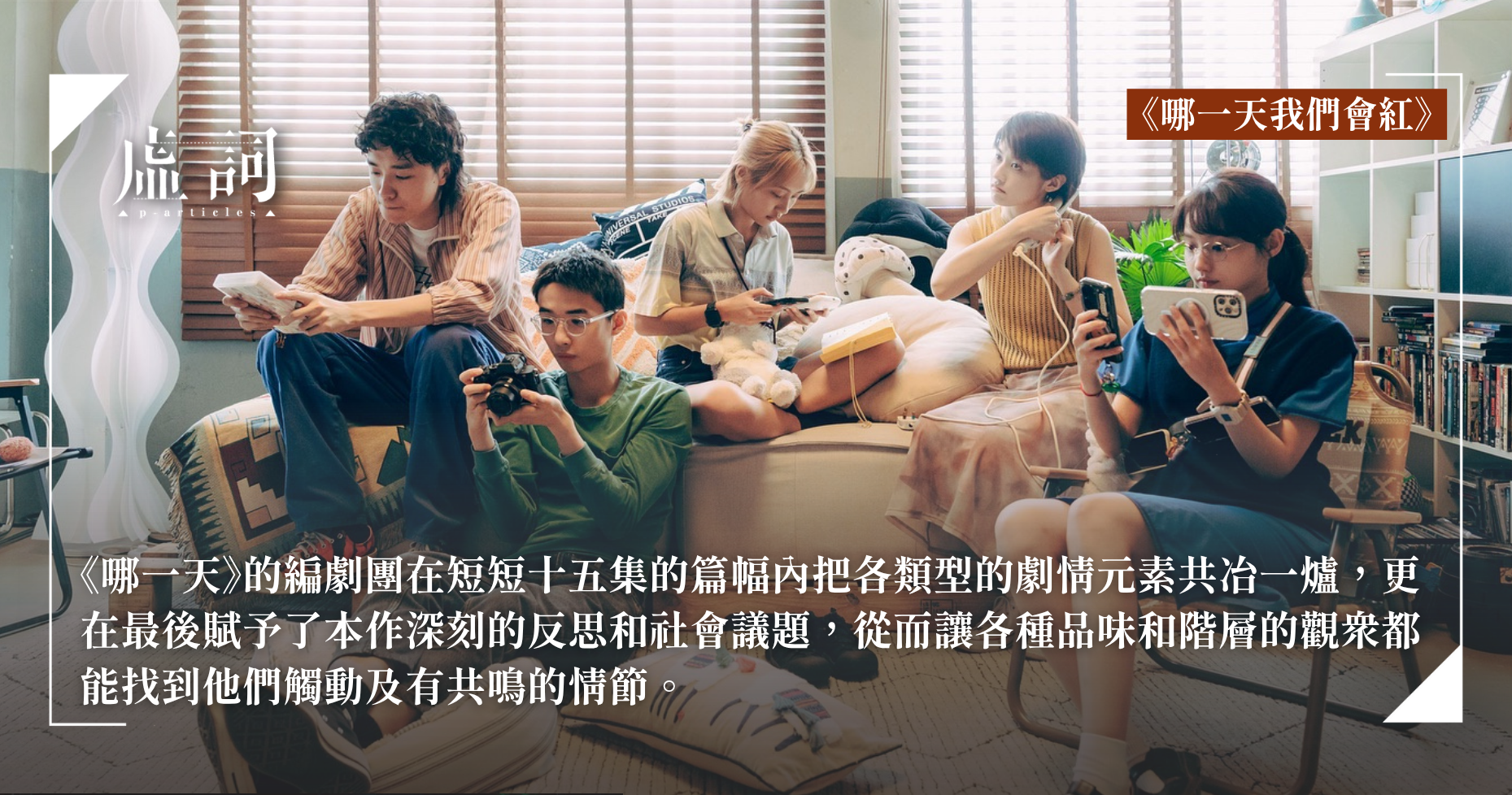當電影業陷入寒冬,電視台卻發起一場寧靜的革命——從《哪一天我們會紅》的三重創新說起
劇評 | by 寧霓 | 2025-05-27
電影業寒冬,幾乎已是令人煩厭的話題。
從戲院結業到票房大跌,再到所謂的演員斷層,幾乎每有這類新聞,都能讓一群電影喜好者傷春悲秋,再紛紛討論或辯論造成「寒冬」的原因及其解決之道。隨著被喻為都市傳說,萬眾期待的《風林火山》在康城午夜場被徹底負評,這樣的情緒仿佛到達新高點——最後的救命稻草應聲而斷,《風林火山》的那場大雪,仿佛已從虛構的銅鑼灣,吹到現實世界。
然而,當這場風雪未見停息,筆者卻從電視中看到各類觀眾的逐步回歸。說的自然不是早已老化得失去活力的TVB,而是在紅館墮屏事件後,一度陷入低潮的Viutv。
踏入2025年Viutv劇930忽然不暴走
在過去,Viutv以旗下的偶像團體Mirror為業務核心。其自家出品的劇集雖偶有佳作,但質量參差不齊。曾引起大眾關注的《I.Swim》、《季後賽》和《冰上火花》等作無不被冠上「暴走」、「爛尾」等標籤。這些作品也極大地打擊了觀眾對Viutv原創劇的信心,以致大眾亦漸漸淡忘了這項娛樂選項。
然而,在2024年尾起,Viu劇忽然悄悄地起了變化。由《2月29日》導演羅嘉駿主導的《十七年命運週期》率先在一群核心觀眾間廣獲好評。及至接檔的《出租大叔》和《無用的謊言》等都能維持一定質量。而踏入2025年,Viutv原創劇更像起了質的變化。一眾作品非但不再爛尾,更開始各有風格,甚能看出它們的作者性。
風格和作者性,這是在強調流水作業和穩定輸出的TVB所無法置喙的。甚或乎,在已日漸公式化和套路化的日韓歐美劇作中亦是難能可貴。試想像,由《老是常出現》的低俗瘋狂喜劇,到《弊傢伙!我要去祓魔》的簡約風CG,再到《三命》的銀河電影風,當中的跳度是何其之大。而幾乎每項「特色」都能讓觀眾識別出其幕後團隊的「個性」。
由是,風格化和一定程度的作者性逐漸成了Viu劇的DNA。這對採取外判制的Viutv來說,既是因,亦是果。無怪乎曾有網上留言說,看Viu劇就像抽盲盒,不到播出日都不知開出甚麼。這種「抽獎」的特性,所說的正正是上述的兩大基因。
站足在風格化和作者性之上,Viu劇總算找到了在「選秀——偶像經濟」以外的出路。而筆者相信,這兩者是真正能讓一家本地電視台足以抗衡全球化串流平台的基石。在這前題下,筆者認為Viutv新近播出的《哪一天我們會紅》,正是這套新公式目前的高峰和最佳範例。
由《三命》到《哪一天》
只要對香港影壇稍有認識,都會聽過杜琪峯和銀河映像的名堂。有趣的是,銀河映像成立於上世紀90年代尾,正是靠其特有的風格和作者性收獲一眾核心擁躉,從而度過上一輪電影寒冬。
今年4月播出的《三命》貫徹了銀河特有的影像風格及其「宿命」的主題,使觀眾從第一眼便能看出其出處。事實上,Viutv的官方亦是以這兩大元素來作宣傳,他們甚至刻意邀請各大傳媒,在電影院中舉行首映,為的就是強調這樣的「特點」。
從各方面來看,《三命》都像是舊時代的經典復刻。從喚回一眾核心影迷來到電視前的角度來看,它極為成功,但他真正的創新和時代性卻是有限,就連執導的三位導演也在杜琪峯及一眾舊神的大名下被輕易蓋過,所謂以老帶新,也許只是故人找到新的替身。《三命》,仍然是「杜琪峯」的作品。
令人驚異的是,只隔了一個月播出的《哪一天我們會紅》卻走上了另一極端。基本上,《哪》除了劇名戲謔了某套港產電影外,它的一切元素都是「新」的。更難得的是,這份「創新」不單是就本地影業而言,即使放眼世界亦可能如此。
《哪一天》的第一重創新:演員的新
《哪》的「創新」可從三個層面逐步論述。
首先,它的演員是「新」的。單看《哪》的宣傳海報和主視覺圖便不難發現,它的主演陣容幾乎全是二十出頭的年輕演員,當中更有不少是首次參演電視劇。單是這一點已令人感覺一陣清新。
進一步而言,演員的「新」並不僅止於選擇和起用的層面,而是劇中所有稍有知名度的演員,都獲分配到與此前的幕前形象完全不同的角色。例如,鍾雪瑩由《教束》和《看我今天怎麼說》中的社會新鮮人搖身一變成惡女形象的「雞粉」;黃溢豪出演了與其外型極為相衝的A0毒撚,「味精」(但卻甚有說服力);而岑加其則一改此前的「精叻小男人」和「毒撚」形象,首度挑戰了需要表現高姿態的Channel老板「況哥」。而其他如梁仲恆、麥佩東等實力演員均獲分配到一個能展現其多面性的位置。
縱觀整個演員陣容,《哪》的編導團就像是刻意要與演員們的一切既有形象劃清界線。同時,我們能看出整個幕後團隊在堅持「新」的同時,在導戲和角色塑造上給了自己多大的挑戰。若將這份叛逆與《三命》對比,則難免令其中一方感到尷尬。
常言道,新演員和新導演需要機會,但顯然不是所有螢幕時間都是機會。正如飾演Kimchi的林宣妤在劇後的直播中談到,這是她從影以來第一次接到有完整曲線的角色。需知林宣妤則曾在TVB工作多年,更出演過《夕霧花園》和《富都青年》等知名作品,但就連她亦沒有得到過哪怕一次證明自己演技和駕駛角色能力的「機會」,我們便知道「機會」從來是重質不重量。
這套理論放在幕後人員身上同樣適用。《哪》的導演應智贇,曾因《超神經械劫案下》而廣受批評,但《超》實際上是一個翻拍再翻拍的三手項目,其原著的韓國電影《我們全村都不是人》以及台灣翻拍的《詭扯》本身已存在不少問題,這樣的機會又有多大的價值?
近年來,本地影視圈「接棒」、「傳承」這類關鍵詞甚囂塵上,不少電影愛好者呼籲「以老帶新」。甚至連政府資助的「薪火相傳計劃」,都是採用了老導演帶新導演的方式。然而,所謂的「以老帶新」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讓「新」的事物有其主體性和能見度?
近年來,TVB亦嘗試開拍了如《青春不要臉》這類力推新演員的劇作,但它重複《娛樂插班生》的舊路,讓一眾新人模仿、戲謔或影射諸如張曼玉、劉德華這類經典演員,到頭來只是消費了集體回憶,和新人們的青春。歸根舊底,這些項目的策劃根本沒能力或意願讓年輕的台前幕後回到他們的主場。而這一點,正正喚應了《哪一天》的第二重創新——題材和年代的新。
《哪一天》的第二重創新:題材和影像的新
假如Netflix的現象級神劇《混沌少年時》的爆紅,有部份要歸功於它談及了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那麼《哪一天》在這部份可能要它走得更前。因為當《混沌》只以旁觀者或成年人的視角看待這群數碼原住民時,《哪一天》已經以他們為主體,去講述他們上位、相爭以及在虛擬和現實身份中爭扎的故事。
來到2025年,Youtuber和Tiktoker早已是年青一代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職業。縱然人們對這現象有何評價,假如時下的創作者沒法正視這現象,那他們的作品便難以回應時代。過去,有不少作品嘗試捉住這種脈絡,但成功者少之又少。國際級的Netflix大製作,《東京星夢》(Followers)拍得像數碼版的《毒海浮生》;《混沌少年時》則把網絡渲染得像是無處不在的克蘇魯;及至台灣的《影后》其主題仍是聚焦於電影和影視圈。能以劇集的形式講述Youtuber和內容創作者的文本,《哪一天》即使不是第一個,亦是第一批。
題材和內容的新,意味著它幾乎難以找到參考對象。試想,《哪》第6集中的「擠牙膏」大戰,第9-10集的網絡輿論戰,除了現實世界外,還有哪些現成的文本可供其參考?
一直以來,Viu不乏具原創性而精彩的作品。但《IT狗》仍有參考美劇”Silicon Valley”的影子;《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可被歸類為日式生存遊戲類型。相較之下,《哪一天》確實在原創性方面到達了一個新高度。
與此同時,新的題材和內容亦需要新的影像語言,以及符合其氛圍的影像風格。要復刻中世紀,或60年代的感覺是有既定答案的,但要把網絡世界的喧鬧和紛爭視覺化,則需要巨大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而《哪一天》確實交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它更捨棄了近年已成標準的兩色或三色的配色法,大膽地以極度繽紛和多彩的畫面,建構其熱鬧和趣緻的世界。這種選擇對服裝、造型、後期調色以及總其成的導演都是巨大的挑戰。更令人敬佩的是,如此破格的藝術決定,不是面向包容度和品味較高的電影院觀眾,而是會坐在電視機前的普羅大眾。
這亦引出了《哪一天》的最後一重創新——建構新的觀眾群。
《哪一天》與新觀眾
傳統影視行業陷入困境,更大的原因在於YouTube或Tiktok中短片和極短片的流行。現代的觀眾不但耐性變短,他們的品味和感興趣的話題也更為割裂和碎片化。
以廣播電視台而言,它的固定觀眾群大多集中在40歲以上的群體。我們因而可以看到「中年好聲音」長做長有,更能成為TVB的皇牌節目。故此,站在台方的角度而言,開拍以網絡生態為題材的《哪一天》實際上是相當困難的決定。這難道不會成為無人問津,遠離主觀眾群的極小眾作品嗎?理想的項目策劃人想必會有這番質疑。
然而,我們能看出《哪一天》在採取新題材的同時,為了連結各大觀眾所花的心血。首先,《哪一天》所使用的「梗」、「迷因」或「致敬」橫跨了多個年代。由《創世紀》許文彪的「公平咩」,到高登年代的古早潮文「靚女唔痾屎」,再到「YouTube is dying」、「廣告從業員」等,《哪一天》都順手沾來,同時為它們賦予了新的語境和活力。認識這些「梗」的出處的人會感到份外親切,就算不認識的也會感到那些對白甚為有力。而這些「致敬」的考據則能成為眾人的話題和談資。
另一方面,《哪一天》的編劇團在短短十五集的篇幅內把各類型的劇情元素共冶一爐,更在最後賦予了本作深刻的反思和社會議題,從而讓各種品味和階層的觀眾都能找到他們觸動及有共鳴的情節。例如多次出現的情感戲、2和3集的辦公室政治、第6集的類諜戰戲碼、9和10集的長片商業戰和最後的政治戲等。這些不同的元素糅合在喜劇的大旗下,足以連結喜好不同的各類觀眾,同時能令所有人深深地喜歡上劇中的不同角色。
坊間有論者認為,本作結局週的走向不如心中所想,但實際上它成功提升本作的廣度和深度,從而觸及自我、存在、群眾等哲學和社會議題,也讓眾多角色完成了他們的蛻變和救贖。若非這種走向,則它始終會是一套輕鬆小品,而非如今這套極具火力和批判性的時代之作。
總括而言,編劇團的努力令《哪一天》不再是束之高閣,需要被影評家重重保護的藝術品,而是真正雅俗共賞,莊諧並重的作品。這樣的取向有利於更廣大觀眾社群的博成。
《哪一天》與電影業寒冬
單從劇作的質量而言,《哪一天》無疑是成功的。這並不代表它能夠或應該成為未來其他影視作品的範式。事實上,這個質量和精度的作品大有機會是可遇不可求。但它起碼指明了我們應對新時代時可留意的幾點:
第一,不應再迷信形式化,已證明無效的「以老帶新」,而是應讓新一代回到他們的主場,並大膽地讓他們讓前輩們平等地角力。
第二,一定程度的風格化和作者性是應對全球化平台時足以立足的基點。同時,媒體工作者和文化評論員應對幕後人員的崗位、職責和創意有更敏銳的觸角。
最後,我們在養成新的觀眾時,應採取更多元和全面的策略。單是令他們有共嗚,或迎合他們的話題並不足夠,甚至可能適得其反。真正要做的,不是「吸納」或「吸引」新的觀眾,而是在現有的觀眾基礎上,建設和擴張整個觀影社群,要令整個社群變得「有趣」和「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