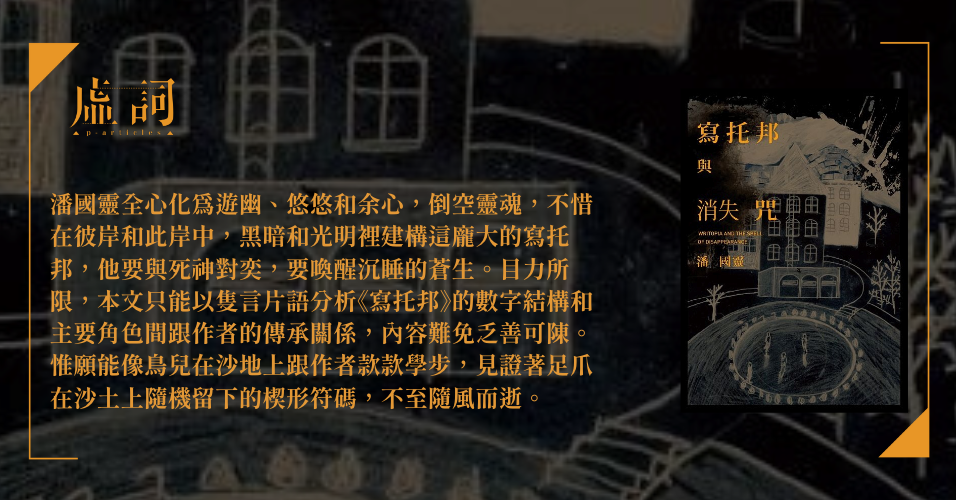從個人傳承到浮沙幻影——論潘國靈《寫托邦與消失咒》
所有書寫都是在距離中進行的,力求接近真實,而終究未可竟,如撲一隻永遠撲不到的蝶。
——《寫托邦與消失咒》・洞穴放映會
一、引言
時間回朔到一九九七年三月,潘國靈於《香港文學》三月號發表了他第一篇小說〈我到底失去了甚麼〉,以一隻雌雄異型的黃蝶銘刻他往後生命的基調——少年的敏感、稚子的純粹,停泊在原初無可折返的彼岸。[1]從這篇短篇開始,疾病、尋找、失落、消散、擬物、愛情等主題均散見於他的結集。二零一六年,他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在歷近廿年的累積下,潘國靈建構了他那森羅萬象的寫托邦,一方既是沙城裡的寫作療養院,同時也是書寫人沉溺的洞穴和幻影,其中虛實交錯,留給一眾評論者在一切消失前竭力解咒。
《寫托邦與消失咒》(下簡稱《寫托邦》) 出版後獲得不少回響,蘇苑姍分析《寫托邦》內三位主角的交替重疊而消解寫作的主體,以「書房」、「被包圍的場所」、「洞穴」等封閉的意象纏繞成一幅一體三面的自(字)畫像。[2]勞緯洛以鐘擺的走向證成小說家遊幽一方面是自己的造影者,同時又是觀影的囚徒,彷如鐘擺的兩端。[3]蔣曉薇以親炙經歷形容潘國靈為末日先知,在原初的洞口中啟發尋道者,或像在鐘擺正反之間以毒攻毒,以生命書寫存在與虛妄。[4]洛楓引克莉斯蒂娃的文本互涉理論,把《寫托邦》內星羅奇佈的古今中外哲收入其「文學萬花筒」,又以傅柯的「異托邦」(heterotopias)和「異質空間」(heterrogenous space)場域比對「寫托邦」與「沙城」,旁及西蘇的以書寫作為一種梯底層的下沉狀態,總括《寫托邦》中的書寫與疾病、作者與讀者、真身與影子、演員與觀者等的二元對立。[5]凌逾認為潘國靈在《寫托邦》中不斷為新詞下定義,自創寫托邦和寫作療養院來書寫他的寫作病理學,又從西西的「我城、浮城」為基礎創建「沙城」,形容本應住在華麗安居的作家卻又不甘安逸而選擇跟城市訣別,這種以毒攻毒卻自損身心的法門,凌逾尊稱為「消失派文學」。[6]
以上論者主要針對《寫托邦》的人物和不同意象作闡釋,本文嘗試另辟蹊徑,以詮釋學“Hermenutics”「以經解經」的方法,重新審視潘國靈過去旁及《寫托邦》的創作文本,分析其中的核心敘事結構,並以故事中的三個主要角色:遊幽、悠悠與余心體現潘國靈對文學的傳承與創作《寫托邦》結構間的關係。潘國靈曾表示,早在二零零七年已計畫寫一部名為《三個人的雙重奏》的長篇小說,以多則古典對照命題(婚姻與獨身、屍體與身體、悲劇與喜劇等),敘述二女一男橫跨二十年包含個人與社會變化的現代故事。雖已寫下數萬字,但最終未能完成,後來才轉向發展《寫托邦》。[7]從現存第一部長篇發展出來的獨立短篇[8]比較《寫托邦》的內容,會發覺這些短篇更貼近他過去的小說結集如《傷城記》、《病忘書》、《失樂園》和《親密距離》,但在角色處理上,《寫托邦》沿用《三個人的雙重奏》二女一男為中心,內文亦不住見到其他短篇的影子。
二、七作為解秘之鑰
詮釋學就字源而言,字根hermes原指「神明的信息」。士萊馬赫(Schleiermacher 1768-1834)指出所有的詮釋都涉及「了解」(verstehen, understanding),他把了解看成是一種對話關係的情境,指作者構造一系列文句表達內心經驗,聽者接收並通過一種「神秘」的過程把握到它們的意義。他又提出「詮釋學循環」(Hermeutical circle)觀念,指出整體與部分之間的循環關係,要理解部分意義,必先理解整體,反之亦然,這種類近作者與讀者間的循環論證正是士萊馬赫所涉及的「神秘」過程。就封印的解秘,潘國靈在《七個封印》嘗言對「七」這個數字有一份難解的情結,七在希伯來聖經中代表完全、神聖和完美,他也把「七」成為在寫作中「由內到外,由肌膚滲進血液的七個生命印章.......一定程度上也是個人創作世界的七根支柱」[9],是伴隨著作家生命歷程的鑄模烙印,也是構成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七根支柱(章節)分別是:一、藝術哲學,二、作家與書,三、觀影世界,四、文化研究,五、城市夜色,六、身體政治及七、愛情經典。頭四項包括他的藝術和文化評論,同時也是他創作小說的養分;後三類是他小說結集類型的對應: 《傷城記》、《失樂園》記錄城市夜色,《病忘書》刻下身體與政治烙印,《親密距離》見證人間愛情的悲歡離合。
《寫托邦》在結構上也延續了這個生命印章。小說脈絡以七章作為柱子,各章分別書寫了「寫作」和「寫作人」各自的命題。第一章〈寫托邦〉描寫寫托邦既是寫作的無有之鄉,理想之國,同時也是「寫作」的「療養院」(Writopia as Asylum)。既是被庇護、被包圍的場所,同時也是復康的場域,這種在標題中英語互文間語帶雙關的結構同時呈現在其他六章。第二章〈招魂屋〉(Apartment as Apart/ment)既為消失作家的落腳地(Apartment),同時也是在此岸和彼岸的虛實、分離間(apart)的招魂之處; 第三章〈消失咒〉(Disappearnce as Character)針對角色間的交換故事。主角悠悠在交換故事來製造更多更大的舞台場景,而這個寫托邦的舞台卻漸漸變成一個龐大的堡壘、洞穴、甚至是沙城中的監獄,人要逃離便如榮格所提出的披戴著多重面具(persona)。接著悠悠提出作者消失的十二種可能,包括閱讀、遊戲、自我沉溺、愛情、時光、憂鬱、寫作、瘋狂、城市、名利場、他方和生命盡頭的另一邊,正是潘國靈多年創作所關心的主題。當這十二種作家消失的可能加上余心其後補充的九個可能後,這廿一個可能平均交換給三位故事主角:遊幽、悠悠和余心後,均分得正好是「七」。往後從第四章的〈附魔者〉(Writer as (Dis)illusionst)到第五章的自畫像(Portrait as Effacement)正是透過第三章中過去東西方作家文字進行抄錄和自畫觀照後,帶出末後兩章〈出走記〉(Exile as Return)和〈洞穴劇〉。遊幽以作家的身份出走、消失,如鐘擺般跟在彼岸中的悠悠飛鴿傳書對話。「七」一直作為整部小說結構的支柱,同時也框住了角色們在龐雜的迷宮下的思想活動。
這種結構除了見於他個人的藝術筆記外,亦見於他的短篇小說結集《存在之難》。他在自序中再次提起九六年第一篇的手稿,那隻永遠撲不到的蝴蝶。他自言《存在之難》是「一個小說創作者由少年走到後青年的一本階段性小說自選集。」他希望藉這部小說的選取與鋪排,「構建出一個較整全的格局」。[10]這裡指的「整全格局」即為「一個作者經歷年月逐漸築建和浮現出的一個小說世界輪廓」,其中包括一些來回復返如圓舞漩渦的存在母題、隨個人成長幽微遞變的小說意境、關切旨趣、語言審美性等,也有貫徹始終的執迷如消失美學、身體疾病、城市憂鬱,以至對短篇小說多變性和可能性的探索和實踐,強調這部小說本身也是一個小說世界較具統攝性的獨特呈現。[11]這樣,《存在之難》的「七部曲」於焉生成,其編排亦依隨作者成長和小說創作的步伐而呈現。從第一部曲〈青春異境〉到第七部曲的〈人物畫像〉,短篇中的女巫逃避光明的地下洞穴、成長後一雙雙戀人玩著兒時的遊戲,由對人與物到對物與我,人與物件、與動物的書寫,再擴展到遊離於城市作地方志式的書寫,時刻「扣連上生命的雙重旋律,如鐘擺之永恆擺盪」,潘國靈稱它為「小說作為沉思體」與「小說作為城市體」,這些或龐雜的結構,或支離的碎片均在《寫托邦》中有跡可尋。《存在之難》在最後一部曲重提他原初創作的長篇小說——那「二女一男橫跨二十年的故事」,而這二女一男的原型: 彼得、多芬和艾繆斯的「三個人的雙重奏」雖然最後無疾而終,卻在《寫托邦》中以另一形式重現。
《寫托邦》的故事從第一章的前一頁就寫下這幾句話作為概括:
一個作家消失了
一場漫長的解咒
一個文字女巫的生成
一段幽靈的召喚
一趟消失的旅程
寥寥數語,已把整個故事內容及人物勾勒。這是一個作家出走、消失的故事; 作家的愛人為尋找心所愛的,展開漫長的解咒過程。其中作家是指遊幽,文字女巫和召喚幽靈者是悠悠跟余心,他們兩者互相交疊,在角色上成就獨特的三位一體。
三、我們都成為了一台戲景
遊幽的原型應來自潘國靈於二零零一年在《香港文學》發表的短篇〈病娃〉和〈母與女〉[12]中的「遊忽」。這位自小聽母親恐怖故事長大的小孩,在兩篇作品中向讀者展現他那充滿魑魅魍魎的童年。四年後發表在小說結集《失樂園》中的〈面孔〉和〈鴉咒〉,遊忽長大了,並成為一位寫作成病、寫作入魔作家。類近的情節見於《寫托邦》〈附魔者〉一章中,潘國靈細緻描述書寫有若附魔的狀態:
寫作是一種附魔⋯⋯如果你見過一些入迷的作家,在寫作的時候完全把自己關起來,在斗室的洞穴中草書著一串串可能只有他們能辨識的文字如符咒,忘了外邊的世界的喧鬧和日換星移⋯⋯[13]
然後是一連串近乎符咒的書寫:
把書牆當成與世界隔絕的距離屏障和防波堤誓死保護,一時意念轉動狂暴發作一拳一拳敲打牆壁或純粹緊緊盯牢它以為這樣憑藉念力就足以推倒弓堵堅固如囚室的心牆; 而這種狀態不是一日兩日而是經年如是日復日地重複如薛西弗斯推石上山般把終極徒勞當成唯一的自我完成。[14]
《寫托邦》另一主角悠悠,在回憶遊幽寫他其中一篇「少作」正是十數年前的〈鴉咒〉,這個「附魔事件」無論在小說的時間和內容上均直指《失樂園》中的同名短篇,而悠悠在談及遊幽第二部小說的其中一篇〈病年華〉時,說城市中的人患上怪病而最終成為異化者,遊幽在小說完成後更病倒就明顯連上了《病忘書》和自身的寫作經歷。[15]又四年,遊忽再次以孩童之身出現在短篇〈遊戲〉中。遊忽彷彿反老還童,能在看螞蟻的腳步中悟道,在玩捉迷藏、點蟲蟲、fort-da中見證珍惜的汽球一個個地消失。[16]直到再一次的四年,即十二年後的二零一四年,他在《香港文學》發表〈給寫作附魔的人〉,遊忽正式蛻變成遊幽,而這篇短篇小說最後亦成為《寫托邦》中的同名章節,只是刪除了最後有關構思小說的段落部分。[17]
在《七個封印》一篇題為〈救贖之姿,信與失信〉的自傳式散文中,潘國靈談及他對宗教與哲學的體驗,稱自己曾在「有神」與「上帝之死」間有如鐘擺中徘徊,[18]形容文學之路是對宗教的叛逆同時又一脈相承。他又自言曾以愛情作為人生的「第三宗教」,但在跌跌碰碰中體會人的意志薄弱,最後只能遊走於信與失信之間。在《寫托邦》中透過悠悠的憶述,有關這段經歷有更文學性的描寫:
你站在了信仰的門外,好幾趟。狹義的宗教之門,你來到一個基督教會門外,踏進去了,生活過了,又走了出來。替代的宗教之門,你來到一個織滿了玫瑰的愛情花園,你被玫瑰的色澤和美吸引過,隨手摘下一朵,發覺是有刺的,玫瑰原來是荊棘,於是你更著迷了,可不久玫瑰凋謝了,你又離開了。[19]
「作家與書」、「身體政治」和「愛情經典」是《七個封印》其中的三根支柱,跟《存在之難》中的「人物畫像」、「身體疾書」和「愛流離曲」章節互相對應。基督宗教,存在哲學和人間愛情都是潘國靈從遊忽到遊幽過渡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既是傳道者也是離教者,像浮士德跟魔鬼的交易,又如分散碎裂的分靈體,飄零在他龐大的文學體系中。
作為遊幽的戀人,悠悠的原型,見於二零零二年的《i-城志》〈我城05之版本零一〉。作為西西《我城》的延續,悠悠被設定成阿果的女友,是一位文藝少女,文本的悠悠只出現在阿果的回憶中。她性格偏執,說要寫一個關於城市的小說,如遊幽一樣,她在創作時會突然消失。她筆下的城市患了疾病,像沒形體的虛擬空間,還原為無數的0和1,漂浮於廣闊無邊的電腦母體。[20]潘國靈曾任職電腦程式員,在城市書寫中不時見到程式代碼的0到1。由「我」到「城」,悠悠延續著西西的「我城」和「浮城」,而〈我城05之版本零一〉中的插圖和標題更與《浮城誌異》中馬格列特的畫作互文,「她眼中的浮沉之城在向下沉沒中」[21],「那眼睛之城如環形監獄在不斷地被人窺視」[22]; 「烏鴉之城由不同的專家不斷地眾聲喧嘩」[23],「口罩之城是讓口罩對呼吸和空氣的陌生化」[24]。潘國靈聲稱從七十年代「我城」翻開,至八十年代「浮城」再到八九「傷城」、零三「病城」,或可稱之為一本「浮城誌」[25]。從個人到城市書寫,從我城到浮城再到《寫托邦》中的華麗安居和沙城,不難看到他對這個城市情感濃烈的書寫。如潘國靈個人所願,悠悠所肩負的絕不止於單單作為一個城市的浪遊者。她是遊幽現世中的編輯和戀人,作為尋覓消失愛人的招魂者,召喚消失咒的女巫; 同時她也是余心,這位長居寫作療養院,對世情冷眼旁觀之人的一體兩面。余心與悠悠在遠古時已有了塵世的約定,潘國靈引《詩經.鄭風》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點出兩角的雙生關係。余心的原型見於一九九八年《香港文學》的短篇〈被背叛的小說〉,後結集在二千年的《傷城記》中,[26]他以余心作自嘲式地道出作家在創作過程的荒謬和悲哀。到《寫托邦》時,余心已進化成寫作療養院的導遊(院長?),帶領悠悠來到“e-dubba”這所「刻寫板屋」,介紹當中為文本傳承而努力的「抄寫員」(scribe),並為月神娜娜(Nana)的女祭司安喜杜安娜公主,和抄寫員的神明女神妮莎巴(Nisaba)尋找繼承者。余心明言希望悠悠成為現代的月神女祭司,[27]正好呼應她對悠悠最後的話: 「一天寫托邦尚在,一天余心不滅。我把棒交給你了。」悠悠與余心之間,比跟遊幽更連著一條「隱影的線,藕絲的纏。」[28]
中國古代負責祭祀之禮者統稱為「巫」,見於《國語.楚語下》: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忠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29]
可見能繼承祭禮為巫之人,必須智、聖、明、聰兼備。悠悠作月神娜娜(Nana)的女祭司,余心為書寫女神妮莎巴的繼承者,兩者的一體兩面非筆者的妄論。潘國靈在二零一三年一月至六月間在《字花》及《香港文學》發表了三則短篇:〈密封,缺口〉、〈死魂靈出版社〉、〈分裂的人〉,同年結集成《靜人活物》[30]。在〈密封,缺口〉中的Nana和Nada,她們把「書房變成了寫作的洞穴.」,「住進了自己一手築起的文字城堡」,一直沒有離開彼此。[31]〈死魂靈出版社〉以後設小說形式,描寫主角娜達為「死魂靈出版社」編輯一本名為《一個作家消失了》的長篇小說,[32]作者是以「幽靈者」之名投稿,小說的主角是一對叫Nana的作家和Nada的編輯,場景有懸浮半空的「天空之城」、「寫作療養院」、「洞穴之底」、「通天塔圖書館」、「心牆」、「此岸和彼岸」等,凡此種種,都不難在《寫托邦》中找到相類的對應。到〈分裂的人〉,潘國靈更緩引《理想國.會飲篇》中阿里斯托芬關於男男女女原為一體的神話,指出人的自我與他者本來並非二分。Nana和Nada,「我」與「你」並存為一個生命的時鐘,並以鐘擺的兩極擺動提取力量,這力量正是潘國靈一直堅持的「存在和寫作的力量」。從中學時閱讀的屬靈作家約翰班揚、蘇恩佩、羅鍚為、余達心、許立中,到後期的艾略特、奧登、卡繆、沙特、羅素、尼采等,[33]他願以「寫作做為存在的方式,努力將自己變成自我創造的一個系統,在寫作的終極邊界或自己身體的羊皮紙上,將意義與虛無縫接。」[34]
時間延伸至二零一九年,潘國靈在《明報》世紀版發表〈地下抄寫室〉,主角悠悠回憶七年前遇見了「我城」的「圖書館療養院」、「文字嚮導 /巫師」余心,悠悠作了安娜(Nana)女祭司的承繼者,遙望一眾抄寫員所信奉的女神Nisaba。潘國靈解釋Nana在日文中正是「七」的意思。[35]至此,在兜兜轉轉的來回,從三而一的角色,到一體兩面的我與你,最後還是回到那完全的數字中。他在《寫托邦》接著訴說這一代一代傳承的文學團體,有人抄著愛倫坡的〈大鴉〉,有人抄著中國的詩詞,也有人抄著《百年孤寂》,但「我」(悠悠)卻抄著作家西西〈肥土鎮的故事〉的最後一段:「沒有一個市鎮會永遠繁榮,也沒有一個市鎮會恆久衰落; 人何嘗不是一樣,沒有長久的快樂,也沒有了無盡期的憂傷。」又抄了西西的〈雪髮〉:「....我只知道,把所有的東西放在歲月裡,不久就都隱去了。」
但丁在《神曲》中,寫下刻在地獄之門上的文字:
來者呀,快將一切希望棄揚。
潘國靈全心化為遊幽、悠悠和余心,倒空靈魂,不惜在彼岸和此岸中,黑暗和光明裡建構這龐大的寫托邦,他要與死神對奕,要喚醒沉睡的蒼生。目力所限,本文只能以隻言片語分析《寫托邦》的數字結構和主要角色間跟作者的傳承關係,內容難免乏善可陳。惟願能像鳥兒在沙地上跟作者款款學步,見證著足爪在沙土上隨機留下的楔形符碼,不至隨風而逝。
注:
- 潘國靈,《親密距離》(香港:kubrick,2010年),頁174-175。
蘇苑姍,微批,2016年4月16日,網址: https://paratext.hk/?p=203,瀏覽日期: 2023年12月12日。
勞緯洛,〈洞穴人的鐘擺——談《寫托邦與消失咒》真正的寫作者狀態〉,《文學香港》書評組得獎作品,2019年12月10日。
蔣曉薇,〈撿拾記憶,一個孤讀者的洞穴穿行 〉,2023年5月23日,見虛詞網址:
https://p-articles.com/works/3840.html,後收錄於
洛楓,〈極端生命的殘酷閱讀〉——潘國靈和他的消失角色,見《寫托邦與消失咒》(台北: 聯經出版),頁3-11)
凌逾,〈開拓寫托邦與消失美學〉——論潘國靈首部長篇《寫托邦與消失咒》,見《寫托邦與消失咒》(台北:聯經出版,2016年),頁13-21。
潘國靈,自序,《存在之難》(香港:香港出版社有限公司),另見潘國靈,《離》(台北:聯經出版,2021年),頁14-15。
包括寫婚姻與獨身的〈現代彼得潘的原初情結〉、寫屍體與身體的〈一個少年醫學生的自畫像〉、寫喜劇與悲劇的〈一個少女編劇生的誕生〉及〈悲喜劇場〉。
潘國靈,自序,《七個封印——潘國靈的藝術筆記》(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頁iv-v。
潘國靈:自序,《存在之難》(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
同上。
兩篇文章後收入於《病忘書》,參潘國靈:《病忘書》(香港:指南針集團有限公司,2001年),頁29-66。
潘國靈,《寫托邦與消失咒》(台北:聯經出版,2016年),頁213。
同上。
同上,頁215-217。
潘國靈,《親密距離》(香港:kubrick,2010年),頁7-18。
參潘國靈:《存在之難》(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頁342-346;比較《寫托邦與消失咒》(台北:聯經出版,2016年),頁213-217。
潘國靈,《七個封印——潘國靈的藝術筆記》(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頁24-27。
同註13,頁256。
潘國靈:〈我城05之版本零一〉,載《i-城志》(香港:kubrick,2002年),頁30-31。
同上,頁31-32。
同上,頁40-41。
同上,頁47-48。
同上,頁53-54。
潘國靈,〈自序:我的十年「浮城誌」〉《城市學2:香港文化研究》(香港:kubrick,2007年)
潘國靈:《傷城記》(香港:kubrick,2000年),頁128-141。
潘國靈:《寫托邦與消失咒》(台北:聯經出版,2016年),頁144。
同上,頁330-331。
李零,〈先秦兩漢文字史料中的「巫」,《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頁41-79。
潘國靈:《靜人活物》(台北:聯經出版,2013年)。
同上,頁68-69。
同上,頁72-86。
潘國靈,《七個封印——潘國靈的藝術筆記》(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頁18-23。
同註30,頁134。
潘國靈,〈地下抄寫室〉,收於《離》(台北:聯經出版,2021年),頁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