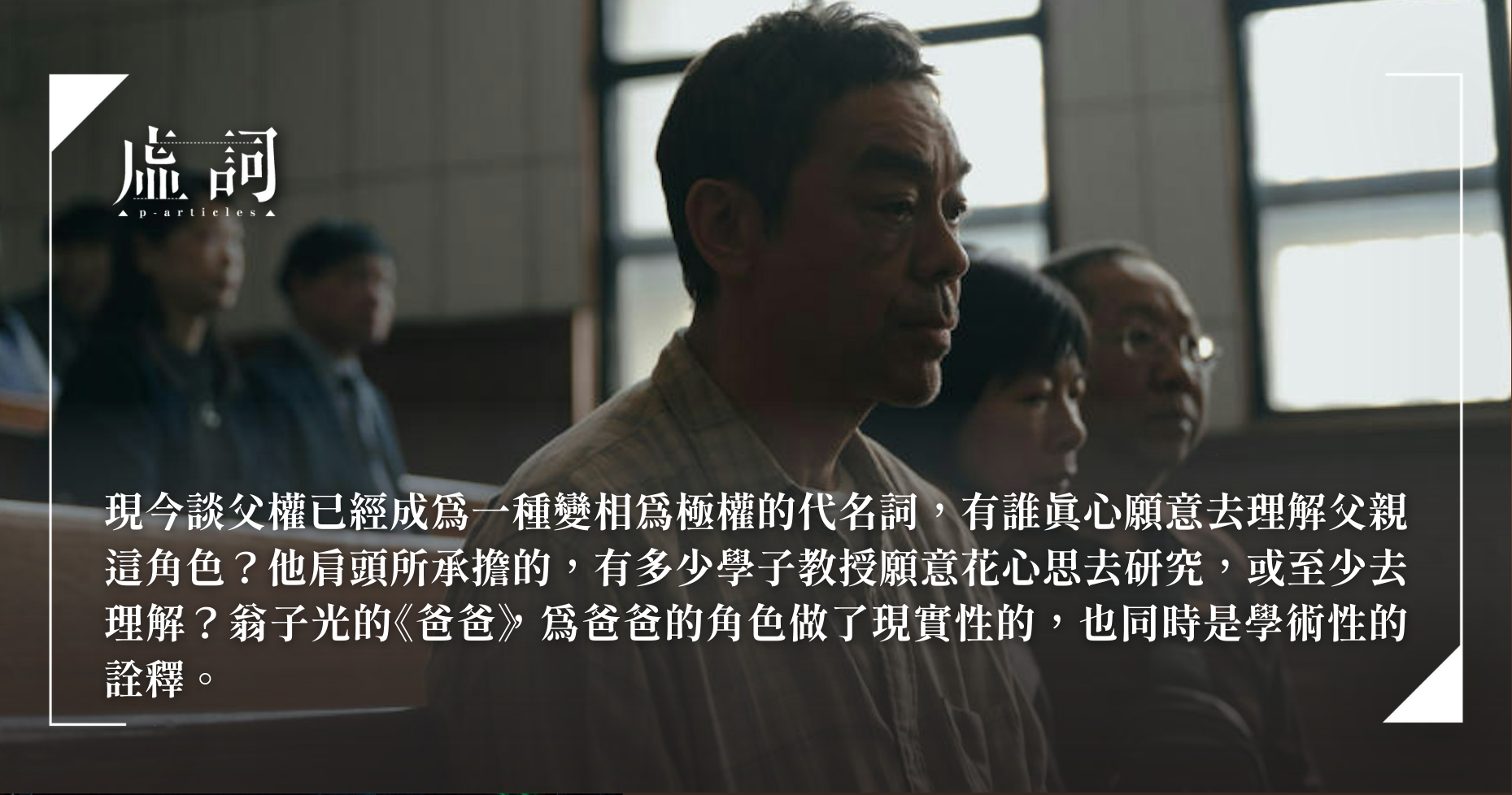我的回憶不是我的——記《爸爸》點滴
「理性觀念的人不是真實的人,因為人的本質原動是非理性的無意識。」
張一賓,《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學映像
平安夜的早上,我看了《爸爸》。並非刻意的想在普天同慶的節日中濫情,只是過去一個月工作至筋疲力竭,想看時已沒多少場次。結果挑了早上一場,場內冷清,旁邊卻正巧坐著年青人,我從劉青雲的演繹中反思如何作一個父親。
剛過的一個多月,在校做著以魯迅為主軸的教學單元,向同學力數父權社會的流毒,並指出國人活在不甘願為奴或欲成奴隸而不得之間的光景中。實情是,現今談父權已經成為一種變相為極權的代名詞,有誰真心願意去理解父親這角色?他肩頭所承擔的,有多少學子教授願意花心思去研究,或至少去理解?翁子光的《爸爸》,為爸爸的角色做了現實性的,也同時是學術性的詮釋。
佛洛伊德認為內隱的無意識才是心理現象的主要部分,意識不過是無意識心理過程的分離部分和外部動作。劉青雲飾演的父親角色永年,在影片未分敍事線以先,率先記下他每天開鋪前的例行公事:把放在桌子上的椅子放下,搬回原處,在門口放半閘下,彎腰走出茶餐廳的門口,抑望那熟悉的清晨天空。這種放下、搬回、走出、無語也無力地望天變成了慘劇後依舊的日常,只是落花依舊,人面全非。
佛洛伊德表明壓抑(Vendrangung/repression)是不被允許的,就如公共場所佇立著「不准吸煙」的牌子,叫你強行壓制你心中某種內在的衝動,把那欲亡轉移,最終淪為無意識。他形容無意識就像一間大屋內的隱閉房間,人諸多的本能也都被壓抑在內同時又被拒諸在外。永年起初以賣雞為業,遇上金燕(谷祖琳飾)後一起經營茶餐廳,其後哥哥、妹妹相繼出生,一家本應平淡快樂地生活下去。沒有解釋,也不能解釋,慘劇頓然而生,一切也只能在壓抑中繼續苟延殘喘。生活依舊,往後的家庭成員敍事,沒有解釋事件的成因,只一同在見證著那根早已繃緊的弦如何日漸斷裂。而讓永年那根弦真正地斷裂,就在他嘗試尋求身體的慰藉。
跟許多奇案獵奇的情節不同,翁子光處理情慾是切合他的敍事線。從永年邂逅金燕到相戀,身體的交纏見證他們的相愛至成家。性是傳宗接代之必要,同時也是愛情的自然流露。當金燕死於親兒之手,身體的需要再也無法滿足,心靈的洞更無法隨年月而癒合。永年過去的賣雞身份與崩潰前的「叫雞」正是語帶相關,他用人民語言罵妓女的不守諾言,恨自己的不懂把持。他扔掉那原是跟家人聯繫的室內無線電話,他跟家人的靈魂之線卻無法摔掉。心靈缺堤只消一瞬間,他終於看見自己身體與心靈的無底洞,他就如魯迅般,半生為家人頂著那暗黑的閘門,他彷彿命定要被壓垮。
人的無意識本能也就成了那個被持續壓抑的狀態,晚年的拉康把他建立的,那個大寫的「我」就像反映著那道老師帶出的壓抑影子。永年過去有對待壓抑之法,或是從一數至廿,或是把它丟在一旁,以為不理會後問題總會迎刃而解;但當發現問題超越理性,同時要求他在一日的八小時內要面、處理甚至解決時,永年發覺過去一切的方法都像行不通。他習慣不麻煩別人,他的工作使命是在最短時間內滿足最多的客人,所以他接受學生們在叫餐時肆意改單;對別人的恩惠,那怕是在程序上、制度下的輔導他也會報以真誠的致謝,但當面對別人指責他在處理兒子問題上sentimental時,他表達出身為父親的情緒與無力反抗。作為一個父親,他不明白的太多。不明白為何兒子會殺害母親和妹妹,不明白他在網絡世界接收了甚麼,他分不清輸入法,更不懂接受在生活中早已習慣的慣性要如何改變。這些在不到八小時之間就把日常生吞、活剝、絞碎,壓抑在一幅一家在海南海灘定格的全家福中。
電影特意拍了木棉樹,也以黑底白字道出木棉的花語是珍惜眼前人,但現實中總有人讓我們既愛又恨,又或是不痛也不恨,對萬事萬物沉默彷彿是父親的宿命。電影有好幾個永年望天的鏡頭,沒有他平常的髒語,是真正的無語問蒼天。要重新走進人稱的凶宅,每天每夜望著那熟悉又陌生的場景,直到那陌生又熟悉的兒子長大,重新再次踏進這道房子,沒有彼此饒恕的濫觴,那種長久的壓抑,隨著成年的厚明(呂爵安飾)在臉龐慢慢滑下的淚,畫面淡出。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是詩人的美化,記憶實際總愛被碾成碎片,埋嵌在那些早被忘記的意識裡。
願我們都學會作個好丈夫,當個好父親,是為佳節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