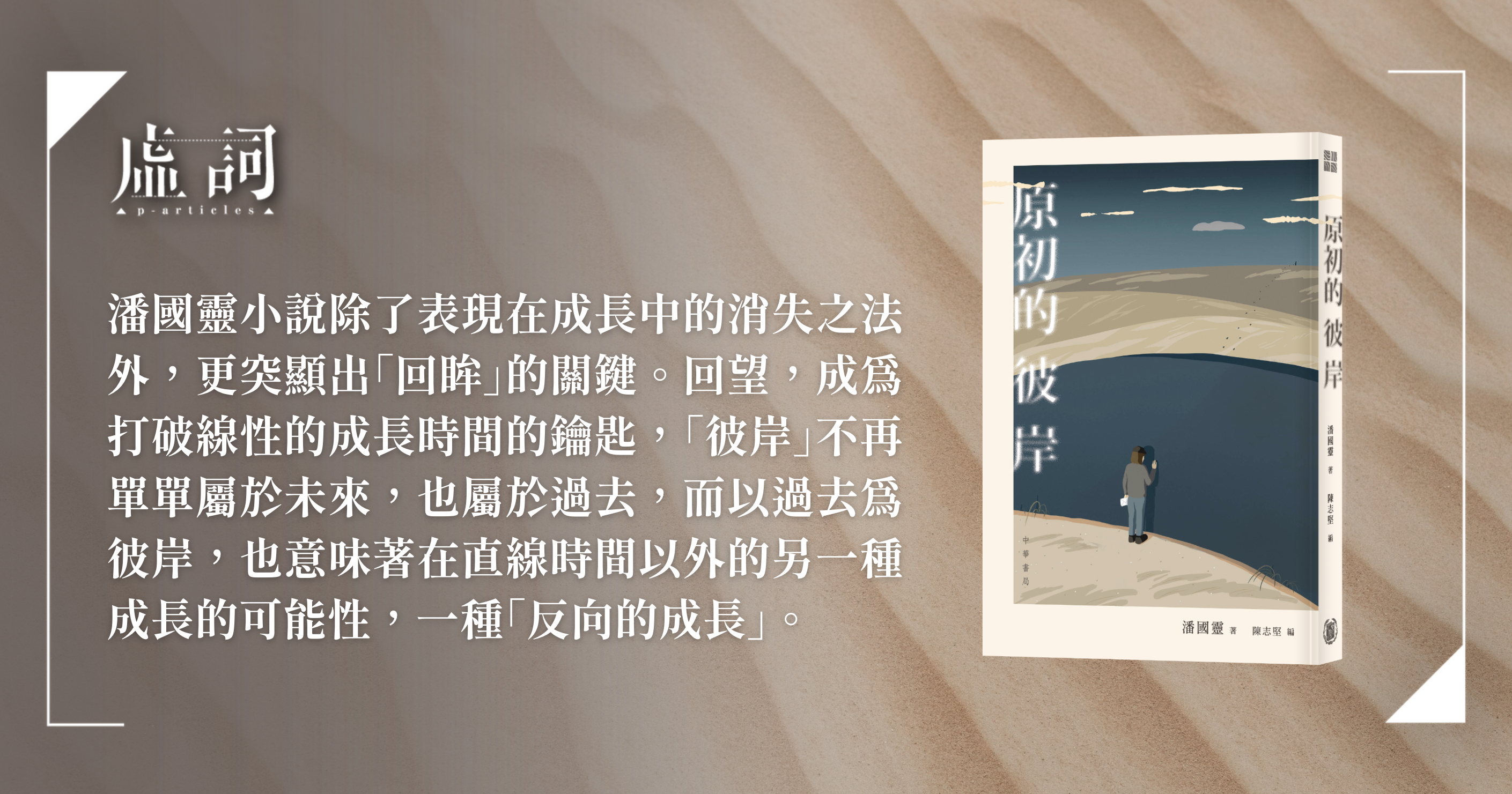懷舊的意義——讀潘國靈《原初的彼岸》
陳志堅先生以「成長」為主題,把作家潘國靈至今創作歷程中的十八篇小說編成一部小說集,以《原初的彼岸》為名向讀者揭示潘氏作品裡其中一個重要的面貌。對於初次接觸潘國靈作品的筆者而言,閱讀這本小說集是一趟不可多得的旅程,也是進入潘國靈小說世界的一次「過渡」,啟程追求在閱讀之中的「成長」。
小說集既以「成長」為題,所收編的作品無疑反映了潘國靈在創作中對相關主題的探討。然而,到底何謂「成長」?一般人說到成長,下意識是以未來的時態來理解,透過想像未來的圖像——尤其是被主流大眾價值所操控的未來——建構出「彼岸」,以此作為生命的驅力,使得自我感受得到生命的變化。他們偶爾用回顧的姿態來看待成長,看似站立在現時的「此岸」,但事實上也同樣以「彼岸」為中心,審視個人生命在過去的進程。因此,成長在一般人的意識中皆是直線的時間進程,生命在其中只有不斷地前進的選擇。然而,編者嘗試以潘國靈的小說來挑戰這種對成長的單一想法。對編者而言,潘國靈小說揭示出另一種成長的姿態:不斷地在「此岸」與「彼岸」、乃至「未來」與「過去」之間循環,以「中途離場」或「消失」的方式在看似無可抗衡的時間之流中重新審視自我。那麼自我在成長中到底如何離場或消失?小說作品揭示首要方法是書寫與閱讀。收錄在集中的第一篇作品〈被背叛的小說〉正是邀請讀者「中途離場」的先聲,小說展現了對直線時間的反抗和對大眾觀念的反諷。這部短篇作品中一心想透過寫小說成名的人物阿心,是一位把目光投向未來彼岸的人,而這彼岸大多更是以他者之目光所建成。敘事者以非常抽離的身份陳述阿心的創作過程,她寫下的片言隻語之間唯一的共通點,是那些內容大部分與她自身的生命及過去無關。在阿心意外墮軌死亡後,傳媒把她的創作點子誤讀為遺言之作,小說更是藉此把大眾觀點的可笑之處展露無遺。在筆者看來,小說提出的觀念正是創作之核心:真正的創作是要回到自身。
不過,回到自己內在只是第一步,畢竟時間的流動並非隨便就能制止,就連本雅明筆下的天使也無法抵禦那股「進步」之風,潘國靈小說中的「畸零遊樂場」只能變成「失樂園」。在另一短篇〈失樂園〉中,這座樂園在城市發展所體現的時間輾壓之下,也只能隨巫女寧默心化成碎片。即或如此,天使仍然回頭面向歷史。潘國靈小說除了表現在成長中的消失之法外,更突顯出「回眸」的關鍵。回望,成為打破線性的成長時間的鑰匙,「彼岸」不再單單屬於未來,也屬於過去,而以過去為彼岸,也意味著在直線時間以外的另一種成長的可能性,一種「反向的成長」。那不僅是一般的回頭看,更是充滿追求的動力。因此,潘國靈在〈失落園〉中為「記憶」與「追憶」兩種概念作劃分:
其實,真正擾人的,不是記憶,是追憶。記憶像一個匣子,你不去碰觸它,它就原封不動在匣兒,只有你刻意追認,才發現當中的虛妄。追憶如撲蝶,撲一隻永遠撲不到的蝴蝶。但也唯有永保與所撲之物的距離,追憶才成其追憶。
然而,若然說追憶過去就是撲一隻永遠撲不到的蝴蝶,人又為何要把處於過去的「原初」當作「彼岸」呢?筆者由此在追憶以外,更想到另一個同樣以過去為標的概念:懷舊。從詞源學來看,「懷舊」原是指「思鄉病」。潘國靈小說充斥着患上「思鄉病」的人:失去「妹妹」的病娃、失去童聲的如嵐、長大後回想起畸零遊樂場的小陀螺、事隔多年後回憶起灣仔波士頓餐廳和紅磚屋的「我」⋯⋯當然,每一位在〈失樂園〉中向記憶之巫寧默心求助的人,都是思鄉病患。之所以是懷舊,乃因這些人物不只是回望過去,更加以認為過去是美好的,構成了前文所謂回到原初的動力。
一般所謂的懷舊都是與空間有關的,但學者周蕾在〈何謂懷舊〉一文中透過分析關錦鵬的電影《胭脂扣》為我們在懷舊的主題上帶來更多的啟發,使我們了解到潘氏小說中的懷舊如何與時間而非單純的空間產生聯繫,其中的關鍵就在於香港的城市變化。香港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的土地發展,香港人對本地空間的感官認知因為不斷的爆破、拆卸、興建而變得支離破碎,因此周蕾指出懷舊不只是空間的缺失,還有時間性的操作:「懷舊之情現在已經完全不同,它的出現不再是因為缺失/失落在空間中被單純投射,而是因為時間性的操控。如果說當過去被搜尋或追憶時,那它也是以壓縮的形式,或者說以時間為幻想物件的形式被搜尋或追憶。」潘國靈的小說固然有以空間為懷舊對象,也有以物件為情感與過去記憶的載體,而說潘國靈小說以時間作為追憶的對象,一方面能把非物質囊括其中,二來也更完整地體現作家對過去生命的思考,切合潘國靈在茲念茲的對「原初」的追求。
那麼,懷舊到底有何意義?周蕾作出的回答是:「懷舊不僅僅是從一個確定的現在朝向某個確定的過去的運動,而是在充滿某個過去的特殊記憶的圖像中尋求自我表達的一種主觀狀態。」要表達自我便先要尋找到屬於自我的聲音,即是發現自我的過程,潘國靈筆下的人物正是一次又一次地經歷這個過程。〈巴士無窗〉的「我」不斷地逃避回憶過去兒時坐舊式巴士的記憶,但是越逃避,那記憶就越清晰,因為那不只是巴士,更是「我」放置在歷史時間中的情感,這懷舊的情感逼使「我」去面對自己的改變,從兒時到當下一刻,或許「我」也如「玻璃窗巴士」一樣,變得越來越「安全」卻也與外在世界越來越疏離。
自我的變化在《原初的彼岸》一書後半部分的數篇小說中就更加明顯。這變化首先體現在自我內在的分裂,卻以整合新的自我作結。無論是在〈信者與不信者之旅〉中踏上那片以資本和消費為地基的「應許之地」的「我」,還是〈面孔我皺褶〉中一邊撫摸情人一邊喃喃自語的「我」,人物在與他者對話的同時,也是向自身發出詰問,在過程中觸及分裂的自己,造就成長的契機,而這主題在小說集中最後一篇作品〈分裂的人〉中更為突出。可是,分裂在潘國靈的這些小說中都只是過程。人的自我在分裂中尋覓、反思,最後能夠把分裂在各處的東西整合成新的生命狀態,發出全新的自我的聲音或形態,那就是〈分裂的人〉結尾「我」在諸般分裂之後得到的領悟:「我與『你』的並存成為一個生命的鐘擺,我以鐘擺的兩極擺動來提取力量——存在的力量。」作者將鐘擺的意象運用得十分巧妙,它既是物質形態上的「一」,同時也因為運動的緣故,化作成不同時空的「二」,而運動的軌跡正是時間之體現。只看到其中一端的鐘擺是一種錯誤理解,正如只看到成長中處於未來時空的「彼岸」也並不是理想的成長,唯有回望過去,在未來與過去中回蕩,才有機會發現更真實的自我。
最後,若說在線性時間中的消失與懷舊是一種從既定秩序中的抽離,筆者認為《原初的彼岸》一書的結構編排恰恰在有意無意中反映出這種抽離的特點,為讀者帶來了有趣的閱讀體驗。編者在書中以小說發表的時間次序來排列書中十八篇作品,這正是一種線性時間的邏輯與形態。然而,在每篇小說之間編者加入了名為「文學詞條」的結構部分,抽取小說中的某一主題加以說明,進一步連繫至潘國靈的其他作品,其中又包括作家的創作手記、小說真跡或其他作品內容的引文等資料。明顯地,編者是想利用這些「文學詞條」及資料產生互文作用,讓讀者對潘國靈的創作有更多了解。但對於讀者的閱讀進程而言,這亦是一種「中途離場」、「消失」甚至是編者引導下的「懷舊」。例如附在〈巴士無窗〉之後的「文學詞條」不只討論〈巴士無窗〉這篇小說,更提及在小說集中較前位置的〈距離〉。若果讀者依循提示再次翻閱前面的小說,那不也是對潘氏小說的「追憶」的方式嗎?而在這個懸置了線性時間的過程中,讀者在編者引介下對潘國靈作品的認識也會有所深化。當然,讀過「文學詞條」後若有不盡明白的地方,也亦是一種思考上受到的誘導。這種結構效果或許大多只是出於筆者自身的閱讀體驗,但背後也是基於編者的付出與用心,使人在閱讀潘國靈作品的過程中有所「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