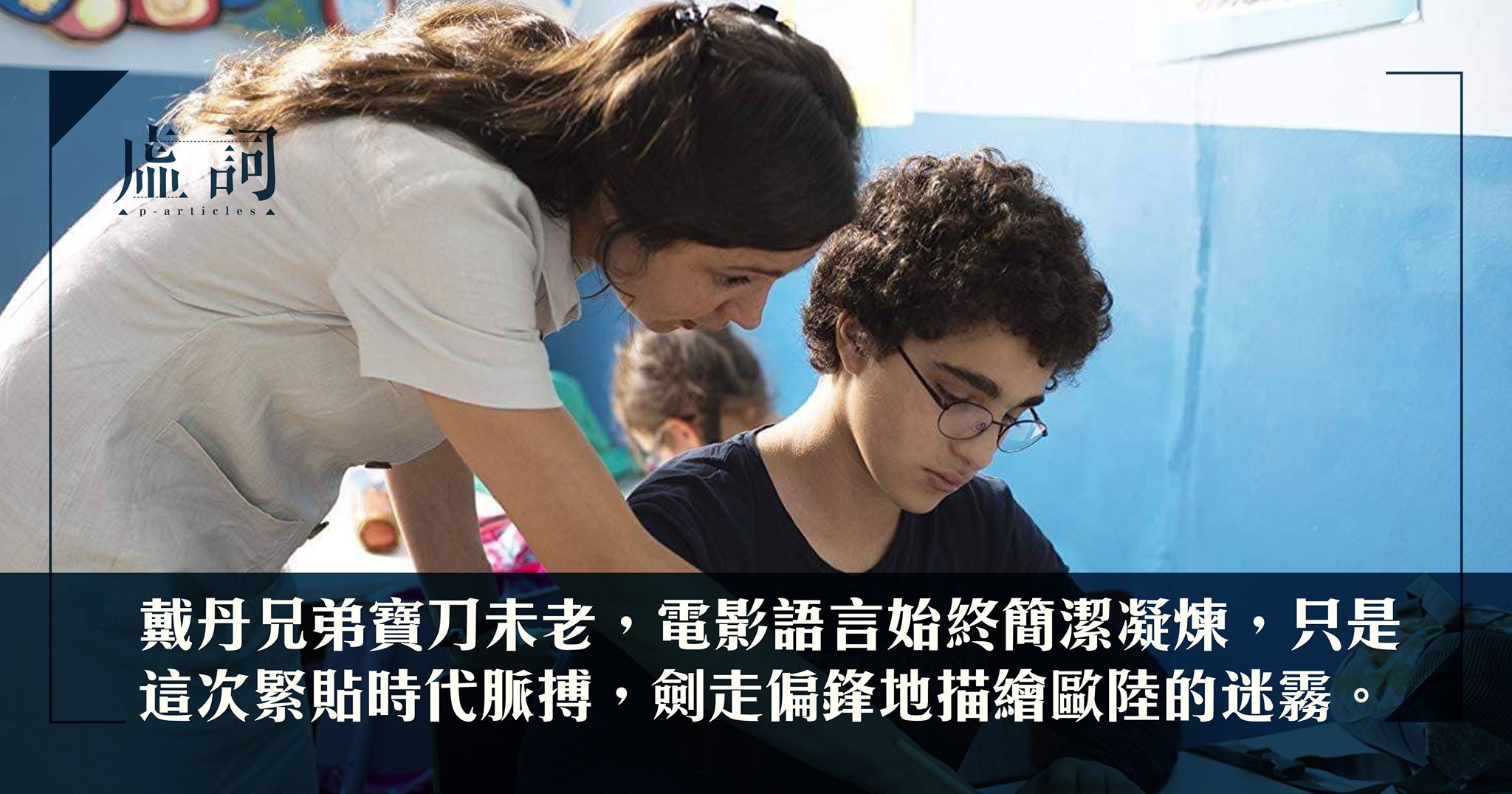學姊,母湯喔——《返校》的兩難
《返校》改編成電影後,編導的方向似乎有意比遊戲更明顯直接地,以台灣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為主題,但陳子雲覺得它始終是商業電影,把白色恐怖收縮成,學姊的心理衝突的結果,對《返校》戒嚴時期的刻劃不滿意,也不滿足。 (閱讀更多)
《「島物詩游」——也斯進劇場》︰依靠想像力來連結人與物
劇評 | by 肥力 | 2019-12-16
進劇場完全把握了這種溫柔,令也斯的多個文字作品變成視覺、聲音及文字拼湊,再在劇場中聚集。 (閱讀更多)
那個時代的流行曲,那個時代的黎小田
比如說,1981年麗的時期的武俠劇《蕩寇誌》的主題曲《你心澈悟時》,黎小田是用兩個短音結尾,甚是奇特,而詞人因應這特點,填了「可有仇人,背後……下手」!配合得妙到毫巔。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