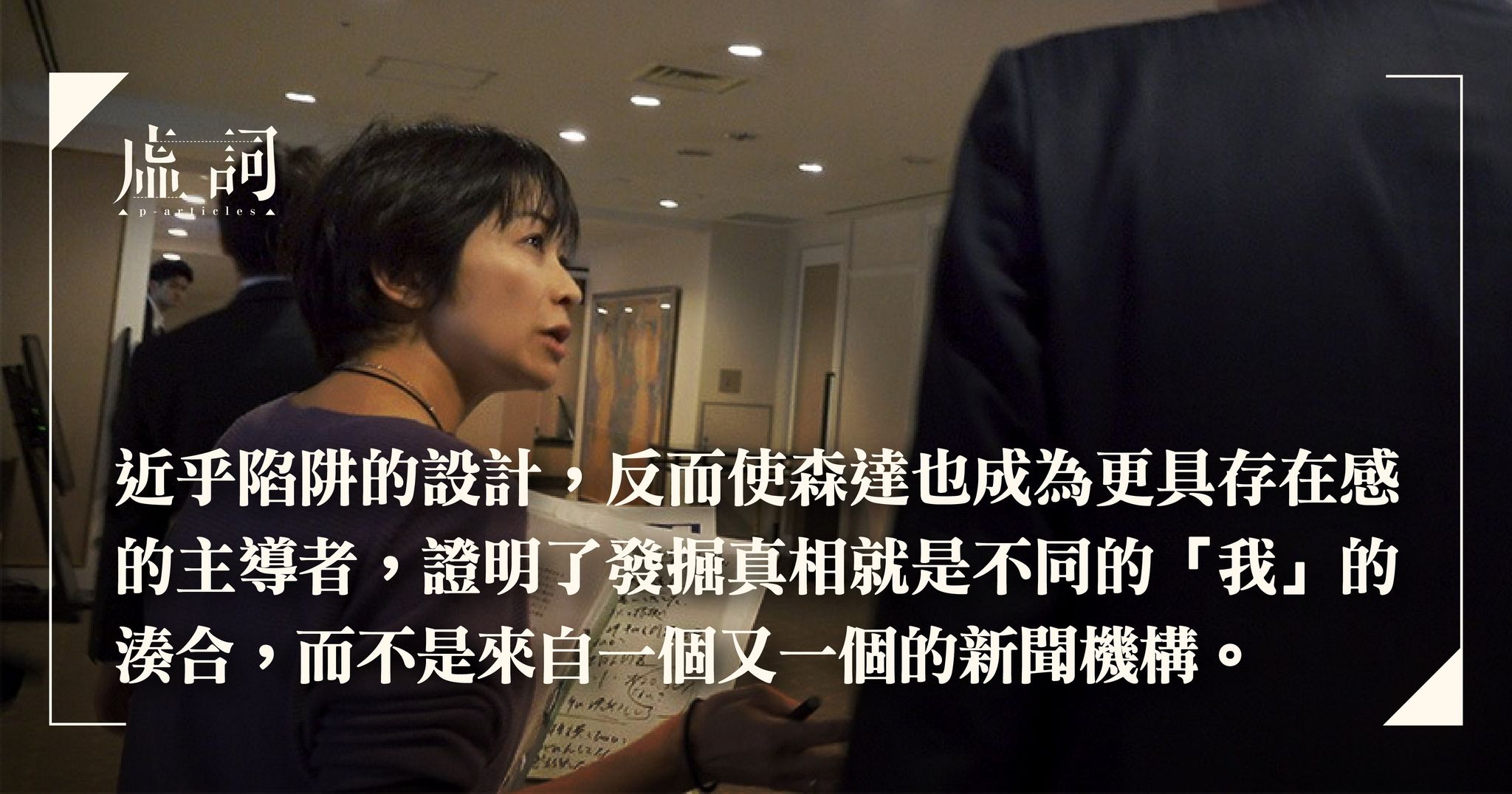《我,直擊真相》:日本新聞界的逆流而上
由傳統冷傳媒到排山倒海的網上平台,一眾新聞從業員和老闆的逐利特徵始終不變,透過各種喧染、誤導甚至造假,報紙的字裏行間進行了無數次的人格謀殺。作為長年以揭穿新聞及權貴醜態著名的紀錄片導演,森達也於新作《我,直擊真相》中緊隨另一位明星記者(望月衣塑子)走訪各個政府及記者機構,誓要以公民知情權反擊不同公權力導致的失當行為。
近日才以健康理由請辭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剛剛宣布由《我》擁有大量戲份,本為內閣官房長官的菅義偉接任。近年來自民黨手握大權的一面倒局面,導致眾多極受爭議的法案或政策浮上水面,如修改憲法第九條(發動戰爭權)、大規模量化寬鬆、僵化的福利制度、檢討國民教育內容等。作為在任時間最長的日本首相,其最大醜聞莫過於望月揭發的性侵案(伊藤詩織)和購地特權弊案。縱使安倍近日辭任首相,讓被譽為「農民之子」的菅義偉接任,乃是以菁英階層壟斷的日本政治環境的特例。事實上,即使安倍晉三卸任首相一職,但內閣成員仍然是以安倍的心腹為主,可見安倍仍存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如此一來,面對講究絕對階級觀念和父權的日本職場,即使望月敢言和堅持不懈的作風惠及小眾,卻仍要蒙受不少網民和同儕的惡言和阻撓。
打從一鳴驚人的首作《我在真理教的日子》(1998),森達也宛如成為了日本的米高摩亞( Michael Moore)。雖然二人均受過謾駡和打壓,不同於略為犬儒和側重譏諷的摩亞,即使語氣總是不卑不亢,森達也大多採取的卻是直線抽擊的強硬態度,經由他的尖鋭提問,受訪者的尷尬失色往往形成了另類喜感。如此一來,《我》可謂承繼了森達也的一貫風格。片名的「我」指出了兩個人物,其中一位是作為故事主人翁的望月,而另一位則是森達也本人,透過紀實拍攝一名記者的採訪過程,森達也拍下的不僅一部具真實故事肌理的電影,同時也是一則又一則的二次採訪的紀錄。
可是,作為一位素來介入感強烈的紀錄片導演,森達也於《我》的角色及其處理,因為強勢(性格)的望月,反而變得微妙。過去的森達也主導並兼任調查者和敍事者的身分,以不卑不亢的語調不斷詢問、質疑當事人,是森達也呈現真相,甚至撕破假面具的手法。可是,《我》 的故事主人翁本來就是以此為業,她不畏打壓或各種奸詐手段(假新聞、刻意干擾視線的數據)已經站在森達也之前。反之,他轉換成從旁觀察的紀錄者,並適時進行自己的反抗行動。比方說,片中揭發傳媒抹黑「森友學園」的涉事者,並保存安倍晉三的聲譽。訪問之初,受訪者固然對首相及其夫人駡得體無完膚,盡訴自己的冤情。此時,森達也在旁靜觀其行,仔細分析他們的闡述。正當觀眾甚至當事人以為已經得到森達也和望月的信任,森達也才一語中的指出他們的思想盲點(保守派 / 自由派),甚至配上小學國民教育的片段(篡改侵華歷史)。近乎陷阱的設計,反而使森達也(敍事者)成為更具存在感的主導者,證明了發掘真相就是不同的「我」的湊合,而不是來自一個又一個的新聞機構。
再者,森達也的取向亦與過往作品有所不同。《真》系列側重於解構惡名昭彰的真理教,透過紀錄信徒各種與常人無異的日常行徑和處世哲學,一方面成功顛覆了外界對於這些「聞風喪膽」之徒的認知,另一方面描繪了傳媒為求收益而瞞報假作的無恥行為。以作曲家佐村河內守的「請槍」醜聞為題的《貝多芬的謊言》(2016)更是再進一步。羅生門般的觀點使人無從入信,即使最後二十分鐘看似終揭謎底,但旋即再次陷入無限懷疑。如此一來,《我》可視為森達也面對相近命題時,再度深化的主題談討。從否定原有的傳統第四權的可信性(《真》) ,到展現人性和事實的多樣性(《貝》),《我》刻劃的是「公私不分」的人物形象,除了展示真相及其威力,也是呈現了追尋真相的過程。
處於森達也鏡頭下的人物,他們深受外界各種誣陷或評擊而受傷,同時卻「如常」地生活。雖然望月特立獨行的風格使她成為有趣的拍攝對象,但導演專注的不是各個事件的起承轉合,或是調查進度,而是生以為人的勇氣、堅毅和生存狀態。一方面,望月窮追不捨的拷問菅義偉和安倍晉三,連番揭發這些政治人物的醜聞。另一方面,她急忙地致電關懷兒子,為排山倒海的文件而不免擠壓出一道魚尾紋,狼似虎地鯨吞便當,一堆的死亡恐嚇信件。森達也甚至用上分割畫面(Split Screen)堆砌望月面對不同的壓力。再者,一段平行剪接沉實交代導演和記者被公權力打壓的經過,由嘗試理論到強行通過,鏡頭直白而赤裸地顯出公權力的僵化而冷待人性的特點,即使二人試圖以道理(和平手段)解決,最後仍不得不使用強硬手段完成記者的職責。電影末段上演一段充滿中二味道的動畫處理,縱然此舉或會破壞了原有的寫實感,但這也可視作面對不可能打破的權力結構,幻想與熱血才是唯一出路的譏諷橋段。如此一來,《我》 編織了公共和私人經驗之間密不可分的人生,既為勇武,亦有脆弱,都是令人疲憊的。用上簡潔的電影語言刻劃人物的形象,不難發現森達也的處理是非常直接、赤祼甚至暴烈的。可是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反而呈現了極致的寫實感,繼而更有利於揭取真實(慾望)或是把玩真實的效果。或許,在森達也眼中,這二十年的創作過程未有為他帶來擊破假面具的信心,反而積累更多深層的焦慮和無奈。
在講究個人表達權益的民主社會中,「我」卻往往是被主流意見淹沒甚至犧牲的對象。當鏡頭從一顆頭顱慢慢拉開,讓觀眾看到當年巴黎解放後的另一種暴行,也就是群體施於獨立思考者的暴力。在互聯網統合一切輿論風向的時局,森達也顯然心存日積月累的焦慮。面對這個看似包容一切言論,卻是暗藏各種演算法、自我審查、執法干預的公共空間,所謂的言論自由弔詭地成為操控人民思想的工具。當聲名狼籍的「稜鏡計劃」(PRISM)被揭,人民卻早已受夠黑暗的政治操作,寧可掩耳暗忖知情權的無能。
或許面對淹沒人性光輝的輿論與政治大氣候中,「獨立思考」是森達也最後的信仰。
(標題為編輯擬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