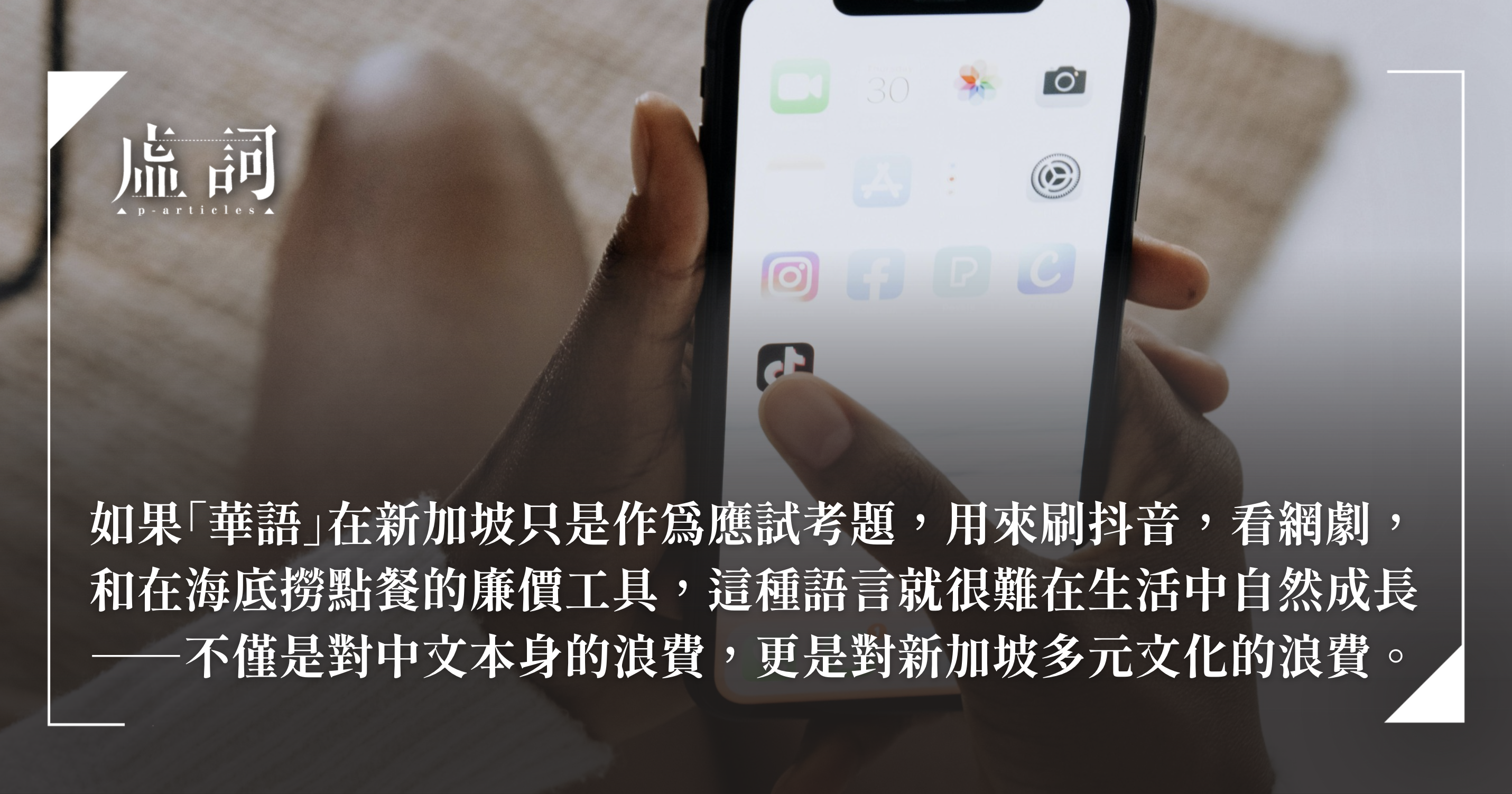殖民地的語言
離開曾參加考試培訓的香港,後在北美學習生活近一載,前年我來到了熱帶的新加坡。要說這些地方有甚麼特點,我的愛爾蘭朋友曾打趣說:「你好像一直在大英帝國的範圍內轉圈。」這些地方都曾是英吉利的殖民地,但卻又各自不同。其中能觀察到的最有趣,實亦重要的現象是「殖民地的語言」。
2014年,美籍華人藝術家及作家陳丹青曾到訪新加坡時作過「母語與母國」為主題的演講。其中最值得關注的論點是「一切語言問題都是政治問題」。這並非甚麼全新的說辭,無論是拉康,抑或福柯,早就意識到我們的語言,包括我們如何組織語言,並在與人交往中使用語言,哪些語言被接受,哪些不被接受,其實都是政治對於知識的結構性影響。這令人思考,對於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的語言來說:母語是甚麼?母國又是甚麼?也許對於寫作「星洲散記」的魯白野來說,這個「母國」既非英國,亦非中國,更不是尚未成立的「新加坡共和國」,卻是一種後殖民地特有的迷失。
實際上,關於「母語」和「母國」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以大陸作為地理和文化中心來思考,而一切座標都淪為與「中心」的相對關係。但殖民地的語言,也許用另一種思考方式來看更為恰當。這種思考方式便是英國社會學家斯圖亞特霍爾所提出的「流散(Diaspora)」系統。他用非洲後裔的流散人群作為主例,提出被殖民主義強行切斷與「母國」或「母語」聯繫的牙買加或海地文化,必須以一種混合(hyrbrid)的,永遠在不斷生成(becoming)的流動濾鏡,來看待殖民地的語言和藝術—即存在(being)就是流動(becoming)。這一框架創新於其靈活性,並將「歷史性的剝奪(Historical Deprivation)」,而非心繫「母國」的想像紐帶,作為語言生成和發展的基礎。但對於以華人為主體的香港和新加坡來說,無論是陳丹青,抑或是霍爾的視角,都無法對語言問題提出完整和連貫的解釋。
生活在中英雜揉的新加坡,也許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待「殖民地的語言問題」才是一種既靈活,亦非離地的方法。對於新加坡的華語文學來說,台灣作家張紫蘭有一句評價:「看那個地區的中文,始終不能透徹,也不能很美。我在想為甚麼他們普遍這麼『不熟悉』?是因為他們太熟練他們的方言,而有所阻礙?」,而她也認為:「像這樣趨勢,要出現一個很強的哲學詩人,要很努力!」概括來看,實際上她在說:新加坡的華語,也許目前仍欠缺將複雜如哲學的思考轉化為語言的能力。
但是相比同為前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新加坡確實在華語文學上,繼英培安先生的去世後,本地再少見任何牽涉複雜社會問題及思考的作品。這讓人想到了陳丹青在批評中國大陸文學時,引用一位瑞典漢學家,令人不置可否的觀點:「中國大陸文學的問題,來源於其中文的缺陷。」其實很難想像語言作為一個非實體的文化元素和功能,會像身體一樣具有某種「缺陷」,但這個隱喻中更重要的是文學和語言之間的聯繫。一個地區的文學若要發展,這個地區的語言一定是最重要的基礎。那麼,新加坡的語言出了甚麼問題?
要說清楚語言的問題,不得不探究語言的實質。從宏觀來說,語言的起源尚不明晰。對於馬克思來說,語言來自勞動。就像音樂起源於原始人的勞動號子,語言可能起源於勞動本身。而對於「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來說,語言則起源於人類想要描述抽象事物的努力,來源於某種討論「謠言(gossip)」的文化。但無論如何,語言來自於生活本身的深化和擴展。而從微觀的角度來說,新加坡和香港的語言,都根植於商業活動,這和香港和新加坡同作為亞洲港口城市的歷史和身份息息相關。
作為新加坡象徵的「新式語言」,即「新式中文」或「新式英文(Singlish)」都具有這樣的商業特質。新式英文曾被一位外派至新加坡的美國記者如此形容:用「Can(可以)」和「Cannot(不行)」替代「Yes/No」的新式英文,可能是這個地球上最具有效率的英文。這也許有誇張的成分,但不可否認的是,新加坡的語言在今天來看,形成了一種能在科技和商業領域快速流通,清晰表意的語言模式。對於一個港口城市來說,這是極其有利的。香港的文化表達也帶有類似的特徵。對於一個被作家陳冠中稱為「職業經理人」的城市,清晰和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但對於新加坡來說,這種清晰和效率也使語言長期漂浮在「功能性」的表層,而缺乏作為藝術、哲學、文學載體的深度。這並非說新加坡的語言並非完全無法成為這些門類的載體,畢竟清晰和效率對於這三者同樣重要;或者說:新加坡的語言也並非不能以更靠近中文和英文任一端的方式, 來獲得主流中文或英文本身的承載力。但問題仍然明顯:即商業的語言,要向文學的語言轉化,這其中需要許多的沈澱和智慧。另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是:同為前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的語言,至少在中文的層面,為何比新加坡顯得更加豐富而有力?
如果回到「語言來自生活」的觀點,香港和新加坡同為港口城市,同為「巨大的旅館」,但在生活的層面卻又迥然不同。殖民地港口城市的特點是:生活(life-ability)性往往不強,這和基於基礎設施的宜居性(live-ability)不同,因為作為殖民地帝國的「轉運港」,人口總在流動,語言也隨之流動,這種流動雖然會帶來語言發展同樣必須的多樣性,但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卻常常因為這種流動而受限。「沒有人想留下,或沒必要留下,畢竟生活在別處」。這種受限往往使生活成為一種「走馬觀花」的表演,而非「腳踏實地」的感受。這個問題在新加坡成為自治獨立的政治實體後有所好轉,但並沒有完全解決。這一方面是由於新加坡的生活缺乏一種自然的力量,並長期處於一種政府調控的非自然狀態,使得生活的拓展常常在狹窄的有限時空內進行,影響了生活本身,及語言本身的延展性。這當然也有身份問題,即華盛頓郵報中曾提到的「新加坡作為世界都市(metropolis/city)和作為獨立城邦(city-state/country)的必然矛盾」。這在新加坡被迫獨立,和馬來西亞切斷了地理和文化上的直接聯繫後,又在六十年代「內部安全」行動中切斷了華人和中華文化圈的聯繫後,顯得尤為明顯—即生活可在別處,可在馬來腹地,可在中國海岸,再移植來此的可能性消失了。另一方面,語言賴以發展的多樣性也常常處在被嚴密調控的狀態,即不同種族和文化間可供交流的元素是有限的,而這種交流的模式也同樣有限。最後,當然也有更明顯的一些因素,即李光耀從70年代所推行的「雙語」運動,不僅使得本土居民陷入一種對中英文雙重陌生的尷尬狀態;這一運動中的「講華語」部分,同樣抹滅了中文方言,如粵語,閩南語,和客家話在新加坡語言中的豐富角色。新加坡音樂人梁文福曾被封禁的歌曲「麻雀銜竹枝」便涉及到了這其中因為方言而引發的政治問題。
但有趣的是,為甚麼香港的中文卻發展出了獨具特色,且頗具深度及廣度的成熟型態?難道香港不是流動的港口嗎?當然,香港是和新加坡同樣繁忙的港口,是錯過無數個「蘇麗珍」的46號房間,是見到無數個「白玲」的永動列車。而新加坡也是楊修華眼中的「幻土」,是巫俊峰鏡頭裡的「沙城」。但是孕育了陳冠中、劉以鬯、張愛玲等眾多作家,王家衛、杜琪峰、許鞍華等電影導演,及無數思考者的香港,且不論曾冠絕亞洲的商業藝術成就,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與英文為主,中文為輔的新加坡不同,香港整體是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雖然這兩者同樣因為殖民歷史,而在商業、法律、科技等公共活動中,選擇以英文作為工作語言。但從生活的層面來看,香港雖然顯得更加混亂,但也更具生氣。這是不同於新加坡在建國後的管理模式所造成的結果。再加上香港和內地,特別是閩越地區從未真正中斷的地理和文化聯繫,以及50年代大量的知識分子遷入,香港的生活,雖然依然浮躁,卻恆以自然的狀態,在深度上不斷探索著本土的身份,思索本土的問題,在廣度上則同樣聯繫著大陸和西方的遼闊世界。這意味著,香港的中文不僅有新加坡所專注的商業性,也具有新加坡所缺乏的其他維度,並將商業中的邏輯,效率,世界性及契約精神,融入到其他維度中。
在這種情況下,紫蘭所說的「努力」反而是無用的,而「無為」,即權力容忍新加坡的語言以自然的狀態繼續發展,其中縱使出現問題,但卻能產生更有機,也更具吸引力的語言藝術。但如果「華語」在新加坡只是作為應試考題,用來刷抖音,看網劇,和在海底撈點餐的廉價工具,這種語言就很難在生活中自然成長——不僅是對中文本身的浪費,更是對新加坡多元文化的浪費。就像新加坡作家雪裏安喬治所說:文化多元性是一種天賦(gift),而不是一種「努力」的必然結果。
「語言的敗壞到底是政治和經濟的原因引起的,」喬治奧威爾在「政治與英語」一文中如是說;他接著說,如果我們能在語言的問題上實現某種改進,一種基於自然法則的改進,則有助於將語言的使用者「從正統政治的荒謬愚蠢中解放出來」。殖民地的語言,在上世紀的「反殖民運動」中扮演了解放性的角色;但在如今,我們更不該放棄思考語言超越其工具性的其他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