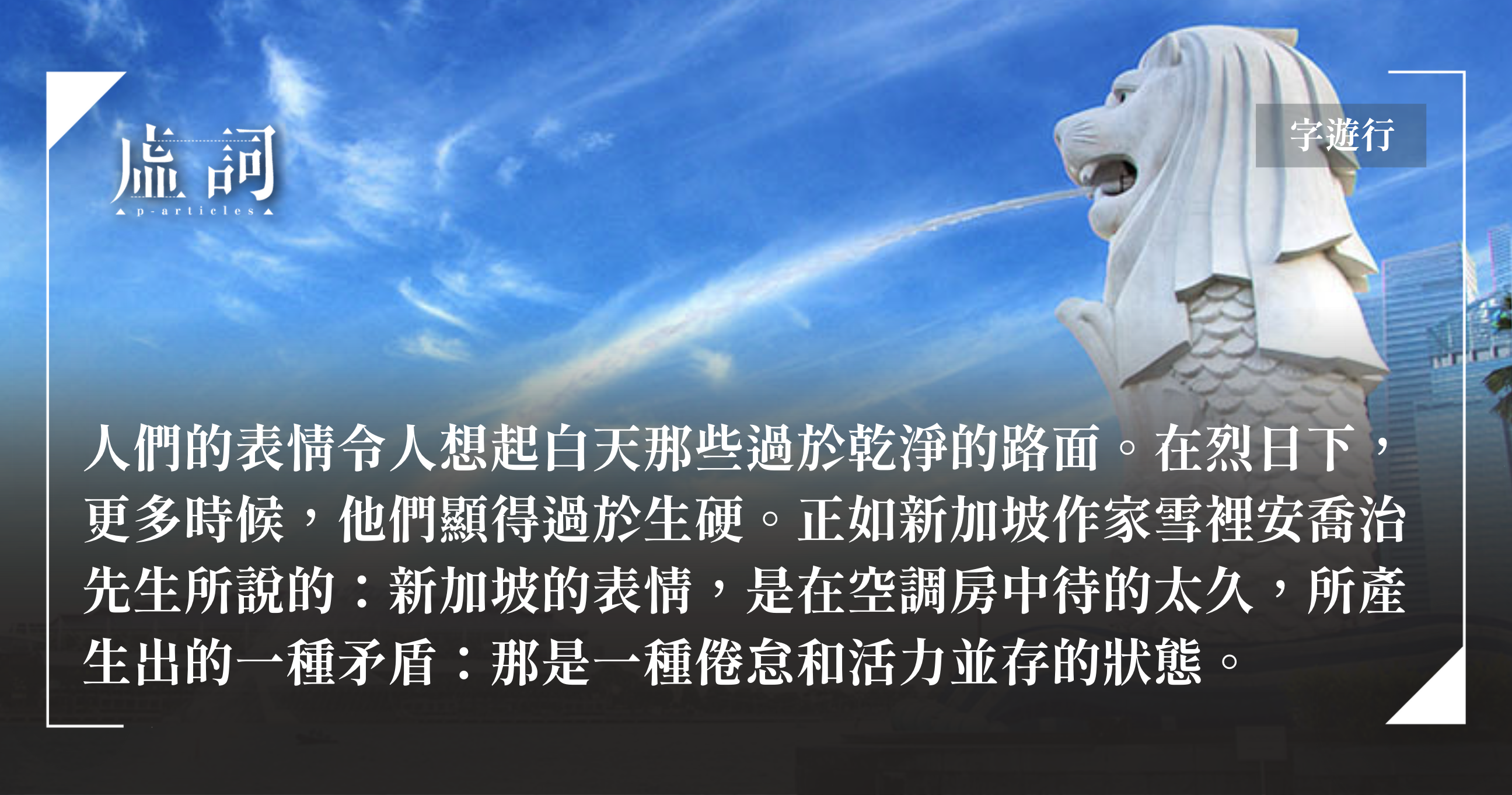【字遊行.新加坡】單簧管的旅行
從文禮站出發,去聽下半年最後一場單簧管音樂會。莫札特對單簧管的喜愛來自於其空靈的高音,於是在去世前創作了最後的單簧管協奏曲。在萊佛士對岸的維多利亞音樂廳,在一個隔絕了熱帶的溫度,卻無法隔絕噪音的獨特場所,來自愛爾蘭的朱利安先生的吹奏像一縷青煙,穿透了南洋厚重的雲層,和那些與植被不太協調的大理石牆面。再回去的時候,戴上耳機——須再聽勃拉姆斯,絕不可用薩蒂去緩和巨大的溫差;最後薩蒂也顯單薄,只能播放南洋小調,捱過從出口至車站的距離。穿過壓滿了橋面的遊客;在另一頭避開晚歸的「サラリーマン(工薪族)」,聞著有些鹹味的河水,便從萊福士坊鑽入了一個不眠的地下洞穴——新加坡的地鐵是如此的龐大,像細密的血管一般撐開了一座本就狹小的島嶼。那個經典的問題是:是這些道路造就了新加坡,還是新加坡造就了這些道路?
在回程的地鐵上,一切重歸寂靜。總有剛上車的乘客仍興奮地交談,但很快在空調的作用下放慢語速,或降低了音量。最後便都沉默,看向手機或窗外。東西線的地鐵丈量著新加坡的寬度,它曾是精英們的大膽設計,如今也丈量著普通人生活的維度。韓國導演許哲先生曾對我說:新加坡雖然深處熱帶,但比起它的潮濕,它更顯得「乾燥」。 這種「乾燥」是一種匱乏,對於豐富的匱乏,對於混亂的渴望。他也曾用舊金山的中國城類比新加坡,而對於我來說,舊金山氣候的乾燥和其文化中的「潮濕」正好形成對比,雖然這種「潮濕」正在灣區不可避免地逝去。
人們的表情令人想起白天那些過於乾淨的路面。在烈日下,更多時候,他們顯得過於生硬。準確來說,是在空調裡的烈日下,正如新加坡作家雪裡安喬治先生所說的:新加坡的表情,是在空調房中待的太久,所產生出的一種矛盾:那是一種倦怠和活力並存的狀態。此時的車廂裡,一位留著70年代髮型的安哥正陷入了睡眠,他兩腿間的吉他正滑向列車的反向。他的裝束令人想起南洋大學的學生,過於寬大的衣領一直延伸到一個深深的袖口,那裡不是香菸,便是變調夾。他們曾作為新加坡的高音,在主流的C調中,總會奏起A調的小號。但和單簧管比起來,他們的小號過於悲壯了。彷彿列車的低音仍在持續。在他的身邊,有一位工人模樣的印度青年,他黑色被汗水浸濕的襯衫上,寫著「Born Lucky (生來幸運)」的字樣。他也許也曾在羅釐車「後座」的熱風中想起遠在德里的兄弟;亦或許他就是「生來幸運」的一群,可以用他腳下的筆電穿梭於新加坡的兩端。
這讓人想到了這座移民城市的過去。這是一座極其「幸運」的城市,坐擁深水港,同時面向三片大陸;但這種幸運卻一直被從李光耀時代就不斷塑造的「危機感」所包圍——在缺乏資源,強鄰環伺的情況下,如何去建設一個新的城邦?這種「危機感」似乎仍伴隨著新加坡人的生活,雖然他們已經擁有了更多元的選擇:這種選擇是物質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但與日本不同,這種「危機感」還伴隨著對於自我身分的模糊和焦慮。
簡莫里斯筆下的新加坡,如同此時的鏡像,一切都類似,一切也都相反。舊的帝國遠去不久,新的帝國已經抵達了繁忙的港口。那些穿戴整齊的英國紳士們,如今被更多的時尚所取代。雖然更加潦草,但也更加隨意。舊帝國的影子頑強地,或著說,有些刻意地留在了新加坡的語言中,獨屬於這裡的新式英文,總讓倫敦的語言學家們爭吵不休:這是英文方言,還是另一門語言?新加坡人毫不在意,因為如同他們的咖啡,他們可以在不同的配比中自由切換,但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於此同時,新的帝國已迫不及待地伸出了它的觸角,比起影子的存在,他們更加張揚地舉起了新的招牌,說起了新的語言,留下了新的,但有些令人不安的痕跡。比起在英培安先生的「騷動」中曾遙望,同情,而最終逃離的帝國,這一切顯得如此熟悉,但也如此陌生。比起那些有些破敗的福建會館和佛道廟宇,新的帝國代表著更高的建築,更龐雜的口音,以及更好喝的奶茶。而在李光耀先生的回憶錄中,這位柏拉圖筆下的哲人王,如同先知一般預料了新帝國的崛起,並提前準備了新加坡口音的華文,儘管生澀卻有效地重建起溝通的橋樑。
在中英文夾雜的燈火中,電車駛入了女皇鎮(Queenstown)。一位穿著錦色旗袍的華人女性緩緩走入身後的車廂。與其他的乘客相比,她顯得更加從容,也更加疲憊。在一個靠窗的粉色座位上坐下後,她拿出了一個畫著魚尾獅的隨身鏡,並開始整理妝容。雖然已入中年,但有些不合時宜的短髮下,她的眼神仍是靈動的,甚至有些可愛;在添補了右眉和唇沿的光澤後,她反覆檢查多次,然後迅速露出了一絲俏皮的笑容。她也許仍要去參加深夜的聚會;或是回到家中,以這樣的姿態擁抱家人。在她的身後,皇后鎮也顯得活潑起來,在駛入下一站的黑暗前,最後閃爍一些年輕的光芒。在這位女士的童年,在電車還無法到達這裡的時候,那些慶祝女王登基的人群,也許也是這樣的年輕,身著華麗地湧入了這一片曾是戰場,但也歌舞不輟的小鎮。她要在裕廊下車,而我在之後的三站:文禮。
我整理好被空調吹乾的衣物,重新匯入新的人群。我想到在維多利亞廳的觀眾,還有在萊佛士坊上車的乘客,在廣播中報站的司機,也有我自己——我們都在這個島嶼上尋找一個身份,一個如同克爾凱郭爾所說的,一個「脫離了時代,歷史,和種族」的身份,這是比那些游離的,或是強加的,被印刷在海報上的形象,更加困難但也緊迫的願望。他說:聯合、超越起這樣的個體身份才能塑造一個真正的集體身份。對於一個過於年輕的國家來說,這種願望是奢侈的,但也呼應著某種潛藏於斯的巨大力量。這種力量將在有些生硬的國慶氣氛中,不斷塑造一個新的文化。而這種自然生成的力量,也許才會為危機中的人們,提供更持久也更親密的依靠。這讓人想到了艾默森在19世紀初的波士頓對於美國精神的呼喚:脫離英國的清教徒傳統後,我們需要塑造一個怎樣美國的精神?而魚尾獅的靈魂,你又在哪裡?這也許是過於龐大的命題,對於總被時代牽引的新加坡人來說,今晚和明天的問題才能提供精神的動力。
我隨著人流,走下了車站的階梯。此時的文禮,不論是新帝國的奶茶店,還是舊帝國的啤酒吧,都已經按時關門。我只好走入了一家有些諷刺的餐館,而它的名字是“Just Eat (快吃吧!)” 在咖喱粉和羅勒葉的映襯下,我和所有晚歸的顧客們一齊為新加坡舉杯,因為電視中仍播放著大運會的轉播。而我拿著檸檬茶,嘴裡正嚼著一些碳水,不妨大膽說,碳水才是今晚的正題:它是滷麵,是咖哩飯,是毫不吝嗇皮蛋的肉粥………此時窗外的街頭藝人吹起了「魔笛」,仔細聽,竟是單簧管的聲音。與莫札特不同,我的腦海中只有一個想法 — 「In Singapore, just eat! (在新加坡,快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