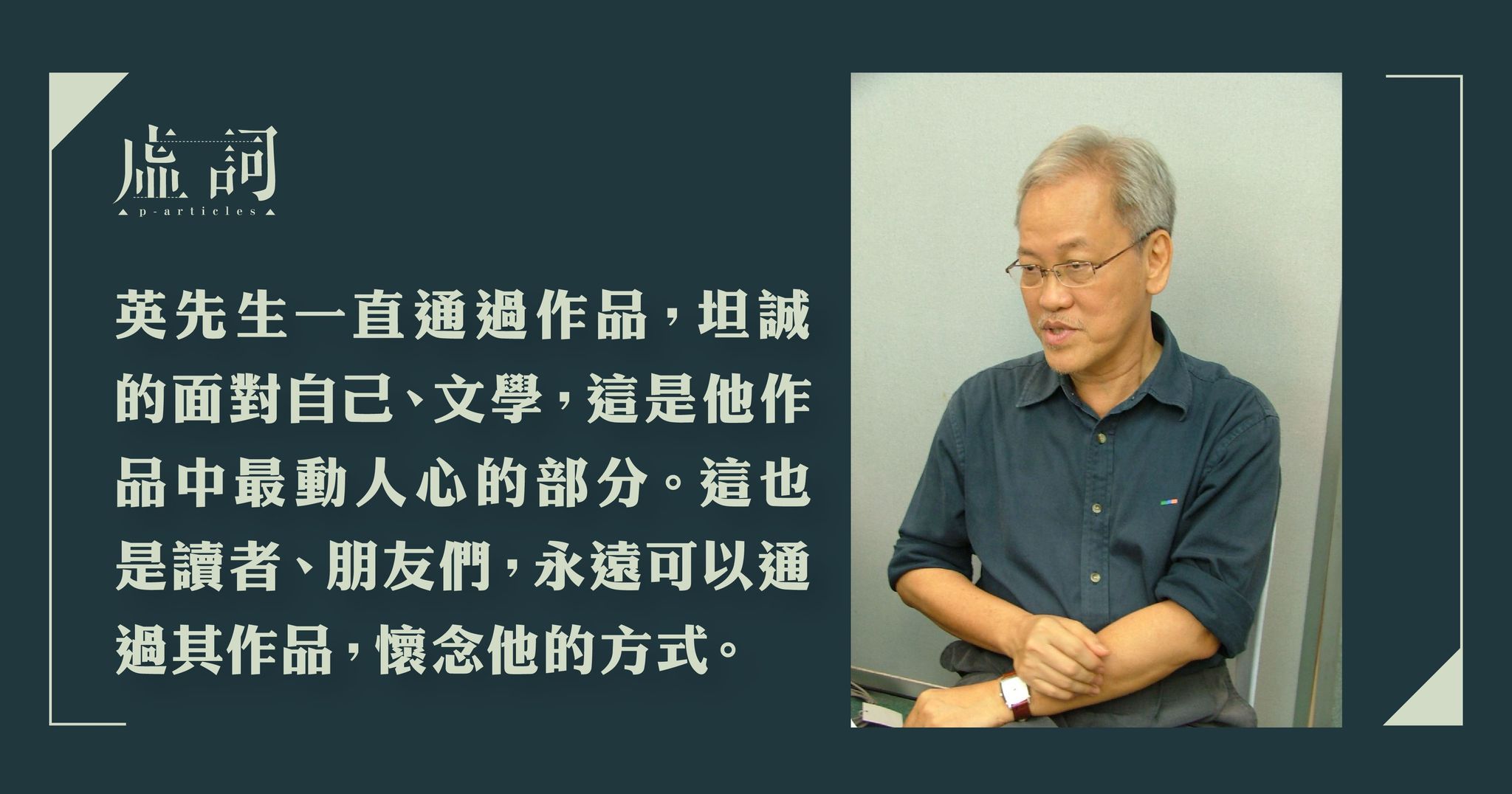紀念新加坡小說家英培安先生 與遺留的新加坡人文風景——草根書室
新加坡華文作家英培安先生驀然傳來1月10日病逝的噩耗,內心暗忖新加坡當代最重要的作家,攜帶著如彗星閃亮的長尾,突逝於華文文學黯然的天空。內心深處暗暗閃動一絲絲的哀傷,沒太過茫然,因知曉他自2007年開始為前列腺癌,2015年為大腸癌努力奮鬥……。即使再多的痛楚與掙扎,英先生一直為文學的生命爭取更多的可能性,不間斷書寫,持續推出了他晚年重要的長篇小說創作:《畫室》、《戲服》、《黃昏的顏色》及詩集《石頭》。從中可探知英先生與時間競賽的晚年,更想確認其小說家的位置,及不忘初衷的詩人聲譽(早於1968年在大專中文系三年級在五月詩社出版了第一冊詩集《手術台上》)。
英先生患病初期,筆者持續送去出版的《蕉風》及書籍於草根書室。或偶爾赴新加坡觀賞電影、戲劇、藝術展覽、文友聚會時,特抽時間在猶如世界文學窗口的草根書室,翻閱最新的港台中新馬出版品,為圖書館、馬華文學館采購最新著作。那時在草根書室,大部分下午時段會遇見英先生與明珠姐探訪店裡一兩小時。有次英先生談及他患上前列腺癌,描繪醫生如何伸入手指檢測等,令我睜大了雙眼。我告知他要多吃煮熟的番茄,他說為何不早告知。我回說:「不曉得您不知道吃煮熟的番茄可以預防前列腺癌啊!尤其是過了四十歲的男人。」有時他抽出寶貴時間,赴附近的海南咖啡館喝下午茶,吃牛油加椰吐司閒聊文學。印象深刻的是某次晚餐,唱完印度神曲的明珠姐隨同,還帶我去吃法式青醬蝸牛,吃完內心起疙瘩,不太習慣初嘗的這道法國菜。
無論何時瞥見英先生,他笑容依舊,穿著長袖襯衫與西褲,溫文儒雅,旁觀難以察覺他是個患病者。詢問他的創作時,自嘴中似乎都處於創作狀態,尤其是在國家圖書館對面比較晚期的英培安時代的二樓草根書室,彷彿在鞭策著年輕一輩需更專注於長期的創作,特別是不容易處理的長篇小說。此草根書室是英先生的第二間草根書室。早在1974年,他創立了前衛書店,1976年轉售後,另設草根書室於布業中心大廈。1980為了潛心創作,他關閉書店。直到1995年旅居香港重返新加坡,借鑒香港的二樓書店,英先生在橋北路重燃再開草根書室的機緣。後因需養病與專心創作,他交託書店給曾協助的許維賢、張惠雯、陳婉菁等打理,每日下午抽出時間來書店處理一些業務。當時的許與張皆是作家、新加坡金筆獎等得主;婉菁則是現今城市書房的負責人,延續草根書室二樓#03-06隔幾間的#03-10。而原本的草根書室已在2014年轉手給林韋地、林仁余等文友接辦,搬遷至新加坡歐南園Bukit Pasoh 路呈殖民時期風味的店屋。這兩間新加坡的特色書店,延續了英先生精挑細選的好書,推薦給讀者,經常舉辦人文活動,廣邀新馬甚至港台中的作家做客,推薦出版的新書、主講各式文學、電影、思想等有趣的議題,打造新加坡濃濃的華文人文精神,為下一代喜歡華文閱讀的讀者,提供精神上的棲息加油站。這是在隔岸的馬來西亞新山書店,已難碰見了。
猶記得《蕉風》復刊第489期的新加坡宣傳推薦會,就設在2002年的草根書室。那時身兼主編、主持的維賢還在草根協助。難忘的是我與作家文友攜帶了百多冊剛復刊的《蕉風》路經新加坡關卡時,被官員扣留,因沒新加坡資訊局准證號附在封面。那時尚不知在馬來西亞的出版品,在新加坡銷售時,需申請新加坡的資訊局准證。然而官員們似乎看不懂華文文學內容,遲遲無法做決定要如何處理,希望扣除一個星期審查後才來取書。或許這也是他們一般的處理程序。後來在扣留室呆了近兩小時,複印了護照等資料,談及此書要在傍晚於英培安先生的草根書室推薦此復刊號,屆時眾多作家雲集主講,久違的讀者們歡聚,希望可以通融過關。其中一名官員耳聞英先生大名,豎起耳朵,或許他是英先生的朋友,忙說既然是去英先生的草根書室,應該沒問題,希望我們之後盡快向新加坡資訊局補請准證。原來英先生的名字竟然是芝麻開門的秘語,內心喜悅不已,才完成那天原本不可能的任務。
英先生早在大學時期就興致勃勃出版書籍及主編期刊,除了最早在1968年由新加坡五月詩社出版的詩集《手術台上》,自大專時期他開始主編出版《茶座》,1969年6月25日至1972年11月共出版15期。如今再翻閱,此刊重點放在文學創作品如小說、新詩、戲劇、雜文、散文上,網羅了當時重要的作家(如今許多已是名家或新馬重要的作家)的作品,如英培安本身的詩、雜文、小說與戲劇;邁克、宋子衡與梅淑貞的小說、李蒼(李有成)、綠浪(陳政欣)、張塵因(張景雲)、溫任平、艾文、飄貝零、子凡、吳韋才、南子、謝清、郭永秀、文愷等,偏新馬現代主義的作品。從中亦能知曉英先生與當時的《學生週報》與《蕉風》靠得近,不僅在這兩份刊物常發表作品,同時也與這群文友產生很多互動,透露了刊物性質靠向現代主義,也傾向自由、民主的作品。如《人與銅像》中,銅像即使是誘惑中年人簽約成為「一天」的銅像,主張是以自由與民主的方式,而非後來英先生被逮捕,控之左傾的成分。英先生當時曾在《茶座》中的第1、2及9期發表了《人與銅像》戲劇劇本。如今對照後來在2002年出版的同名戲劇集,經過時間淘洗與不斷為演出修訂後,明顯的可看出後來的戲劇文本更簡練,場次的發表次序與最後的版本亦不同,篡改甚多,尤其是重新改寫蠻多部分,刪除戲中的小題或主題的「字幕」暗示,刪除累贅與激進的部分等,最主要以寓言方式探索人與銅像的關係,人內心深處的渴望,通過即使非名人的銅像,或許通過革命,甚至踐踏朋友而從腳底翻身,最後通往虛無縹緲的權力追求或其它最終目的。
除此之外,《茶座》的「論文」刊登文評、影評或偏批判性的時評,在第11期特別組稿「星加坡報業風波特輯」。最近英先生髮小李文撰寫了紀念文提及英先生1977年被拘捕時,縱然此好友在內部安全局任職,多方疏通亦無法拯救,僅能提點同事讓他少受罪,因為當時此特輯中提及的華文報業風波(黑色行動)未結,除了李文的文中提及「草根書室被共產黨利用作為傳送消息的聯絡站,時有共產黨聯絡員出入,內部安全局就以為培安也是一份子」,相信《茶座》此期的報道也開始備受新加坡內部安全局持續關注英先生的舉動。英先生以知識分子的身份,1973年主編出版《前衛》兩期。與《茶座》不同的是《前衛》收錄的文學作品明顯遞減,突出的反而是社會、政治、教育與藝術類,導向綜合的知識分子期刊。1990年代初,英先生再次主編期刊——《接觸》12期,收錄的創作文學作品明顯更少,甚至以介紹翻譯的文學作品取代,更專注在大師思潮、性學如福柯、藝術、學術、文學評論、影劇理論等,拓展讀者認識到人類多方面的文化寶藏,讓胸襟更寬闊與視野更深遠,帶領讀者走入經典。
1980年代中,英先生除了撰寫雜文專欄與廣播劇,重心轉向創作長篇小說《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並在1987年出版,隔年獲得新加坡國家圖書發展委員會國家書籍獎。小說以簡潔明晰的文字,敘述青年轉成年人,在新加坡1980年代的生存狀況,折射出作家對於自己、戀人、家庭、社會及國家體制,時代與大環境的問題。文中自然的流露某些名家的字句,顯示作家的身份,在不斷地閱讀與小說的情境。作家的企圖心,描繪大時代中的主角人物,如何通過生活、情慾、面對政治與時代的壓迫,走出另一條生命的歷程。與他之前在短篇小說或劇本的創作,使用寓言式或荒謬手法等略有不同。英先生在長篇小說,以平實的文字(但並非純粹的現實小說),似乎更勇敢的面對自己與體制,結果意外的獲得國家書籍獎,對於他之前面對牢獄之災,可說是極大鼓舞,有重回國家舞台的榮譽。再加上之後2003年英先生最重要的作品《騷動》獲得新加坡文學獎,有實至名歸之譽。
英先生長篇小說的創作,到了《騷動》,嘗試複雜的小說結構,注入更多大時代小說人物如何的生存,逃亡至他鄉,情慾的處理甚至跨越性別,是他備受關注,登上文學巔峰之作。在英先生的作品中,自省的能力、性別與身份的關注、孤獨與孤立的狀態、面對政治與華文語言到《戲服》中粵語與粵劇的使用與變化、疾病與生命的糾纏、尋找新的創意注入其作品、跨越不同類型的書寫等,凸顯了英先生創作的特色。英先生一直通過作品,坦誠的面對自己、文學,這是他作品中最動人心的部分。這也是讀者、朋友們,永遠可以通過其作品,懷念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