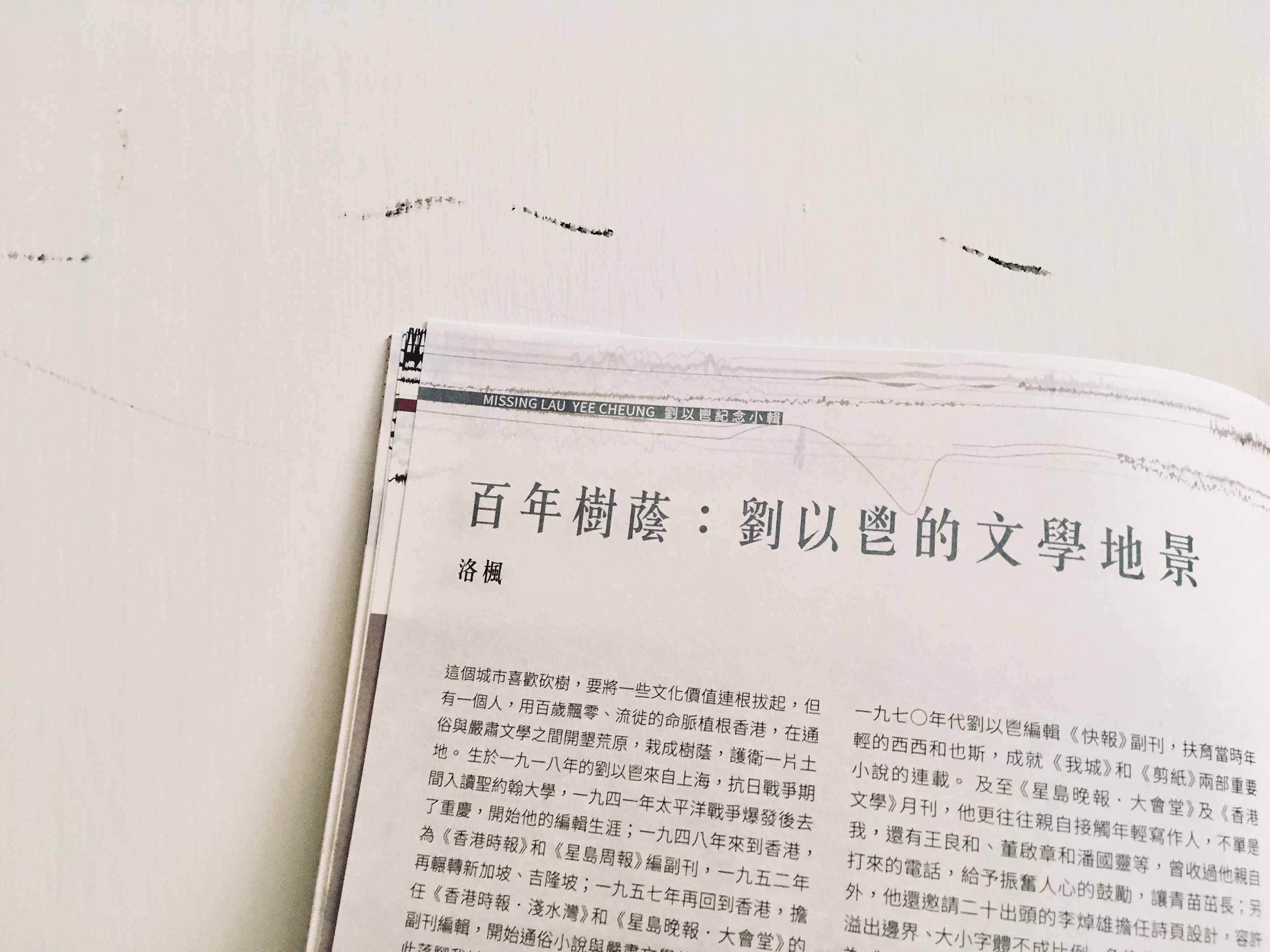【無形.劉以鬯的陌生人】百年樹蔭:劉以鬯的文學地景
其他 | by 洛楓 | 2018-08-10
這個城市喜歡砍樹,要將一些文化價值連根拔起,但有一個人,用百歲飄零、流徙的命脈植根香港,在通俗與嚴肅文學之間開墾荒原,栽成樹蔭,護衛一片土地。生於一九一八年的劉以鬯來自上海,抗日戰爭期間入讀聖約翰大學,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去了重慶,開始他的編輯生涯;一九四八年來到香港,為《香港時報》和《星島周報》編副刊,一九五二年再輾轉新加坡、吉隆坡;一九五七年再回到香港,擔任《香港時報.淺水灣》和《星島晚報.大會堂》的副刊編輯,開始通俗小說與嚴肅文學的雙線發展,從此落腳我城,並在一九八五年至二○○○年間,創辦及主編《香港文學》月刊。從一九一八到二○一八,劉以鬯活了百歲高齡,管窺他的百年生涯,有兩條縱橫交錯的主幹:一是他的離散行旅,二是他的文學枝葉。
為文學荒原開疆闢土
經歷日本侵華與八年抗戰,也因著國共內戰的局勢而四方流徙,活了一個世紀的劉以鬯見證了現代的文明與殘暴,那些流離的城市,成為日後無數故事的底本。另一方面,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難民潮、六七暴動、 七十年代的建設期、 八十年代的中英草簽與「六四事件」、九七的主權移交到「後九七」的動盪二十年,這是劉以鬯植根香港的生命版圖,時代編織了人,人以文字勾連了時代,這座城市跟他之間是一個磁石環扣的場域。其次,從報紙的副刊到文學雜誌,劉以鬯為極度商業化的殖民地開拓文學園地,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作家。我曾在大學圖書館翻閱一九五○至六○年代的《香港時報.淺水灣》,赫然見到劉以鬯以前衛的眼光,容納大量現代派詩人與藝術家的作品,包括紀弦、崑南、葉維廉、王無邪等,同時通過評論,介紹西方現代派,辨析當前文藝使命,匡扶讀書風氣,闡釋文化危機,為文藝創作奠定基礎。這份薄薄的副刊專頁,連同當時馬朗創辦的《文藝新潮》,一起帶動了香港現代主義的文藝發展,延續三十年代上海的斷層,同時跨越海峽,影響台灣的現代詩風。
一九七○年代劉以鬯編輯《快報》副刊,扶育當時年輕的西西和也斯,成就《我城》和《剪紙》兩部重要小說的連載。及至 《星島晚報.大會堂》及《香港文學》月刊,他更往往親自接觸年輕寫作人,不單是我,還有王良和、董啟章和潘國靈等,曾收過他親自打來的電話,給予振奮人心的鼓勵,讓青苗茁長;另外,他還邀請二十出頭的李焯雄擔任詩頁設計,容許溢出邊界、大小字體不成比例、色塊衝撞的破格試煉,為《香港文學》帶來後現代的美術風貌。那年頭,我常常跑到灣仔的雜誌社,聽他手舞足蹈、上下比擬那些風起雲湧的編輯生涯,如何像頑童搬磚那樣,用花鳥蟲魚的流行文字頂住上頭的壓力,保住嚴肅創作的文藝專欄,或像魔術師那樣切割版面,讓報紙容納長達數千字的稿件,語調輕鬆卻高潮迭起,體現劉以鬯是一個天生的說故事者!
以小說家的眼睛見眾生
劉以鬯的小說為何好看?因為他跟人講故事,而不是說道理,或許在一些十幾二十萬字的長篇改成短篇的過程上,有時候不免嘮叨重複,但他的小說世界依然華麗豐盛,也斯說過:「劉以鬯可能是香港小說作者中對不同角色心理刻劃最成功的一人。」劉以鬯能寫不同階層的人物,由販夫走卒、工人、妓女、孤兒,到知識份子、白領階級、闊太,以及死物,無不栩栩如生,七情六慾盡皆七情上面,他以人物行動及其性格發展推動故事情節,以電影鏡頭的書寫方法調度場景,同時發揮新感覺小說派的感官書寫與城市地景刻劃,不避聲色犬馬,或伸入中國古典的民間傳統,或結合西方現代派的文學技巧像意識流、平行敍述和文本互涉,建構一個一個世俗而具有血肉的人間景觀。劉以鬯說過:「小說雖非歷史,小說家的敍述卻記錄了某些經過的事跡。」在日間寫通俗文類以換取生計,晚間寫娛樂自己的文字,就這樣他的筆下銘刻了幾許的繁華地,諸如馬場、夜總會、手指舞廳、賭館、徙置區、商業大樓、茶餐廳、百貨公司和橫街小巷的滄桑變幻,以及活動期間的香港故事。如果說〈過去的日子〉和《酒徒》帶有自傳的寄身,是作者見自己的視點,那麼,《對倒》、《打錯了》和〈動亂〉等涉入各個階層的命相,便是他見天地、見眾生的胸懷。
千奇百怪的創作實驗
劉以鬯在〈我怎樣學習寫小說〉一文中,除了自述創作的時空背景外,還列舉不同的寫作技法,包括詩體小說、長篇刪為中篇或抽出短篇的做法、沒有故事情節的佈局、用兩種假設組成的敍述方式、黑白對比、現實主義跟現代主義結合等等,體現他恆常勇於打破規條的實驗精神。《酒徒》成書的意義,除了意識流的運用及作者的傳奇色彩外,還夾雜許多詩化的斷片,文字鏗鏘有節奏、意象和比喻靈透新穎,而書中大量引用中國與西方現代文學史料,通過人物的獨白或對白,褒貶經典、提出創作綱領、分析詩歌流派、批判文化底蘊,形構一套非常完整、 屬於劉氏的論述,類近後設的格局。另一本為人津津樂道的極短篇小說集《打錯了》,更利用報刊版面短小的特性和讀者容易接納等有利條件,恣意實驗各類前所未有的寫作技法,包羅編年體、時序排列、漸進式、連環套、書信體、超現實夢境、魔幻寫實、前後對比、獨白、圓形結構、鴛鴦蝴蝶式煽情、人物二重敍述、故事新編、戲劇衝突、滑稽諷刺劇或漫畫筆法等十幾種,藉此反映人性的貪婪和愚昧、生活空間的擠壓、城市的功利主義、人際關係的計算,活脫脫就是一本寫作大全和香港照妖鏡!
《對倒》寫道:「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是的,劉以鬯那個文學副刊的年代、動輒連載十數萬字小說的黃金歲月,早已一去不返,我們在感慨追思之餘,仍必須相信時代總踏著前人腳步滾動,而高齡辭世的作家留下的樹蔭依舊護衛我城,因他以編輯栽培、 或以作品滋養的幾代寫作人,承受雨露潤澤,繼續抵抗砍殺的惘惘威脅,但願樹蔭常綠、花果永在!
14.6.2018
引用資料:
引用資料: 也斯:〈劉以鬯的創作娛己也娛人〉,香港:《信報》,1997年11月29日,版24。
劉以鬯:〈自序〉,《劉以鬯中篇小說選》,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5年,頁2-3。
劉以鬯: 〈我怎樣學習寫小說〉,《他的夢和他的夢》,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年,頁338-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