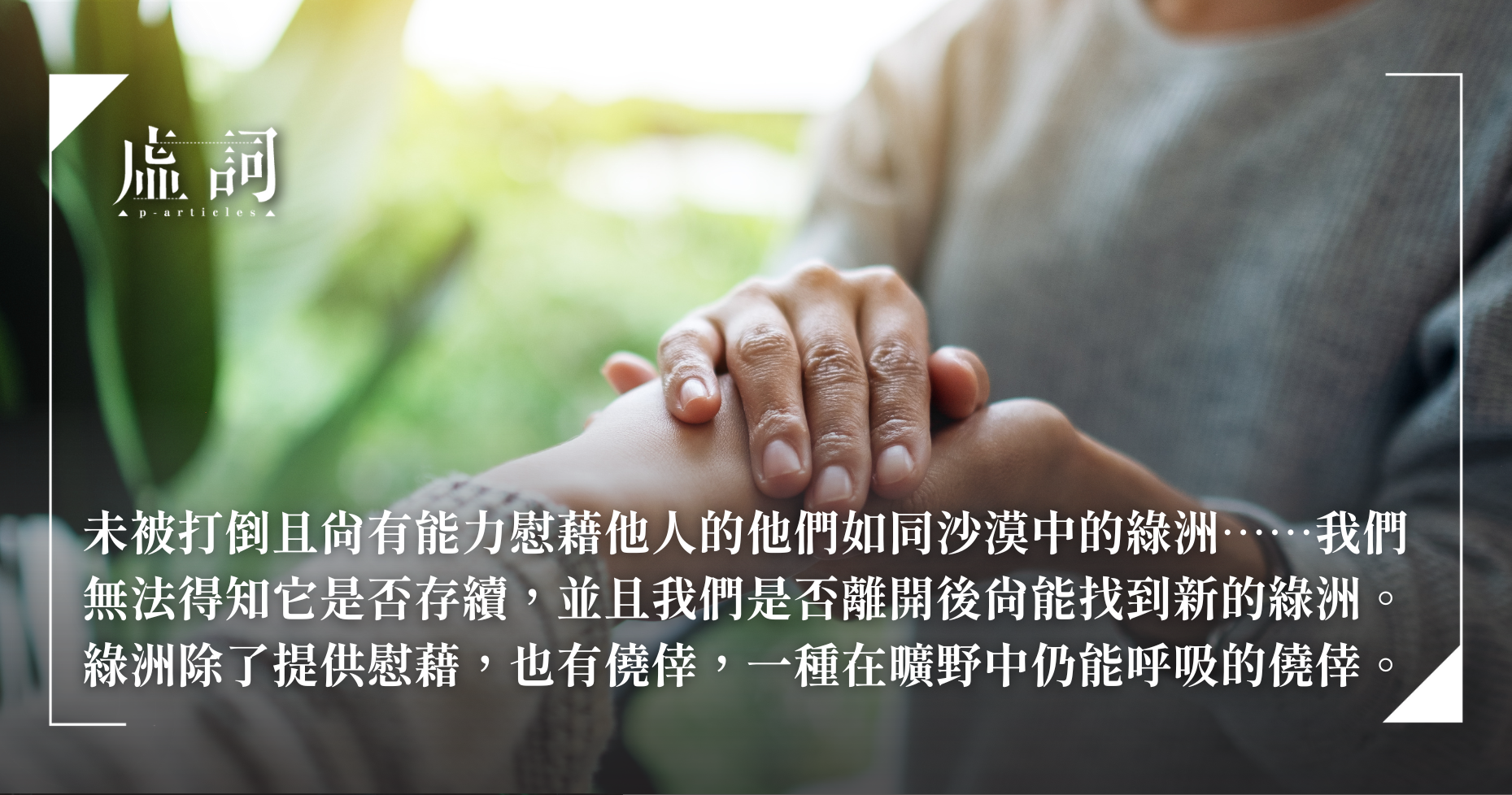一場有關宏觀的自我辯論
赤道的早晨每天準點在七時到來。我仍然無法入睡,手機中是仍在播放的新聞和教程。隔壁遲到的水聲彷彿匯聚成了一陣鼓點,讓我懷疑過分壓抑的花園中竟有人在深夜奏樂。這裏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新聞永遠是「雅俗共賞」—— 一會是關於俄烏戰爭的最新報導,一會又是有關東海岸野雞是否擾民的採訪——最後都有同一個答案——看人怎麼想,或者用英文的俚語來說:「Perspective matters(視角很重要)」。新加坡總在宏觀的事物中尋找確幸,他們藉由美國航天局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但也會為咖啡的濃度爭論不休。我想到拉娜·德雷「The Greatest(偉大事物)」中的一段歌詞:「夏威夷剛剛躲過了導彈危機;洛杉磯陷入火海,天氣越來越熱;侃爺染了金髮,已經變了;『火星生活』不僅再是一首歌;哦,直播快開始了」。
來到這裡三年後,我承認對宏觀事物徹底失去了興趣。我很羨慕那些還能對某個國家,某種意識形態,某種歷史傳統抱有興趣和希望的人——這些可以延伸到任何概念:民族,民主,自由,象牙塔,文學傳統等等;他們甚至可以通過這些去抵抗微小生活中的苦難和事故。但這種羨慕很快化為一種曖昧的懷念——因為我曾也是其中的一員。我也曾站上洛杉磯的街頭疾呼。有趣的是,我竟然來到了一個除了一處公園,其他非提前註冊的公共示威均為非法的國度。在芳林公園,他們看似憤怒地討論一些很日常的問題:電動車是否應該被允許上路;新加坡的雞蛋是否仍可以漲價。另一側則是對著抖音跳舞的年輕舞者,以及忙著分發傳單的保險員。問題來了:當你為他人疾呼,誰又真的在乎?抑或,誰又為疾呼者疾呼?一位移民在帕薩迪納可以隨時失去他早已習慣的椰樹藍天;而一位藝術家在太平洋的對岸卻必須靠揣測過活。
到頭來,想起過往的生活,那些場景如同恐怖情人對少年的撫摸,常常讓人在興奮和恐懼間震盪不已。我也對曾寄託了一生之夢的場所(實體或虛擬)感到了一陣永恆的寒意。失眠後的晨曦是溫柔的,黑夜中仍有少許個體是可愛的。未被打倒且尚有能力慰藉他人的他們如同沙漠中的綠洲,用愛滋養的慰藉,我們無法得知它是否存續,並且我們是否離開後尚能找到新的綠洲。綠洲除了提供慰藉,也有僥倖,一種在曠野中仍能呼吸的僥倖。
但好消息是,如今我可負責任的說,在三十歲來臨前,我徹底失去了對一切宏觀事物的希冀,以及慾望,並非覺得它們和我無關,而是過於有關。它們總是敲碎我的甲殼,讓我必須面對一項項不平等的交易—— 一次次我長出新的甲殼,它們便再次敲碎我,讓我的心幾近乾涸。於是,我只可靠著微小生活中的細節足以續命——如木心說動亂中的一碗餛飩;或者村上春樹在全共鬥抗議者經過東京時,背過身點一根菸。我唯一還維持著和宏觀事物的微弱聯繫,是為了提供一些微小生活的基礎而已。這意味著,生活將是痛苦,但也將是偉大的;我必須認清一切宏觀謊言,然後用一把油畫般的鐵鍬捍衛我的生活,就算那只是一幅油畫。真理和正義的時代已經過去;誰都無法奪走我早上必須要抽的那根駱駝,打擾我喝一杯豆漿,因為我咖啡因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