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書
散文 | by 黃戈 | 2025-0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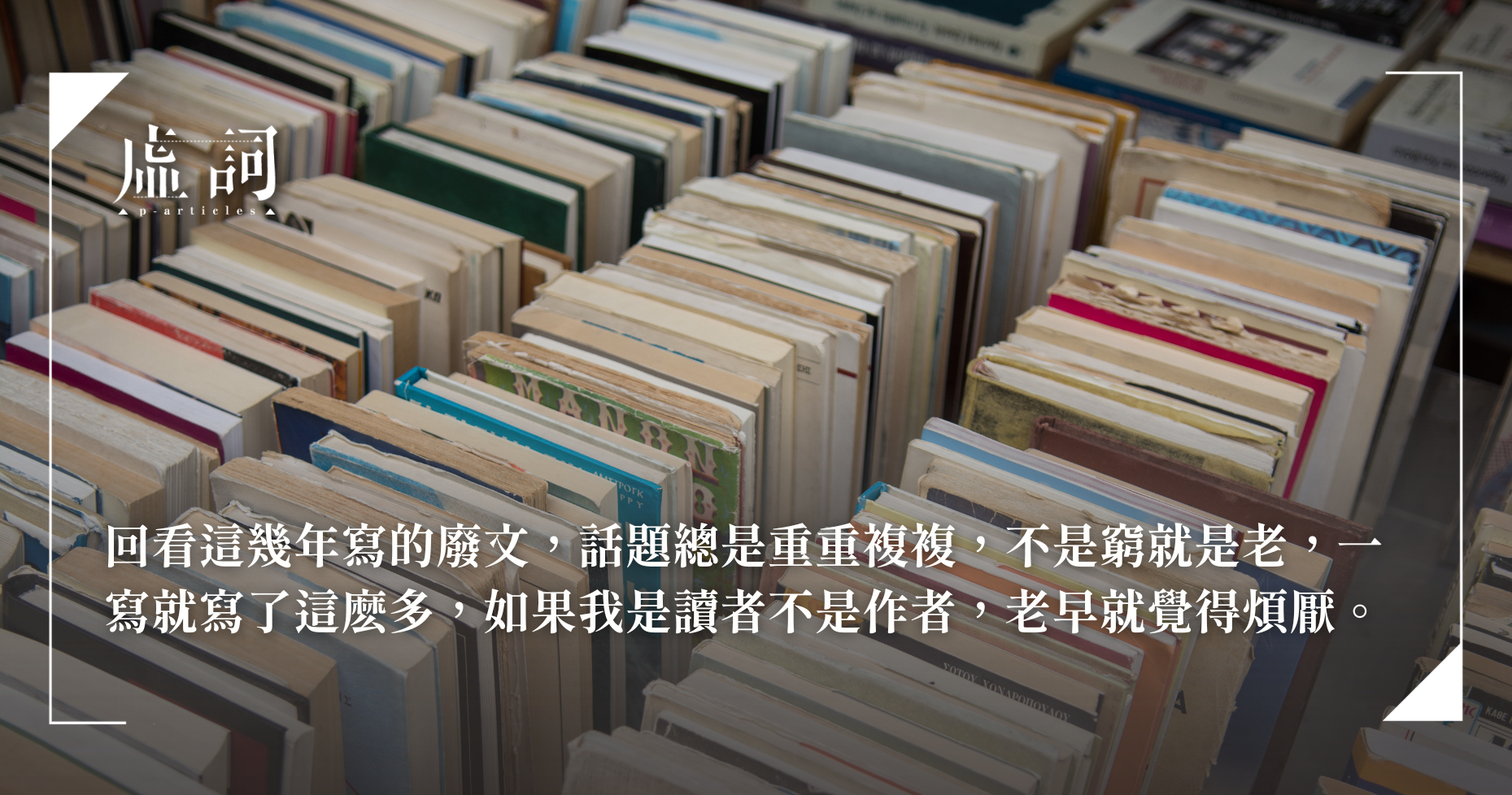
舊書FB.png
書,的確是老了。
三年前來台灣讀碩班,行李箱大部分都是書,衣服就是冬夏幾件。機場行李秤重的時候極限壓線,書的重量大概也是這個數字,但忘了有多少。當時是2021年,疫情尚未完結,入台還需十四天隔離、七天自主健康管理。從十四天到七天,從七天到正式回校,兩段遷徙,學校都有安排巴士統一接載。司機協助我們搬運行李,打趣說我的箱子是不是裝黃金,那麼重。搬了兩次,第二次是相同的內容,相同的黃金。說黃金也不是不可以,「書中自有黃金屋」的俗語大家都聽過,把行李箱的書比喻成「黃金」,倒也並不陌生。儘管這個時代讀文組,說這句話多少有點自欺欺人,甚至「自欺欺人」也開始失效。人是肯定欺不了,自欺應該也很勉強,窮是實實在在的。我不知道黃金價格,只是設想行李真有相當於書本重量的黃金,那我這幾年讀書,乃至於未來幾年讀書,也不用考慮經濟問題。有時真覺得形軀就是意志的負累,人要食飯是很反人類的設定,可以不吃不喝,就沒有那麼多鳥事。所以比喻畢竟是比喻,就算書中固有黃金屋,但這種黃金並不能變現……應該也可以,當廢紙賣。
帶過來的書不盡跟研究方向有關,有部分是通論,就是《中國哲學史》、《中國散文史》、《經學通論》那一類;有部分是邊疆史、思想史、政治史的專論,當初是覺得好像有關但又未必有關,貪多務得,一併帶來;還有一部分是新購之書,沒來得及看完,像《詩論》、《娛樂至死》、《克蘇魯的呼喚》這種。最後則是紙本雜誌──兩期《無形》、一期《方圓》,因為有我自己的廢文。其中一期《無形》刊出不久我就要過台灣,所以我是自己買一本帶過去,並且交代編輯部不用寄給我。其餘的《無形》、《方圓》,我都有兩本,就是自己買一本,編輯部送一本;一份留在香港,一份帶來台灣,類分靈體的概念。我的書並不是甚麼孤本、善本、絕版本,都是圖書館輕易可借的著作,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是台灣的出版物,帶台灣出版的書來台灣,這件事是有一點搞笑,沒事,整活,大家開心就好。除了廢文留作紀念,其他的書只是圖個「隨手翻閱」,以備不時之需。其實這幾年也真的不常翻閱,最多是跟研究方向有關的書,即使相關也未必全部常翻,要看議題是否有對上。有部分是當初覺得有關,後來發現用不著。所以翻來覆去,都是那麼兩、三本。就是這樣,沒有的時候徬徨疑慮,存有的時候卻置之上架,以前就叫人「小甜甜」,現在就叫人「牛夫人」。
為處理大學成績單,2023年12月短暫回過香港。「時長兩年半」,「一坤年」說長也不長,只不過多了重台灣身分,香港也就多了重異地感覺,正如兩年半前初到台灣,身分是香港,異地是台灣。晚上回到香港住處,書櫃上2020年買過的書,有《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與日本》;2021年則有《香港電影王國》、《武俠電影與香港電影現代性》,還有《老殘遊記》,小說早就讀過,只是想買本「私伙」。行李空間有限,無法全部帶走,一定要有人留下。上面這幾本書,就這樣閒置在香港的書櫃裡。過了這麼久,紙質如新,頁面完好,書的狀態依舊不錯,連墨油味都還很明顯。帶過去台灣的書就沒有那麼幸運。可能是保養不慎,跟我一同來台的書,紙張頁面,幾乎都開始或已經泛黃。最大對比,就是留在香港的《無形》、《方圓》還是那個樣子,帶來台灣的則已泛黃、發皺、質感軟化,明明不到三年,卻跟圖書館那些幾十年前破舊泥黃的庫藏有得比。當然,《無形》今年四月之後也停刊了。
不過更有趣的是,我居然還找到《論嘗試文》,一本更舊的書。大概2016年尾,大四上學期末買的,當初根本不認識作者,對文學界也沒有很了解,文章討論的往事,總有點狀況外,大學階段讀完就讀完,放置再放置。這幾年在台灣讀書,教授就是馬來西亞人,也遇過不少馬來西亞的同學,黃錦樹的名字就時有聽聞,再加上台灣出現散文爭議,《論嘗試文》的觀點就經常被提及。黃錦樹「黃金之心」與唐捐「山寨散文」,沒讀過都有聽過。無意之中,這個名字就不陌生了,文學獎的往事,也略有所聞。但在香港書櫃重新翻出這本書,最奇妙的感覺,反而是「原來這麼早就讀過」,當時才二十三歲,這樣就七年。
2024年,碩班已到尾聲,也是時候離去。文科在香港被稱為「乞食科」,台灣則是「文組地獄」、「文組低薪」、「文組無用」、「文組無產值」的標籤一搜一大堆,從「乞食」到「地獄」,可謂無縫交接,倍感親切;從「地獄」回到「乞食」,不過又是一圈循環。這次不打算將書放進行李,除了常用的幾本,其他大部分都已事先寄回香港,兩箱合共約兩千,不貴重,但貴,也重。實際要帶的東西確實不多,書卻是例外。遠行都要費神安置這堆仁兄,不能說走就走,輕裝上路。現在當然可以回到香港,起碼還有一個目的地,但永久住址,也難免有一天要遷移。別講買房的事,除非你送層樓給我。記得第一次去香港書展是2010年,自此之後,每年七月這個時間,就是固定買書的日子,逐年累積,書就越堆越多。帶來台灣的大約是兩箱,如果全部書加起來,有多少箱我並沒有統計過,可以想像的是,日後真的要搬遷,書就是大工程,也是大麻煩。可能超前部署,多少捐個幾本,減輕重量,或者直接閉眼丟棄。其實還是那個老問題,這麼多年買的書,很多都讀了一次就放下,尤其是小說、散文類,沒有興趣就很少再看,放置而不棄置,只是因為有時瞥見書名,偶爾會想重讀一次;工具書就真的有需要才會拿出來,但工具沒有很好用。放下「萬一想讀」、「萬一有用」的心態,解脫可能就更容易。
未來或許要適應電子書,無論閱讀還是儲存,正如以前從寫字逐漸變成打字。書沒有實體紙張的限制,不會變舊,也就不會被時間折磨到發黃殘損。「電子生命」這玩意,人體還未實現,書體卻容易過渡。人能夠像掃描電子書那樣虛擬轉化,「機械飛升」,倒也不錯。另一個類似但相反的概念是「血肉詛咒」。《魔獸世界》「AFK」了幾年,而「暴雪」喜歡吃書,現在故事版本、設定跟得不是很足。以前是說,艾澤拉斯的物種,原本都是岩石、金屬之類的無機生命體,後來受到古神腐化,無機變有機,開始有皮膚、血液,最後演變成現在的血肉之軀,容易生老病死。這個過程、結果就是「血肉詛咒」。英文原文是否有其他意思我不清楚,從中文的字面描述來看,血肉,其實是一種詛咒、腐化的產物,無機才是原本面目。擺脫血肉的是「飛升」,變成血肉的是「詛咒」。
回看這幾年寫的廢文,話題總是重重複複,不是窮就是老,一寫就寫了這麽多,如果我是讀者不是作者,老早就覺得煩厭。從作者的角度看,寫作可能不是一種「療癒」,而是圖個「麻木」。魯迅〈祝福〉大家都讀過。如果要為這篇小說構想一個符合當下語境的詮釋、啟發,或許就是「無限loop」的厭煩。祥林嫂不斷惦記著她的故事,逢人就講,講到最後魯鎮的人都能背誦,麻木煩厭的情緒上來,反而清除了故事的悲痛。我不知道祥林嫂有一個無限說下去的機會,是否有一日她自己也會覺得無聊,作者跟讀者一樣,對自己的故事失去興趣?魯迅沒有寫下去,小說也就無謂糾纏,但或許我可以親身實證一下,亦即不斷說老,不停講窮,是否連我自己都會厭倦麻木,不再介懷。如是,這不失為當前版本「最佳的解」。我解決不了問題,就解決提出問題的我。
202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