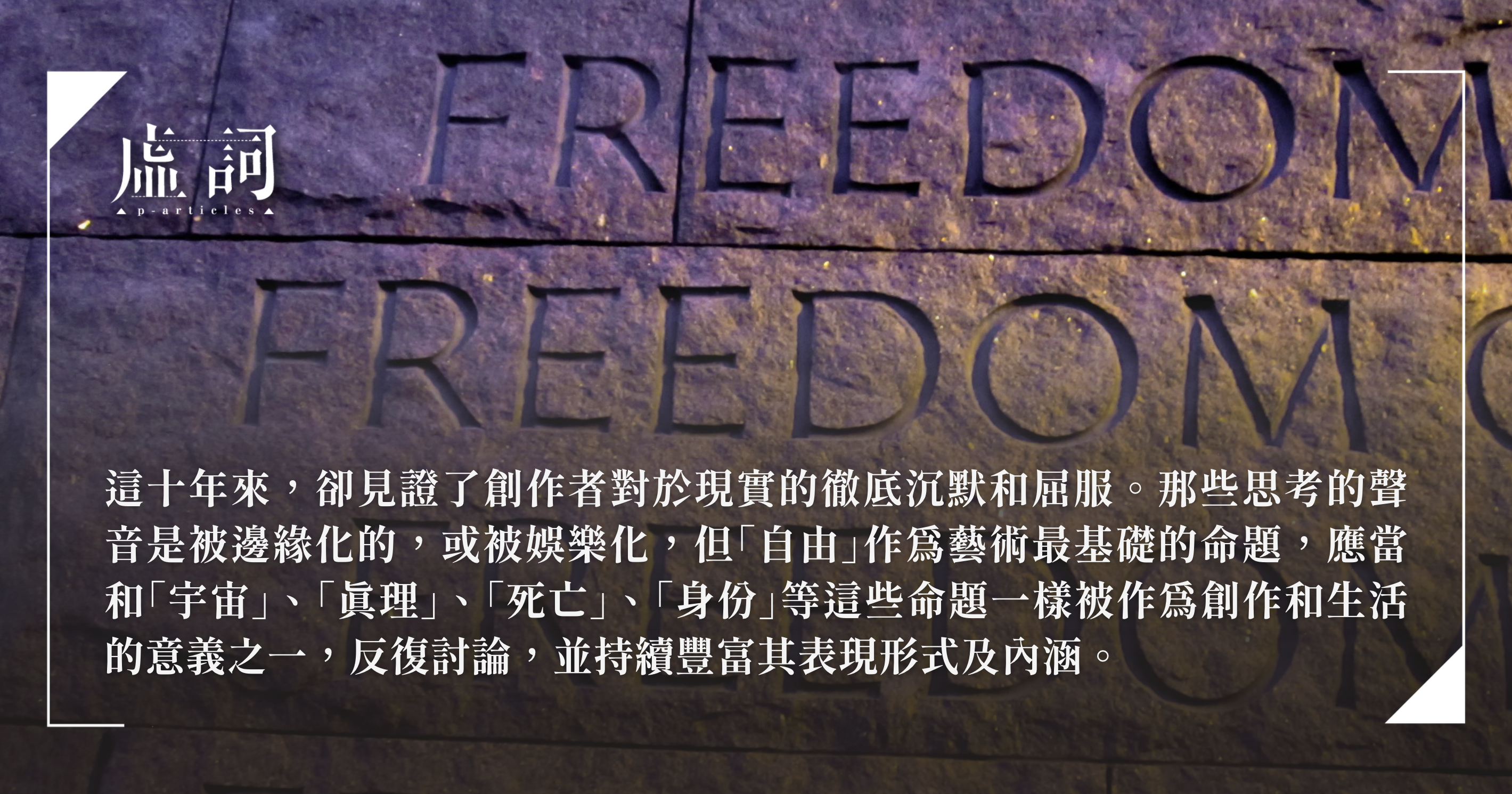對中國藝術,重新談論自由
有人不明白為甚麼創作者總在講「自由」的問題,我也疑惑。最近看音樂人黃明志和媒體人志祺的對談,有所心得。當黃被問到對所謂「理想的自由社會」的定義時,黃明志重新提出了那三項標準:細化來說,就是「言論,創作,出版」自由;這三項乍聽顯得過時,早在啓蒙運動或是五四運動,常有涉及。但在如今的節點重新討論,反而很有必要。作為討論藝術的基礎條件,這三項的意義仍然重要,並沒有因為後現代的語境而自然消解。缺少它們,將使我們在一個極其狹窄和扭曲的狀態去討論一些看似有用,貌似宏偉的話題。
在文化藝術行業生存,先不論行業走向,待遇高低,地區差別等等,大部分從業者是依靠這三項存活的;就算轉向虛擬平台,這三項仍然相關。從整體來看,如果沒有這三種自由,則意味著符合主流,迎合權力的作品和言論可以形成市場壟斷,而其他的種類要麽可以強行控制自己怎麼說,怎麼創作,怎麼出版,要麽直接被被邊緣化。
當然,我們也可以強行說:那些商業作品,那些主旋律作品也有批評價值,藝術價值,但本身這些作品本不需要承擔和顧及這些方面。這是其他類型電影的工作。比如好萊塢就是好萊塢,歐洲Arthouse就是Arthouse,藝術片可以走自己的院線,找到自己的觀眾,自己養活自己;商業片也可以繼續走商業路線;主旋律片在每個國家都有,美國也有主旋律大片,但也可以繼續自己的路線。這三者本來可以互不影響,或者不至於互相影響到其中一方難以存活。
所以可以說缺少這三種自由,不僅僅是政治問題,更是一種市場和權力結合下所形成的市場壟斷,是一種經濟問題。再有人會說:就算沒有這三種自由,前蘇聯和中國大陸也有很多很棒的藝術家和作品。這確實是真相。甚至軍事獨裁時期的韓國,也出現過優秀作品。
但是這樣想就掉入了一種思維陷阱,覺得越缺少自由反而越能逼人創作。這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缺少自由確實能逼著一部分人繼續創作好作品,因為一部分人類的本性就是創作,就算被關入監獄,總會有人想著拿衣服寫詩,拿牆壁畫畫,拿牙刷頭刺青。可是,藝術不僅逼問人類的底線,更是探索人類的極限。我們在這麽想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馬來西亞,韓國,甚至新加坡,這三個國家的電影和藝術在近年來的快速發展,都和不斷「解凍」的政策有關。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中國大陸藝術(包括文學、電影)的幾次爆發點,都正好是這三項自由稍有寬鬆的時候:二三十年代(1926-1937)(民國時期);一九八零年代的「文藝潮」和「八五新潮」;以及千禧年初的「媒體之春」。但這三種自由的不完全發展,意味著這些爆發都是不可持續的。甚至會造成文化上的斷層,產生新的矛盾。
而在最後一個階段,尚有創作者會反復討論這三種自由的問題;這十年來,卻見證了創作者對於現實的徹底沉默和屈服。那些思考的聲音是被邊緣化的,或被娛樂化,但「自由」作為藝術最基礎的命題,應當和「宇宙」、「真理」、「死亡」、「身份」等這些命題一樣被作為創作和生活的意義之一,反復討論,並持續豐富其表現形式及內涵。
但我們都產生了新的共識:自由的討論是無意義的,甚至荒謬。我們學會了討論商業的成功,甚至忘記了商業的初衷。這種結果,是長期的失望和疲憊所造成的。而更多優秀的創作者,選擇回到東方的靈性傳統中去尋找和保留對自由的探索,如佛教,道教,甚至儒教,或是其他民間信仰。因為這是唯一允許進入的領域。在這些領域中,創作者如竇唯可以在誦經聲中,用「後出師表」來表達那份「中道崩殂」的追求。這基本是中國藝術家的歸宿:他們對自由的探索會因長期的失望,疲憊,和遺忘,走回到傳統中。不論是吳冠中,還是李叔同,還是竇唯,他們最終都無法持續性地給出更進一步的答案,導致中國藝術對自由的探索,總是不斷走到那扇門前敲門,再敲門,卻從來沒有人真正打開,並走進那個空間,告訴我們那後面是怎樣的:那到底是普魯斯特的房間,還是柏拉圖的洞穴;是波德萊爾的小巷,還是薛定諤的盒子。很多藝術家已經給出了他們的答案,但卻一直等待那個來自古老文明的聲音:中國人,你們對自由的理解是怎樣的?他們想:你們可以大聲說,或者小聲說;你們可以給出許多不同答案,甚至推翻歐洲人和美國人的見解。但你們別忘了這件事,總之。
賈樟柯其實在07年的「賈想」中也以電影的角度,問出了類似的問題,但除了當時的質疑和吶喊外,並沒有得出他的結論。他嘗試在《三峽好人》中給出一個相當東方的結論:自由是一種道德力量,是在商業的大潮中做個「好人」。這是儒家的自由,在今天顯得更加單薄。後來他走向紀錄片,用《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告訴我們:自由就是看這群曾經的文化先鋒們——面前的大海,並相信他們既然游了這麽長的距離,他們一定能帶我們游到更藍的地方。說實話,這是比《三峽好人》更令人失望的答案。因為這種自由,是做不成「好人」後的「小武」,看向了歷史,因為既然未來不確定,那麽只有回溯是自由的。但問題是,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回溯的權力,因為這意味著要留下一條歷史痕跡,屬於所有人。這也意味著,這種自由,好像只屬於這群先鋒;並因他們過去的幸運,可以繼續獨享這份自由。賈樟柯也是其中一員。
但若要追求更廣泛,並具有可持續性的自由,這意味著,賈樟柯要徹底告別他的汾陽;畢贛得永遠離開他的凱裏,張曉剛忘記他的家庭照,劉小東從岸上,走入水中,走入他的模特;這意味著胡波在上吊的前一刻,突然想到用繩結拍一個新電影;也意味著余杰所說的,我們不能只做昆德拉,我們還得做哈維爾。我們不能躲在人物身後安全地琢磨自由,我們都要走到幕前,像哈維爾一樣,勇敢地解構自己。因為解構自己,也是解構時代,解構我們想追求自由的原罪,和時代缺乏自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