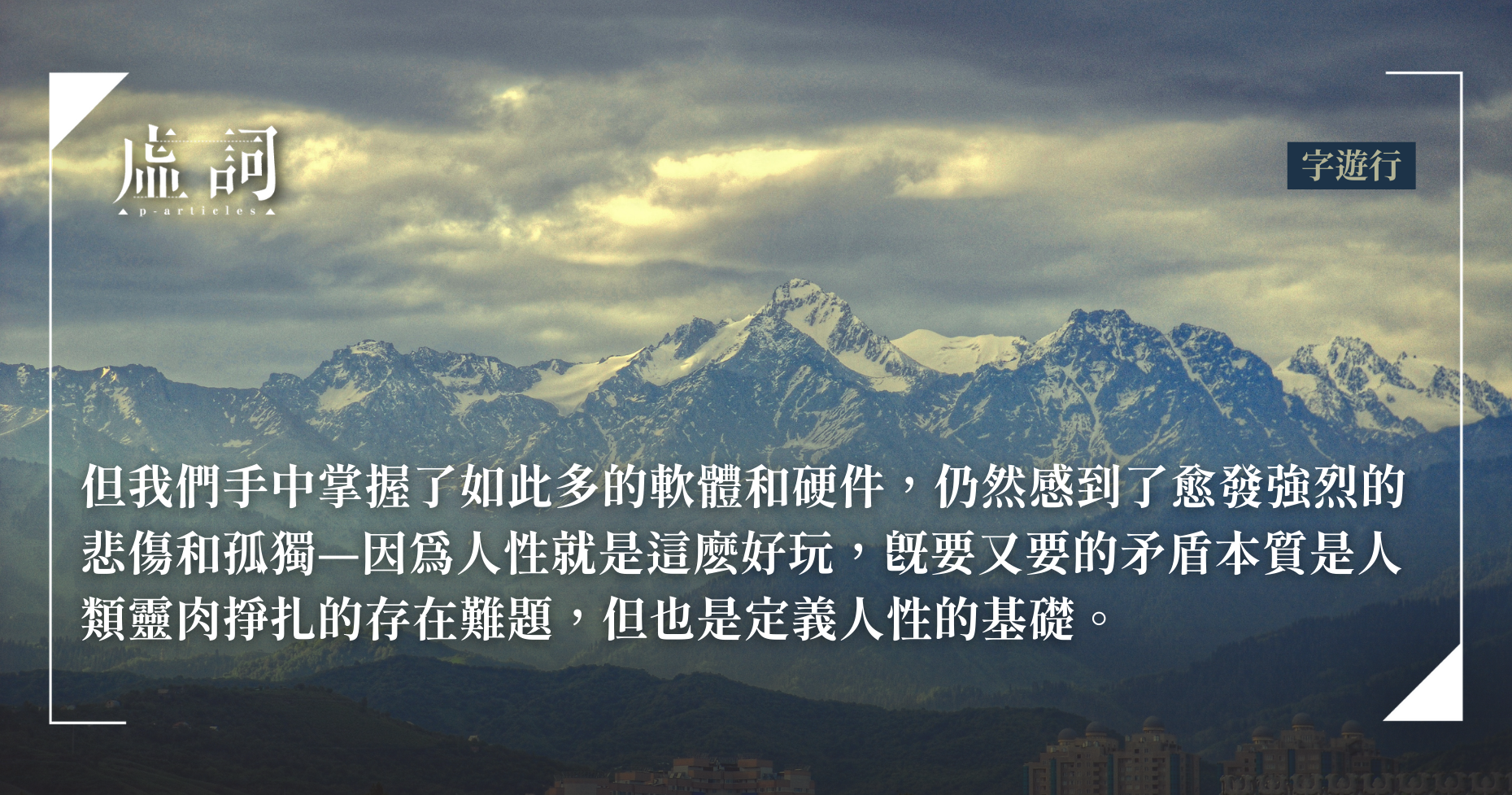【字遊行・阿拉木圖】阿拉木圖隨想
雪夜再聽明星合唱金曲「We Are the World (我們就是世界)」,重回人類群星閃耀時。曲罷開窗,樹葉窸窣抖落一些白色的音符——當在蘇聯故土的阿拉木圖,看見林立的高樓,遍佈街角的星巴克,漢堡王,以及虛擬貨幣的投資廣告—「機會如同雷電」;再看見小巷中下著小雪的赫魯曉夫樓,燈光閃爍,滯留著獨屬於過去的節奏,讓人無法不回憶我出生的九零年代。
九零年代不僅終結於蘇聯解體,柏林牆倒塌,也結束在了「九一一」的一聲巨響之中。冷戰固然殘酷,但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人類曾經相信有一些東西必然比動物性的生存本身——飲食男女更加偉大。一個有關個人成功的謊言快速取代了一代人追求的卓越。幻滅的結果是,我們用最精緻的手段來反覆包裝飲食男女,急功近利——「Tinder(聽的)」,「MidJourney(中道)」,「Twitter(推特)」,「YouTube(油管)」等等。這都沒什麼,美國作家大衛弗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說:「這都沒什麼,可以幫助你娛樂和休閒,在少量如同零食劑量攝入下,它是暫時安全的。但如果這成為你的主食,你作為人類的部分會死亡。因為科技只會變得更加發達和便捷,所以你的屏幕前只會越來越多地存在這麽一群人——他們不愛你,卻只想賺你的錢。」 緊接著歷史紀錄片視頻的,是一則有關手機的廣告——「流量比我們祖先騎的駿馬還快」。
昨天阿拉木圖下了今年的第二場雪,和本地朋友T聊天,沿著一條名叫「春日」的小河散步。據她說,河曾經的俄語名字是有關一位二戰烈士。雨水在北風中逐漸粗礪,悄然轉變成雪片。她伸出袖口中的左手指著右岸說:「那些是昂貴的別墅私宅」;又指了指左岸:「這些是過去留下的家屬樓,最近被重新改建成了商業房。」里茲卡爾頓酒店的巨大身軀擋住了我的視線,她又踮腳指著左岸說:「它們都在酒店的後面」。我陷入沈默,只好陪她一起坐下。於是我接著問她:「那這個公園呢?」她說:「公園可是一直都在,只是不叫公園」。我們聊起了類似的小學教材,這反而成了更輕鬆的話題—如何能讓一個小學生讀懂德國哲學家的觀點呢。
我們都認為這些意識形態本身並沒有錯,錯誤的是美國導演伍迪艾倫(Woody Allen)電影「Whatever Works(怎樣都好)」開頭拉里大衛(Larry David)說的一句話:「人們用它們的名義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雖然無論是西方民權運動,抑或是東方國際主義,它們都在二十一世紀到來前即走向失敗,簡單而流行的理由是:因為人性貪婪自私,因此無論是「蘇聯笑話」,還是「美國麗景」都成為茶餘談資—能成為談資是因為它們至少有部分真實性;但這並不否認他們的存在本身,已經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勇敢的社會實驗。任何有趣或有益的結果,往往來自於這些實驗,來自實驗中所蘊涵的某種「童真」和「俏皮」。
而我們引以為豪的二十一世紀呢?我們好像已經把「飲食男女」修煉到了極致。通過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沒有什麼比二十一世紀的,「後馬丁路德金」時代,「後蘇聯」時代,或者我們說的更有趣些,「後邁克爾傑克遜」時代——還有總結這一切的時興詞彙「後真相」時代過的更加輕鬆和舒適——但我們手中掌握了如此多的軟體和硬件,仍然感到了愈發強烈的悲傷和孤獨——因為人性就是這麽好玩,它一面如此的追求飲食男女,一面又不甘於這麽活著,既要又要的矛盾本質是人類靈肉掙扎的存在難題,但也是定義人性的基礎。
但我們都忘了:我們的父輩曾經也是一無所有,卻要在廣場上夢想一個公平社會的年輕人。而我們卻在他們的幻滅中,學會用一種故作成熟的口吻說:「人間不值得」。人間真的不值得嗎?值得不值得,你要麽先走遍世界再說;要麽不要輕易接受人他人的答案:你自己決定就好。總之邁克爾傑克遜和他的同好們告訴你:人間充滿失望,但總之還算值得—因為人類一體。你要知道這個男人,在第十年失眠到早上十點時,沒有選擇尋短,而是用麻醉針暫時安眠,雖然他並不知道麻醉藥劑量早已過量。關鍵是:你真的要一個也只活了一次,而且涉世未深的網紅告訴你「人間不值得」嗎?這讓五旬還在高唱「Heal the World(療愈世界)」的邁克爾顯得要麽虛偽,要麽幼稚。當然,從這個角度來說,「人間不值得」絕對也不可能是完全的通透,因為連弘一法師也沒有完全否定——他只說「悲欣交集」,而非用值得或不值得做簡單的判斷。因此,早早堅信「不值得」的態度要麽是怯懦,要麽是疲憊。但最好是後者—寧願做一個疲憊的「莽撞」勇者,也不要做一個怯懦的所謂「智者」。後者也最多是明哲保身,甚至有些狹隘的自私;很少真的有自己結束自身荒謬的勇氣。所以我會覺得他們怯懦,而非某些社會實驗,或是人生實驗的殉道者。
但是,經歷了二十一世紀的二十四年,無論是宏觀的社會事件,還是個人的生活坎坷,對於二十世紀的理想主義,我們當然不能理解,包括我自己也無法總是理解。所以對於我們中的大部分來說,邁克爾傑克遜所創造的「Neverland(烏有鄉)」不僅顯得虛妄,還成為了他孌童的主要證據。就像面對二十世紀末的亞洲,我們的父輩不是不記得,而是選擇性忘記,或是生理性否認。大部分人類在幻滅之後,不會選擇重拾勇氣繼續嘗試,而是用一種虛假的生活藝術,來扮演一種個體的,民族的,甚至種群上的「成熟」。但可怕的是,這不是一種真正的成熟,而是一種停滯和倒退。如果我們真的把詩人顧城,音樂人鮑勃迪倫,甚至曾長居阿拉木圖的蘇聯歌手——維克多崔(Viktor Tsoi)看成是特殊年代的口欲期小孩,所以童言無忌—那麽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是多麼的可憐和狂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