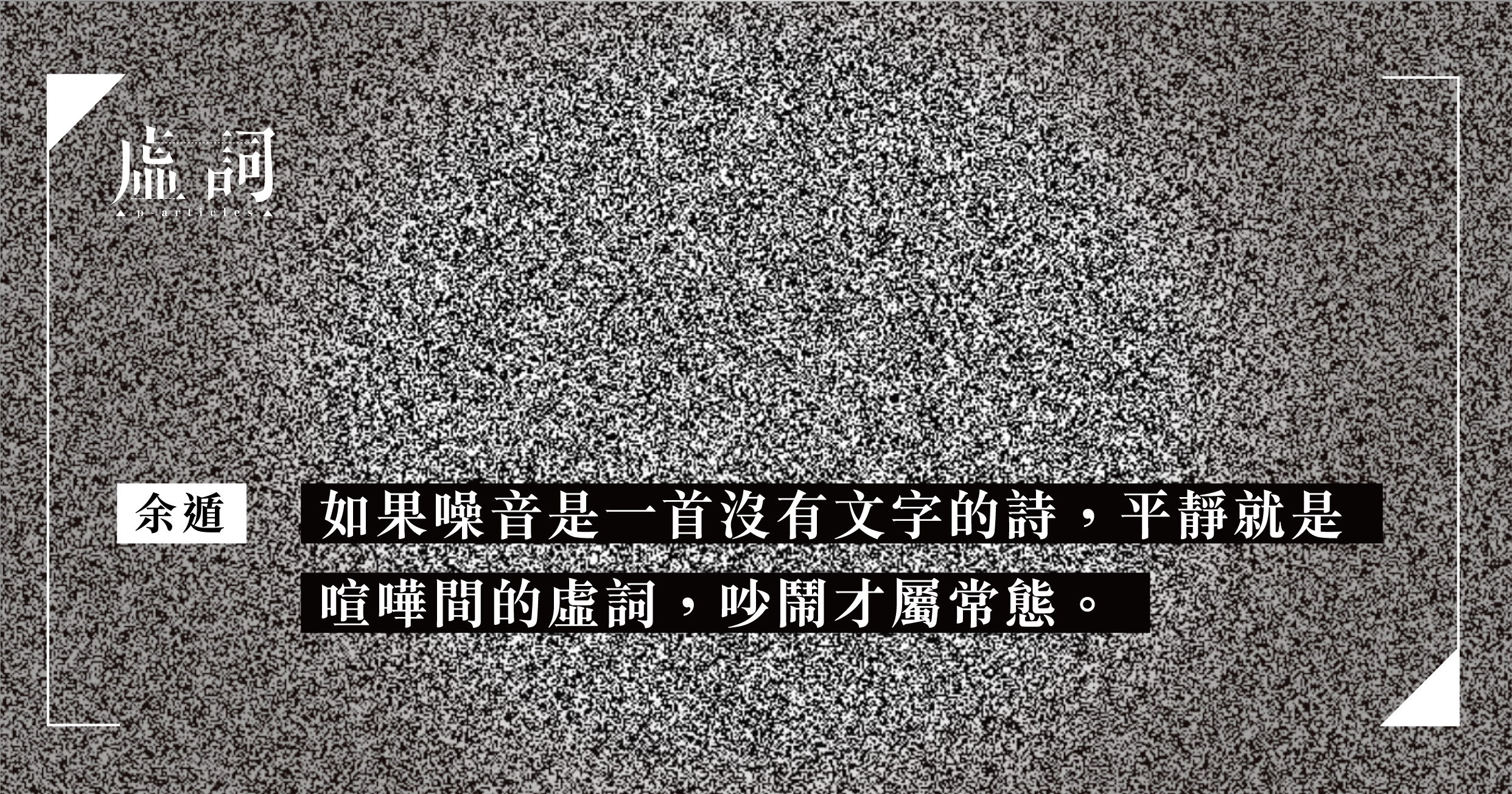噪音
人類總愛緬懷過去,嘗鮮時也念念不忘那口「古早味」。從前鳥鳴山更幽,詩人墨客以蟬噪洗心更是養氣之道,英文有palaeolatry一字來形容對遠古的膜拜,可見心同此理。我們未出娘胎前已在母體內聽盡音聲,一生長在哭鬧中與世界共鳴共震,除非天生耳聾或是避世遁居斬斷六親,否則現代人談死生孤獨,只是胡扯。人不想看東西時可以闔上雙眼,不想說話吃喝時可以閉嘴,聞到異味時更可以絕息閉氣,唯獨一雙耳朵沒有門窗,廿四小時迎賓,中國人說話大聲,掩耳亦難防迅雷,中氣十足乃健康的標誌,安靜又如健康的身體,失去時才會知道是何等重要。
現代社會的麻煩不止會自找上門,更有方法入屋上床,鳩摩羅什「誤譯」的觀世音比玄奘在《心經》中正譯的「觀自在」更能反映時代思潮。大廈高樓的建築模式早已跟隨蜜糖農場的美學風格:薄天花配矮樓底,層層疊層層,每戶小室都變成共鳴箱,沖天怨氣失去緩衝,大事瑣聞無不穿牆過壁,聲聲入耳。城市綠蔭之地又似中年男人的光禿前額,覆蓋面積日漸稀疏,港人上班放假都愛擠成一團,大家在磨擦中忘掉生活的藝術,不知不覺間又學會應付生活的藝術,香港這顆東方彈丸豈能不熱鬧。
這場「流動的盛宴」,賓客們恣意闖入生活中的「店舖後間」(arrière-boutique),何須理會你感受。噪音就是城市旅人(flâneur),長街陋巷無孔不入。時裝店例必播放節拍強勁的音樂,交通工具上的廣告更令乘客明白在疲勞轟炸下的十秒鐘比永遠更漫長,行人專用區的四面楚歌更是名聞中外。聽過金曲後才知道何解斯多噶學派要追求沒有激情搔擾的「無感」境界(apatheia),伊壁鳩魯派的哲學家更以「無擾」(ataraxia)為人生目標,如若他們穿越時空來到旺角,天知道會否影響日後哲學的發展方向。
噪音劃下兩個圓:主觀的和客觀的交接部分就是移情作用的界限線,當中更有小部分屬於《噪音管制條例》的適用範圍,無奈自身安寧與別人的快樂之間永無相交點。錢鍾書在〈通感〉中以聒鬧帶出詩文描寫手法中的「感覺挪移」之道(synaethesia)(《七綴集》),聽覺和視覺之間的「通財之宜」豈只是聯想感受或藝術手法而已。聯覺之人(synaesthete)六根溝通不受意志所控制,吃炸雞也能嚐出味道間的刺點(punctum),天賦異稟者更是牽一髮而動全身,裝修師傅隨意鑽牆也能搗出五臓六腑中的萬條小蟲。正所謂財多身子弱,他們可能只盼五鬼快來運走通財,多多益善。
如果噪音是一首沒有文字的詩,平靜就是喧嘩間的虛詞,吵鬧才屬常態。明槍已經難檔,最狡猾的噪音更像奶奶的老婢女,鐵心不會隨傳隨到。樓上孩童練習操兵,但覺得步法有《胡桃夾子》中薑媽媽(Mother Ginger)那幫裙底孩子的功架,不知他們日夜踩地究竟慶祝何事(ruffing)?英語有epicaricacy來形容幸災樂禍的快感,德語亦以Schadenfreude來形容這種幸福感受,不遑多讓,德諺有云:「幸災樂禍真極樂,皆因此從心坎來」(Schadenfreude ist die schönste Freude, denn sie kommt von Herzen),日夜身處在強迫性的「去敏療法」(flooding)之下,世人不是對聲音麻木就是格外敏感。話說回來,人家也未必全心整蠱,甚至可能只是對其所作所為不痛不癢,「鈍感力」不止內敷還可外用。如果「鈍感力」是身處亂世的眾妙之門,「過敏力」則可算是自製地獄的無上神功。過敏之人日夜身陷囹圄,全身細胞都是放大鏡,半夜廁所傳來水滴聲也宛如凌遲苦刑,他者無門可進,自身無處可逃,一茶匙一茶匙去品嘗這種生命中的鹽(le sel de la vie),只會愈吃愈咸,愈咸愈喊苦。
「失其守者,其辭屈」,真相又不聰不明,大多時候選擇沉默。苦主在恐懼與憤怒交煎下發聲投訴,只能算是繆斯借人類之身來唱頌生活的無奈與不幸。管理員忙著與周公及摩耳甫斯(Morpheus)竹戰,吃租者對任何投訴更是愛理不理,自住業主猶恐門前雪瓦上霜,轉念想起愛鄰如己的教訓,噪音來訪時有怨無路訴,《伊利阿德》(Iliad)開首的「憤怒呵」也難以叫出屈積心底的不滿。亞里斯多德在《詩學》第六卷及《政治學》第八卷中指出激情能使精神得到淨化(katharsis),此詞更有淨滌和澄清的意思。(苦主)終日滿腔哀怨,(不妨以怒氣為藥,借如火激情修煉內丹或可更快到達坐忘大同的境界)。
任苦主舌燦蓮花,設訴內容始終萬變不離其宗。聆聽訴苦彷彿是在閱讀類型小說中的人物故事,如果語言是真實的影子,複述就是影子的影子,當情節已成俗套,談話雙方都能看出故事中突起的建構,膩滯不平處是何等眼熟。戒酒聚會中的史卡德(Matthew Scudder)曾經說過:「今晚我只聽不說」,朋友得悉怨情時大多觀棋不語,嘴臉恍如法國大革命時期在斷頭台旁邊玩針織的婦人(Tricoteuse)。羅馬神話中的門神雅努斯(Janus)提醒世人一個銅幣總有兩面,(《莊子》中就有卮言一詞以申此理)。事件如果是泥膠,解釋就是說話人的巧手,豈能盡把說話當成真相?聽者除了保持緘默之外,或許應該反問對方是否幻聽,畢竟吳爾芙(Virginia Woolf)也聽過小鳥以希臘語引吭高歌,噪音或許是香港郊野公園中經常出沒的「老虎」,猛獸如神無所不在,正如波赫士詩作〈另一隻老虎〉(El otro tigre)所言:牠不在詩詞之中(el que no está en el verso),試圖抓獲捉不到的東西只是在虛空中捕風。
王爾德(Oscar Wilde)的「壓抑美德組織」成員(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rtue)遍佈全球,總部則設於香港。成員都不喜歡認錯,當被指責時大都選擇顧左右而言他,然後問對方憑甚麼拿石頭來丟我。太易認錯之人又會被視為人格障礙者,至此才知道甚麼是左右做人難。中國人喜歡探討禮、樂、法三者之間的關係,各家哲學的爭論更是無日無之,書中不斷求索道德的文、體、用,見解日新又新,書外是否言行一致卻是另一回事。聾的傳人談論甚麼都有「黐線㗎」或「犯法咩」的結論,好像異議者不是蠢蛋就是傻瓜。原來事非犯法,大家喜歡做甚麼或怎樣做都不成問題,怪不得噪音會成為問題,因為所謂的問題從來不被視為問題。
警察上門時大多勸喻息事寧人,「以大局著想」,至於閣下能否參與那個「大局」,還待事過境遷後才能明白。人家驚聞噩耗時亦請苦主反躬自省,速累招尤未必無因。《易.解卦》六三,《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可見責怪被害者一事(blame the victim)古已有之。情操高尚者更先怪責自己,人家還未亮刀就揮刀自宮,此舉免卻了不少問手鬥嘴之苦,逆向操作的思維實在難能可貴:誰叫自己生長在福地之上?福爾摩斯在《紅髮聯盟》(The Red-headed League)中說過:「真實生活永遠比任何幻想更大膽」,此事反說亦有理:現實的差勁之處比小說中的沒趣地方更是沒趣。
聽聞人生是堂課,人類總要從各種經驗中尋找意義。就算最後只能掘出荒謬,它亦會成為新的線索,指出那條尋找哲人石之路。噪音亦非全屬壞事,作家貝利(Elisabeth Tova Bailey)因病臥床一年,她在《野生蝸牛的吃食聲》(The Sound Of a Wild Snail Eating)一書中寫出微細雜聲可以動人心魄。音波振幅決定音強响弱(acoustic intensity),白噪音(white noise)除了有助入眠及紓緩耳鳴症狀之外,還能提高注意力並提升學習能力。雜訊甚至令人認識過去,展望將來,宇宙背景微波輻射(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Radiation)令人類了解大爆炸後宇宙的可能形狀,物理學家說三種模型只有兩條前路,不是大塌縮(Big Crunch)就是大凍結(Big Freeze)。澳洲昆士蘭土著以木器旋轉時的聲音作長距離溝通,莫桑比克的約奧族人(Yao people)以怪叫召喚採蜜鳥(honeybird),採蜜鳥以歌聲回應後一起找蜂巢,之後大家分享成果,雜聲中自有識者知音的喃喃私語。任何統稱都會泯滅經驗的獨特性,(《詩.邶風.終風》說『願言則嚏』,思念能引發噪音,音波更是記憶的觸媒,猶如那塊從半空中塞來的瑪德蓮蛋糕),臉譜後的臉龐馬上浮現眼前:不是去追逐那團喧天氤氳,而是想念呼出那抺煙火的人。
如果聲色迷眼,人人在鏡象蝶夢前未飲先醉,虛晃間就易錯過弦外之音。張潮說讀無字之書,會難通之解,方可得妙句參上禪(《幽夢影》),噪音也如禪宗的當頭棒,突如其來打在肩膀,肉綻中流出真實的味道,提醒大家活在當下,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小說《島》(Island)就有八哥鳥飾演樸克中的小丑牌,整天到處飛叫:「注意!就是現在!」
從意象和比喻中勾勒噪音,好比畫家以顏料迫出留白。大隱隱朝市,孤獨可以喧囂更需要喧囂,否則失掉萬華後要到何處尋找反襯的形容詞?現代人亦應該為噪音寫下禮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