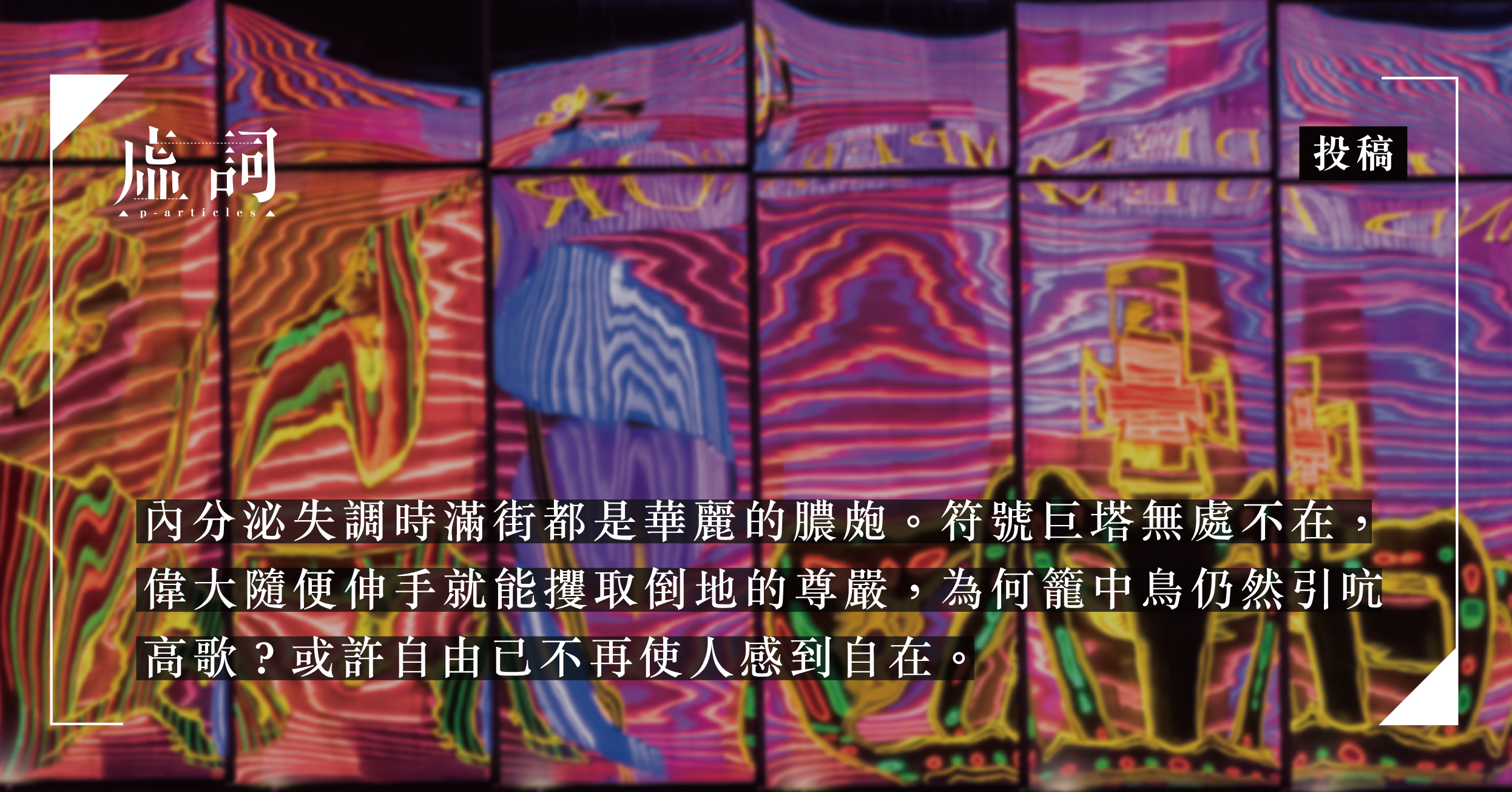【虛詞.荷爾蒙】白玉觀音
終點在設定起點時經已到達,其後走過的路,只是印證當初何以原地踏步。人類害怕忘記又怕記起,想忘記時才學習忘記,當忘記時已忘掉忘記,念念不忘是顆廢紙球,一層一層包裹叠成千層下的秘密,當內核離你愈遠,錯覺會愈加堅實。她曾說過,荷爾蒙隨血液循環全身,一生在粘膜之間消亡。血漿九成都是水,當中還有各式血蛋白、電解質、廢棄物,荷爾蒙從來不是故事的主角。得到的最終被丟棄,得不到的因為累極而放棄,只有患得患失鍛練出最甘美的士兵,奮力抵抗歲月來襲,回憶被摩擦成毛衣上的刺點,靜候扎人的季節悄步到來。還記得初見的晩上,她是高額投注區內的發牌機器。煙臭穿上甜膩的絲襪在賭桌上搔首弄姿,口沬蒸發成薄霧,籠罩圍觀者上空,射燈下賭客滿臉愁容,低頭向荷官禱告,腎上腺素隨咒罵叫喊飆昇暴跌。她的黑髪變白,白臉發亮,恍如白玉觀音靜坐波濤上,一副撲克臉只管派發撲克牌,當時我倆之間的距離,早已相隔不只一個賭廳。某天晚上,我在公司附近的候車站外再次遇上她。說她貌似誰人都是抹上恭維的侮辱,因為化學鍵合已告知心臟:她就是那個誰,她就是聖徒追求的美德,一個只有響音的名字。她上車坐下,我在隊尾向前蠕行,步步忐忑結成計時炸彈,等候登車一刻爆炸。單戀是如此精確乏味,我已摸熟迷宮中的死胡同,那堆錯發的邀請函上都印有「無此人」三個字。最終我們沒有對望,亦沒有交談,我在車內慶幸不必說將來會後悔的話,我在車外又後悔失卻後悔的機會。給生命希望,希望就來玩弄你,可想而知,希望只是自虐。生於人人必以十段文字作自我介紹的時代,解剖自我只是用文字來姦污靈魂的表演。除卻告解我不能以第一人稱訴說自身經驗,因為那是屬於詩人、瘋子、獨裁者的神聖領域。我是一扇門,阻止可憐人進場騷擾想成為可憐人的可憐人。有人忘記屈辱,有人重新定義何謂屈辱,有人選擇擁抱屈辱,甚至成為製造屈辱的工具。反正藉口與理由厚如整套百科全書,不愁找不出合用的解釋,如是我天天替罪惡吹笛,日漸成為斑駁的門飾。世上有兩種無聊:當我手握一切時,當我慾求不滿時。罰站令我感到無聊,無聊卻來教我如何觀看:不是你看到甚麼,而是你看見甚麼。站立感帶我返回現實現場,瞬間重拾對話的能力,恍似拿起玩偶時向自己說出一切的清新自然,腦內積言成畦,我把靈魂的嘔吐聲紀錄在筆記本上,隨站隨寫。此地有巴黎人和威尼斯人,沒有蒙馬特山,沒有嘆息橋,沒有歐洲的價值與精神,一齣鬧劇具備神效:昔日聖人從塔樓上被摔死後,死蔭之地就被冠上他們的名字,此地的本名又是甚麼?內分泌失調時滿街都是華麗的膿皰。符號巨塔無處不在,偉大隨便伸手就能攫取倒地的尊嚴,為何籠中鳥仍然引吭高歌?或許自由已不再使人感到自在。沉默令人退無餘地,因為發聲總被賦予在高地上冷眼的權利,我早已習慣把發聲獻給社會,行動留給他人。究竟是沉默令恣肆愈長愈高大,還是有種更驕橫的沉默令萬籟俱寂?故事尚未開始便已結束。同事的同事正在追求她的朋友,那位朋友說她突然辭職不幹,問我們隔天要否同去薦行,好事之徒早已看透我心。美麗招惹是非如同紛至沓來的情夫,當日我在被窩裡輾轉反側,大半天被各種蜚短流長消磨殆盡,最後才帶上菲林相機提早出門。過客把他鄉當成假日郵輪,居民卻把街頭巷尾視為家人,地方的意義與功能長期錯位,誰擁有定義的鑰匙,誰就有權掌摑他人。羊群被注射激素後可在柵欄內到處奔跑,經濟成為修飾萬物的燈塔,反射金光之處才是吃草的自由之地,被馴養的刺蝟自以為是英勇的豪豬,沒甚麼比守門人與全世界為敵更加可笑。偉人整天工作不休,教人沮喪,我情願虛擲光陰,捕捉在白牆上擁抱的黯色蝸牛。舉起相機,按下快門,咔喳聲剪掉身上的尖刺,迫使我貼近日常經驗劃過的鋒芒:它提醒拍攝者,尋獲與收穫之間長存私密對話,排斥異己。
「我窺見家鄉的童年照與遺像在此相交重叠。」
名勝是個沾上蜂蜜的捕獸夾,張開血口等待傻瓜到臨。我離開如鯽遊人,信步走入教堂躲避淹至的黃昏:抬頭但見彩色玻璃輕唱詩歌,音符在木漆剝落的長椅上輕舞,教堂內恰似早上六時起床的森林,只有二三遊人或站或坐,落日還在隔壁唱頌晚禱文。我坐在最後排的長椅上,見前方有女子跪下向聖像低頭默禱,我又舉起相機,按下快門。我將長鏡頭向前推近,看見頸上的紫色絲巾在她膊頭上下晃動,那抹背影令我一時忘記呼吸。她仍在低頭飲泣,我卻不敢按下快門,只能遠看她在呼吸間抖震。我再也待不下去,轉身竄出教堂外,街上石板芊芊如浮萍亂生湖面,黃昏隨晚鐘湧向失序的出口。我把各種想法包裝成精巧的秘密,急步走向相約之地。我最先到達,她姍姍來遲,那條紫色絲巾也掩不住笑靨。前此我倆從未交談,更說不上相識,兩條平行線並無「我倆」這件事,那只不過是僭稱。如今終於見面,我卻失去幻想的主軸:她好像更白皙豐潤,雙眸更大更有神采,我還未察覺種種美艷都是病徵。我們先去冰室吃雪糕,一匙一口呑下片片白雲,樂得不用說傻話。此刻我仍在夢遊仙境,說話不敢望人,她好像沒有甚麼胃口,吃飯時一伙人亂喝亂叫,未到酒館前已有醉意,其後幾位同事擠眉弄眼說要先走,留下兩個未浮大白之人向車尾揮手告別。戀愛要我扮演慈母,只問付出,不求收穫;我的心卻是個膽小後母,凡事斤斤計較,只願愛人快快歸還愛情的本利和。我曾經如此幼稚,立誓今後要熟誦她隨口亂說的話,還在筆記本上寫下句句狠毒的報應,此刻相對無言,我才發現自己早已忘掉她今晚說過甚麼話。她問我住哪兒,我故意反問她住哪一區,然後我步送她回家。同事離開之後,我們變得安靜又自在,活像兩隻小狗看見主人坐在大廳時一般愜意,她聽說我來打工後覺得有趣,問我為何選擇此地。她說,明天要去香港,也許從此不再回澳門。我一時無語。她說要去醫病。甚麼病?她指著自己的頭。穿過長風來到湖邊,她說有點累,我們便坐在岸邊石階上說些細碎,當晚結伴走過的地方,日後都已成為禁地。她刷亮手機,面露笑容,然後把它放回皮包內。她說生日快將到來。祝你生日快樂。謝謝。她說,爸爸生前是個人力車伕,當年在媽閣廟前地工作,每年又到生日,爸爸總要接她到廟前讓她當一回乘客。她跳上車後總是說去東京,因為那些卡通人物沒事就在當地街頭四處閒逛。每次聽到目的地,爸爸總會高聲說好,馬上拉車在公路上使勁奔跑,最後他們會去橋頭婆婆處吃芒果布丁。那件濕透的背心就是生日卡,車輪的鐵鏽聲就是生日歌,她覺得現正生活在旋律重複之處,渴望某種抖動能令跳針彈離唱盤。她望向夜空,猜想未來,天空卻披滿酒店的光害,不見星星。她指著遠方的地盤,說起荷爾蒙的一生,我發現她有時會側望前方物事,當時卻未猜出答案。她說,那邊好像有星星。真的嗎?太遠了,看不到。她說,閤眼就能看見,多遠也不怕,她抬頭閉目,我看見她的眼角聚滿星星。我抬頭說,看見了。她笑問流淚有何作用,是否因為雙目天生討厭光明?還是真相猶如太陽般刺眼,每次拉弓射下一顆,我們都要為此喜極而泣,悼祭真實再次消亡。我想起獨坐教堂內的白玉觀音,如若此刻我跪在地上向她表白懺悔,她會否輕吻我的前額?不一會,她起身說要回家,我跟著她前行,一路無話。她站在十字路口前,再次感謝我陪她回家。我急忙拿出筆記本,胡亂撕下一頁,在空白處寫上自己的電郵與電話。生日快樂,有空找我。她拿過我的筆記本寫下電話。她說,你回港時致電給我,我帶你重遊香港。她揮手說再會。天空漸見魚肚白。同事仍未回到宿舍,我隨便梳洗一下後攤在床上,窗外鴉雀無聲。我找出筆記本,借助手機的光線看那娟秀字跡,頓時想起在相機中晃動的紫色絲巾。我滯留在她的出生地之上,她卻將要到訪我的家鄉,兩個互換位置的異鄉人擦肩而過,最後無事的結局未算太差。
我閉上眼睛,看見她正閉上眼睛。當時未曾發現,撕下的一頁背面原來寫滿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