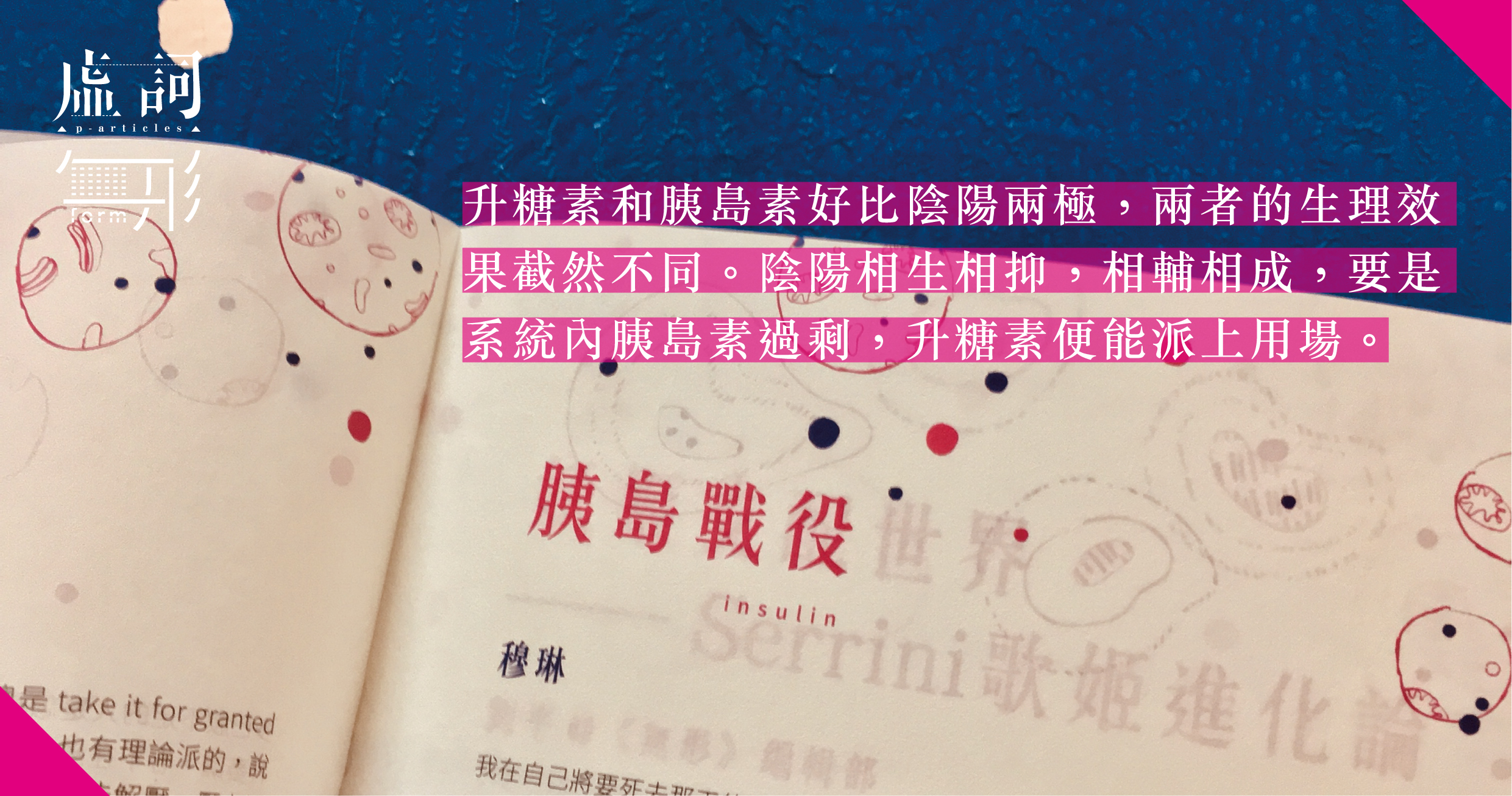【無形.荷爾蒙】胰島戰役
小說 | by 穆琳 | 2018-11-20
我在自己將要死去那天的早上,如約覆診。
「為甚麼你會覺得自己今天就要死了呢?」內分泌醫生問我。
我在五歲那年確診糖尿病。幼兒園的同學們嚴格依循時間表過活,每日24小時被精確分割成幼兒園、英語班、鋼琴班,分秒不差;我的一天則按量血糖和注射胰島素的時間割成幾塊,每天打四針,餐前量血糖,餐後量血糖。
自家胰臟罷工,外來的胰島素總是不夠貼心,有時食量或運動量不定,血糖便飄忽起來。護士教我和父母預估食量和運動,自行調節該打多少度胰島素。一開始我拿來紙跟筆做算數,老是算錯,後來我算著算著就悟了:所謂預估,重點不在猜測事物如何發展,而是找個法子使事物朝著自己預估的方向發展。從那天起,我便拋掉紙筆,換成每天起床時心算接下來那天胰島素的用量。再後來我算熟了,這項工作便提早在夢裡進行,讓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變回睜開眼睛。
「你使用的估算法確實了不起。那麼,你願不願意告訴我,為甚麼你覺得自己今天會死呢?」醫生以微笑鼓勵我繼續說下去。
我昨天──應該說是前晚的夢還很正常,那天我算出自己需要六度、八度、八度的胰島素,昨天的血糖控制也確實良好。但是昨晚,我的夢境崩壞了;在我運算途中,一個武士忽然在我面前現身,將劍遞給我,要求我為他切腹。我依照要求,將劍刺入他的腹腔。然後我死了。
「你有沒有考慮過其他解釋?比方說,你的胰島素注射器壞了,或者你今天會出現低血糖的情況之類的。」醫生握住筆,神情凝重地詢問。
我曾經試過低血糖。要是如此,我便會在前夜的夢中計算出負數;而即使注射器壞了,也不會影響胰島素用量,自然不會影響計算結果。所以,死亡是惟一合理的答案。我今天來,不是來拿胰島素的,因為我再也不需要了。我來是向醫生您告別的,謝謝您多年來的照顧。
醫生點了點頭,語重心長地說:「謝謝你專門過來跟我道別。但是依我看,你的夢還有許多解讀方式,這回的胰島素我還是照老樣子處方給你吧,萬一沒死成呢。這裡還有一支升糖素注射器,萬一你血糖低時,路人也能幫你注射。另外還有一封信,麻煩你拿去掛號。」
我拿著胰島素注射器、升糖素注射器和精神科轉介信離開診室。升糖素和胰島素好比陰陽兩極,兩者的生理效果截然不同。然而我心知肚明,升糖素不會幫得上忙。陰陽相生相抑,相輔相成,要是系統內胰島素過剩,升糖素便能派上用場;如今我的前方是一片混沌,連系統都早已崩塌失形,升糖素摻和進來,無非徒增混亂因子而已──我想到這處時,眼角餘光瞥見候診室門口、位於我左邊的座椅上坐著一名女子。第一眼。她看起來好小,幾乎是個孩子;臉部長得不太對稱,左臉比右臉圓,左眼比右眼大,左眼是雙眼皮而右眼是單眼皮,一根低馬尾靠在右頸側,整張臉向右邊收束,每邊側臉都很漂亮,合起來是個不太對稱的美女。我想正眼看進她一雙眼睛底處,看清楚她的視網膜上有沒有病變,兩塊視網膜的大小又有沒有區別。
但我沒有。我頭也不扭地往前走,任由瞥向左邊的餘光愈縮愈小。走到離開診所的大門時,我突然想借個廁所,便反轉方向,前往護士站借鑰匙。第二眼。她看見我剛才看她了,直直回望我的臉;我佯裝看不見她看見我看她,略低著頭前進,以餘光瀏覽她的雙手。我想拿把小尼龍掃子,輕輕拂過她的手指尖,問她感不感覺得到我。
我向護士拿了鑰匙,這回再也沒有讓視線飄去任何其他地方,直直走向女廁。
我按下沖水按鈕,待嘩嘩水聲響起後,才離開廁格。一走出廁格,便見到洗手枱前佇立一個小小的孤零零的背影,黑髮在頭頸交接處束了起來,辮子甩向前胸。我定睛望向洗手枱前的大玻璃窗,第三眼。女子低垂下眼,兩手裹在肥皂泡裡互相揉搓。我也不看她,直直走向她旁邊的洗手枱,將雙手置於感應式水龍頭下,一雙眼睛死盯著自己的指尖,靜候水流。我剛從廁格出來,她肯定沒用廁格,來廁所只為了洗手。我想拿根針,輕輕扎向那躲在肥皂泡裡的指尖,讓她滴落眼淚一般滾圓的鮮艷血珠,染紅血糖試紙。若是指尖的主人從此長眠不起,那我願意窮盡一切方法──為她注射葡萄糖,甚至奉獻出自己的升糖素注射器──只為了喚醒她。
「你好。」冷不防,一把聲音打斷我的思緒。
「你好。」我出於禮貌回望身旁的女子,一開腔才聽見自己的聲音已經龜裂開叉,像是自火災過後的聲帶中發出來。這是脫水的徵狀。
「你也是張醫生的病人嗎?我看你剛從診室出來。其實我是剛確診糖尿病,打針好難呀,怎麼學都學不會。」
「是,是這樣的。」
「那麼,」我在一陣暈眩中看見她的臉揚起不懷好意的微笑,她的左手猛地掀起自己的T恤,露出雪白微凸的小腹與其中橢圓的肚臍,她的右手自不知哪裡掏出一根注射器,遞至我眼前:「你介意現在幫我打一針,示範一下嗎?」
我感到天旋地轉,心跳加速,四肢發冷流出冰汗,下一秒便要暈倒在地;與此同時,傾倒在地的砂糖全體同時溶入體內流動的血液,化作甜膩濃稠的半流體,這難以流通的血液使我口乾舌燥,浸得大腦無法思考。我在狂喜、巨大的驚惶以及剩餘的些微思考能力下,突然福至心靈,悟出夢境終於在此刻化做現實:此時此刻,無論是胰島素、升糖素還是任何其他荷爾蒙,於我都已藥石無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