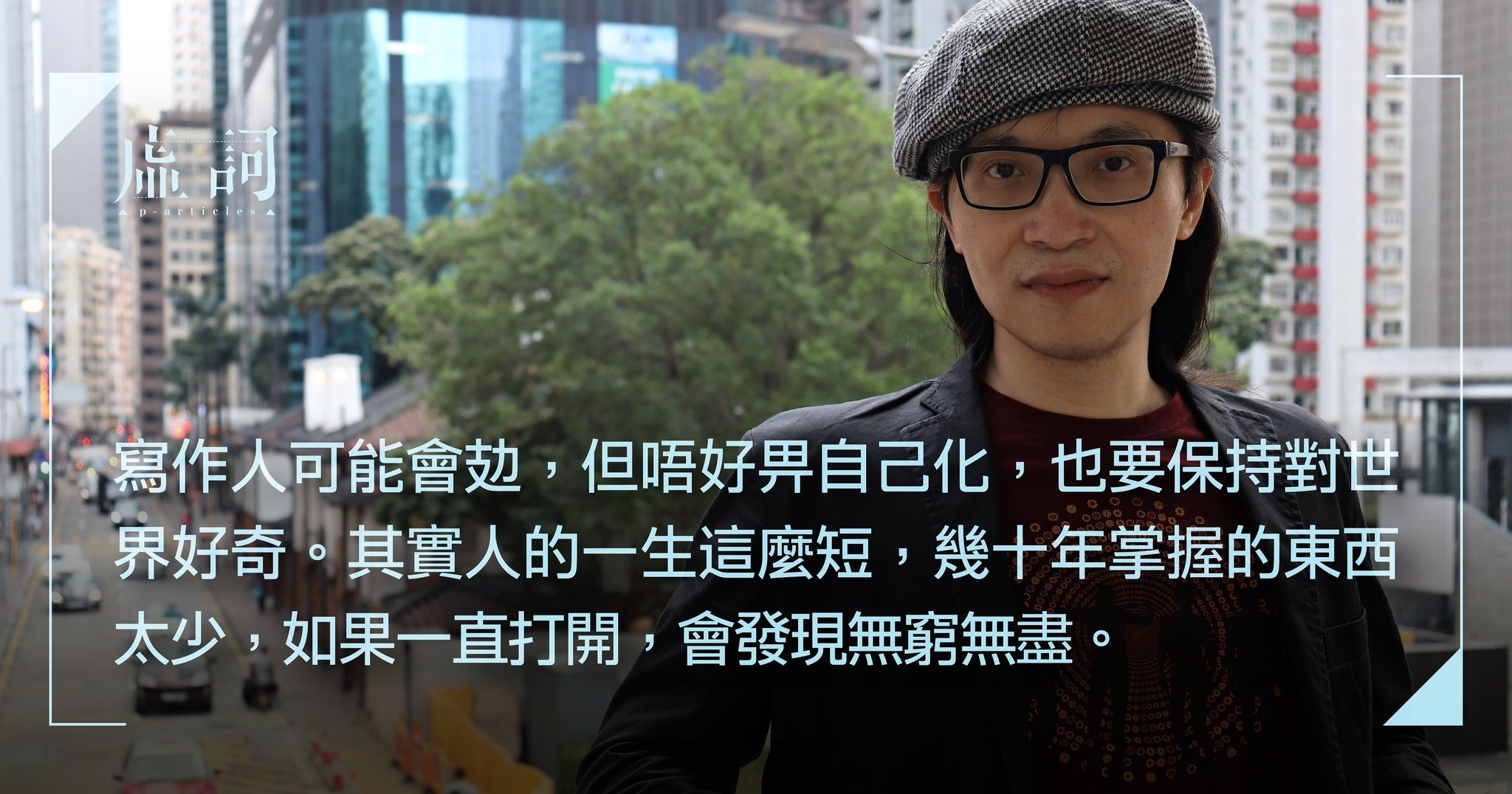訪潘國靈《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失去」是通往寫作的力量
由抗爭年走進抗疫年,兩股不同旋律相互盤纏,城內人站在風暴之眼,難免感到疲乏。多年來遊走於不同文類的潘國靈,靜下心來,重新整理自己千禧年以來有關城市文化研究的文章,編成新書《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當生命不斷面對失去,一切跌到最幽谷的狀態,頓感疲倦無力之際,失去的過程卻又迸發另一股力量,潘國靈說,這正是寫作最弔詭的地方。
社會遺忘太快,過去並非過去
從《明報》的副刊記者出身,到出版首本短篇小說《傷城記》,寫回歸前城市與成長之傷逝,一路以來的寫作,潘國靈也是城市的觀察者。這種意識的萌芽,潘國靈說是啟蒙自1989年的六四。「當時我參加很多遊行,也上過不少關於六四的延伸課程,第一次聽李怡叔就是中七,聽他講到治和人治。所以,有時social awareness的萌生很偶然,有時是社會事件所trigger,但它的萌芽必定先於寫作。」對潘國靈來說,虛構與非虛構的文學寫作,並不存在很明確的界線,重點反而在於寫作人對身邊世界事物的意識。「有時候花開兩朵,從一件事可以散落、轉化。早年我寫廟街,寫九龍城寨,小說、論文都有,所以這種social awareness一直都存在,問題在於表現手法,有時在小說,有時在公共性的文化書寫,甚至散文。」出版新書,一方面是以公共性的社會事件為主軸,另方面也是作者個人的整全回顧。重新梳理脈絡,潘國靈除了希望在這個時代做點事,也希望藉此試圖與讀者建立溝通。「2019年衝鋒陷陣,大家都有啲攰,停下來覺得可以點呢?可能文字的力量很微弱,但我都想做返啲嘢。我經常覺得,過去並非過去,即使某些generation經歷過,但社會遺忘得太快,那些以為自己經歷過的,其實只知道表面,很多過去還有待解開和發掘其中意義。」
潘國靈在書裡的序提到,1998年在科大人文學院讀書時,曾跟李歐梵教授讀著他還未成書的英文文稿《Shanghai Modern》,彼此的淵源也是由此而生。「回歸之初,我寫過上海香港的雙城特輯,李歐梵比我更早寫《上海摩登》,當時其中一堂,就是看他未成書的英文manuscript。後來彼此建立更密切的關係,是我讀PhD的中大年代,他是我法語課程的後期supervisor。雖然他是我的前輩,但有趣的是,我們屬於同一類人,大家也很open,並非恭恭敬敬。」師承這位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潘國靈自然也受到他的影響,並坦言「如非因為李歐梵,當時可能不會開始讀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這亦為他在城市文化研究的道路奠下基礎。
有心進行城市研究和觀察,潘國靈認為可分三個層次,首先打好理論基礎,其次是個人跨城市的經驗,最後是參與其中的在場感。「Urban studies是很豐富的一環,我的很多啟蒙也是來自書。我覺得文學與非文學並非不可割裂,寫城市的筆觸也可以非常文學,所謂的文學性其實滲透在很多書寫之中。」然而,單從書本吸收並不足夠,潘國靈覺得擁有遊走生活的經驗,方能以相對視覺寫出更深入的角度。「如果沒有comparative的城市視覺,有些角度也未必寫到。例如2011年我在紐約,正值當時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親身出入過現場幾次,在地知道它是怎樣的一回事,當這種佔領空間放到香港又會怎樣?裡面是否有直接關係呢?很多時候,了解自己需要一面鏡子,其他城市就是這面鏡子。」
潘國靈相當強調臨場感的重要,書裡提及的反國民教育、雨傘運動、反送中等,他都曾以不同形式參與其中,內文也收錄了不少他在現場拍攝的照片。重視這種在地身處的臨場感,只因當中有些感覺和體會,潘國靈深感單憑資料蒐集,永遠無法獲得。「事情是否有臨場感,相片對我來說很重要。寫作人除了閱讀,生活經驗都很重要,其中一部分就是社會上的經驗。你可以完全不理,但會顯得略為蒼白。親眼觀察現場狀態、自己的身體狀態、身體如何帶著理智走.臨場感記錄的筆觸可以更加細膩。無論想寫小說或記實,如非身在現場,單靠research是無法知道那些氣味。」
「物本無聲,但敲它卻會發聲」
任何事件,必然包括時地人,如何決定甚麼議題值得書寫,潘國靈認為得須回到「何謂事件」的討論,並由此說起書中收錄「控煙運動」多達五篇文章的原因。「只看表面的話,可能只會看到『2007年1月1日(開始),室內全面禁煙』,但裡面其實還有很多元素,例如煙的圖像、歷史性、空間、形象、階級性,以至『控煙條例』為何會在香港成為中國第一個試點,背後原來跟聯合國的公約有關,牽涉其中的也非只有香港,而是全球global health的重要議題。」即使如斑鳩在商場築巢、石牆樹遭殲滅等社區保育議題,潘國靈都能由小觀大,一葉觀秋,看到它們放諸城市的荒誕和重要性。「所謂抗爭,有時並非直接地抗爭那事件,而是明知我們的故事將會被改寫,民間聲音繼續肯寫,依然有人做記錄,其實也是種堅持和抗衡,所以選擇收錄的文章時,也想收納某些較另類的事件。儘管看似小事,但擁有人文關係的城市,如何處理它們是個很重要的議題,對我來說亦非地區性,而是人與動物和大自然的關係,同樣屬於城市的一部分。」
笑言自己是個「儲物狂」的潘國靈,歷年來不少書寫也與「物」有關,潘國靈更提到曾有意為這本書,找個空間舉辦實體展覽,展示自己過去儲集過的物件,只是單靠一人之力太費功夫,最後才沒成事。「我有想過可以隨著這本書,找出儲低過的相關物件作展覽。我儲了很多有關六四的書,包括當年的報紙廣告、歌曲和概念大碟,雖不敢說全部物件都有,但始終需要可觀的空間作為展覽之用。」滿足自己的儲物癖以外,「物件」對潘國靈來說也是一種痕跡,在他過往所寫的《消失物誌》、《靜人活物》等,均可見「物」在其眼中的重要性。「當記實貫穿文字,非文字的一面就是物件。物本無聲,但敲它卻會發聲,透過物件會出返好多可能性。」
寫作往往建基於「失去」
訪問當日,潘國靈正好到酒店暫住幾天,隨行帶上好幾本書和雜誌,閒時閱讀,也為寫稿,其中的讀物之一,包括以「終結瘟疫」為專題的《國家地理雜誌》。原來,這才是他疫情至今以來,首次落筆書寫這個主題。「今次很奇怪,SARS寫過很多文章,但這次明明很多題材想寫,卻一直沒有開筆,我自己也在思考,點解呢,我發覺可能因為太複雜,很難向其他人表達香港如何由抗爭年走到抗疫年,病毒也加添了很多政治上的因素,香港比起國際的處境更加複雜。」疫情以外,《國安法》衍生的寒蟬效應.對寫作人與出版業帶來的衝擊,城內也愈見明顯。艱難時代,書寫還有甚麼位置和力量,潘國靈坦言自反送中運動以來,內心不斷自我質疑與反思。「很多東西要縮的話好容易,對於我這些作家,確實也有部分板塊的轉動,唯有見步行步,as long as有個空間都寸土不讓,守得幾耐得幾耐。」
生命中不斷面對失去,正如失城的議題,也非現在才感覺得到,只是這兩年意想不到的急劇變化,讓我們更加確切感受到各種逼在眉睫的失去。「對於寫作,甚至其他方面,沒有人希望看到這些事情發生,但它卻會trigger很多可能,成為通向寫作的力量。無論公共或私密書寫,那些因創傷而消失,或某些東西沉落而出現寫作的雙節奏,都貫穿在自己很多作品裡面,對我佔有很重要的位置。」無論個人抑或社會,當跌到最低沉的狀態時,潘國靈覺得往往能迸發出另一股力量。「寫作是很弔詭的,往往建基於某些東西的loss,過程反而會出到創作的力量;又或者有些東西跌到很幽谷的隧道,反為寫得出人性的深層,我長久以來都帶著這種心態。」
寫作至今超過二十年,依然持續關注身邊新事物,潘國靈笑言自己「某程度都幾唔長大」,但也唯有保持著這份最原初的心,才可讓他對世界抱懷好奇的心,一直如此書寫下去。「寫作人可能會攰,但唔好畀自己化,也要保持對世界好奇。其實人的一生這麼短,幾十年掌握的東西太少,如果一直打開,會發現無窮無盡,也要知道有些議題,年輕人的筆觸會寫得更好,我覺得寫作人都要有這樣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