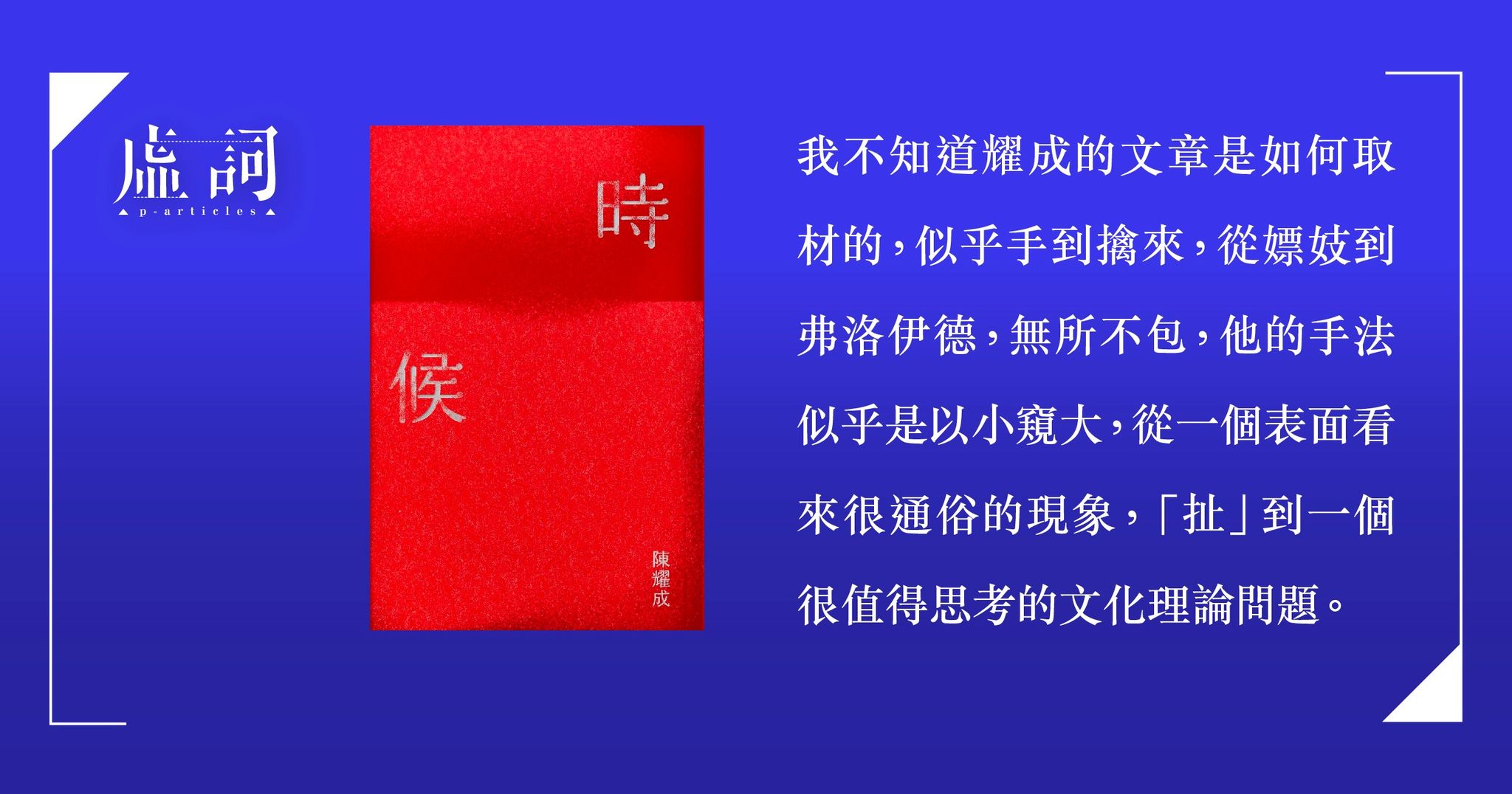【新書】散文集《時候》序——多才多藝的文化人陳耀成
書序 | by 李歐梵 | 2023-04-26
陳耀成(Evans Chan)是一位奇才, 他身兼多種身分:紀錄片導演、專欄作家、橫跨香港和紐約的知識分子、受過高等理論訓練的學者(曾在紐約著名的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和芝加哥的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深造, 得到碩士和博士學位),他不僅是「華文世界的最具創意的要角」(白睿文語), 也是中英文兼備,活躍於香港和紐約的文化人,他曾訪問過美國當代最著名的才女蘇珊桑塔 (Susan Sontag,1933-2004),並且編過至少一本她的論文集。最近幾年他拍的幾部別開生面的紀錄片更使得他的聲名大噪,例如紀錄香港社會運動的《撐傘》(Raise the Umbrellas,2016)和《我們有雨靴》(We Have Boots)。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康有為紀錄片:《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和關於香港名作家董啟章的《名字的玫瑰 》,我在後者片中接受他的專訪,親身經歷了他的拍片過程。
說起來我和Evans (這是他的英文名字)的緣分,卻是從美國學院開始的,記得有一次他到我的辦公室來看我,我們不知不覺地高談闊論,當時我就覺得他認識很多美國學院研究中國的學者,說起話來引經據典,儼然像是一個同行,對某些歷史問題更是如數家珍。後來我出席他在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演講,宣傳放映他新出籠的康有為紀錄片, 在座的都是研究近代史的學者專家,他講完後大家群起而攻之,爭論的焦點就是辛亥革命後是否屠殺過滿人的問題。我在聽眾席上冷眼旁觀,卻發現他依據的是幾位美國「新清史」學者的近著,我對此毫無研究,沒有發言資格,然而在座的學者沒有任何人討論《大同》這部影片的藝術成就,何況電影(即使是紀錄片)並非歷史文本 ,一個電影從業者大可追問:什麼才是歷史真相?什麼才是藝術呈現 (representation)? 二者的關係又如何?然而陳耀成還是保持君子風度,事後還向各位歷史學者致謝。
一個紀錄電影的「作者」如何重塑一個歷史人物?關於康有為的文字資料很多,但是影像資料 (如照片和當時的紀錄片)絕無僅有,即使找到少許也殘缺不全,這麼辦?一般紀錄片導演的手法就是訪問大批專家或與當事人相識的朋友和後代,作密集訪問,也有的導演從大量文字資料中提煉出自己的一套看法, 唯獨陳耀成發明了第三種方法:請專業演員去模擬演出歷史的主角,外加旁白和訪問。《大同》中的那兩位香港演員廖啟智和陳令智(分別飾演康有為和他的女兒康同璧)就是一例。令我更刮目相看的是該片的敘述者江青的演出,這位我稱之為「俠女」的昔日影星和舞蹈家長年住在瑞典,那是她自願的,因為她嫁給一位瑞典的醫學家,她的經驗和康有為被逼出來的流亡經驗形成一個微妙的世紀對比,也凸顯了康有為鮮為人知的一面。不少評論家對這種作法頗有微詞,然而我是贊成的,原因之一就是陳耀成為紀錄片開創了一個新形式,敘事者也可以是一個演員和受訪者,代表一種主觀視角。我認為即使紀錄片也無所謂「客觀」這回事,它免不了代表一種觀點,只不過如何把這個觀點呈現出來,方法卻各有不同。其實陳耀成更注重意象和戲劇性,《大同》幾乎可以被看作一部劇情片(原來陳耀成就拍過數部劇情片),以演員模擬歷史人物,事實上也是一種「後現代」的手法,從後設的「電影眼」中看世界。
董啟章的紀錄片又是一個真人真事的例子,片子開頭的場景是一個創舉: 導演讓這位作家坐在香港的老電車頂上談他的身世,同時影像紀錄的是瞬間即逝的流動香港夜景, 人物和影像融在一起,形成了另一套紀錄片美學, 與董啟章的作家身分和創造出來的小說世界恰好呼應。 當耀成訪問我的時候,他事先早已安排在中文大學的新亞圖書館進行,把攝影機放在一排排的圖書前面,讓我隨意發揮對於董啟章作品的印象, 我知道拍完後他會花很大功夫做剪接,把這個小片段融進他的影片敘事韻律之中, 就像在寫一篇散文,表面上形式很隨便,其實不然,這就是陳耀成紀錄片的魔力。其他導演也用過類似的訪問手法,端看片子剪接後變成什麼樣子。我認為耀成所有影片的特徵就是風格,英文叫作style, 也是蘇珊桑塔常用的字眼。他深諳電影藝術本身的形象魅力,然後用於記錄人物或現實,因此也與眾不同。
寫了這麼多題外話,原因無他,就是為了向港台的讀者介紹這位或許大家還不太熟悉的作家導演, 也算是受他所託,為他的這本雜文集《時候》寫的一篇小序。這本書的內容可謂五花八門,包括他早期和近期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表露出他的才華的另一面:專欄作家和影評人。我瀏覽後的初步印象是他的語言風格和他的取材,這也是在香港作專欄作家的必備條件:文章必須通俗易懂,也要知識豐富,才能迎合香港讀者的各種口味 ,而且要寫得快,按時交稿, 沒有太多時間琢磨字句。 這當然是我個人在香港寫了多年專欄文章的經驗之談。 我不知道耀成的文章是如何取材的,似乎手到擒來,從嫖妓到弗洛伊德,無所不包,他的手法似乎是以小窺大,從一個表面看來很通俗的現象,「扯」到一個很值得思考的文化理論問題。我個人最喜歡看的還是他的電影文章,他回憶義大利導演貝托魯奇 (Bernardo Bertolucci,1941-2018)的那篇長文, 我讀後大為佩服,也感嘆不已。這位大師級的導演,也是一位最引人爭論的藝術家,我也曾有幸和他見過一面,但沒有機會長談,所以很羨慕耀成的好運,竟然和他談了一天。文中對於貝氏的名作《同流》(或《同謀者》,The Conformist) 的分析,從弗洛伊德的理論切入,挖掘男主角被壓抑的性向,我看此片數次,竟然完全忽略了這一面,不禁連想到他的巨作《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內中也隱含了政治和性向(女性)的描寫, 耀成所尊重的李翰祥絕對想不出這種手法。陳耀成對於貝托魯奇的仰慕,除了出自同行惺惺相惜之外,還包含了二人另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知識分子型的導演,貝托魯奇更是義大利導演中的菁英知識分子, 記得我在北京第一次隨著文學評論家李陀和他見面時,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很寂寞,因為還沒有見到這裡的知識分子!」當時他正在北京拍攝《末代皇帝》。
陳耀成為香港民主運動拍攝的兩部影片,曾經極受注目,如今卻給他惹上了更多的麻煩,據聞現在連香港也禁演了。似乎沒有人提到他在世界各地參加影展大受歡迎的事實。他最近一次來港的目的是參加港大主辦的台灣女作家邱妙津學術討論會,我看過他為這位傳奇女作家拍攝的紀錄片《蒙馬特之愛與死》,又是一個關於性向和文學藝術的題目,表現得更別開生面,我本來答應參加作講評人,然而這個會議因為疫情取消了。
陳耀成是香港人,雖然長年住在紐約,卻對香港這個城市魂牽夢縈,幾乎每年都返回香港一趟,參加電影節和其他學術活動,幾乎每次回港都和我和妻子見面,最近一次來港,也約我和妻子吃飯,我們在餐桌上相談甚歡,他再三勸我們打防疫針,我當時還猶疑不決,好在聽了他的勸告。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是Omicron瘟疫席捲香港的時辰,在一片風聲鶴唳中勉強寫下對這位藝術家朋友部分作品的感想,拉拉雜雜,不成敬意,希望耀成和本書的讀者鑒諒。
李歐梵
2022年3月7日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