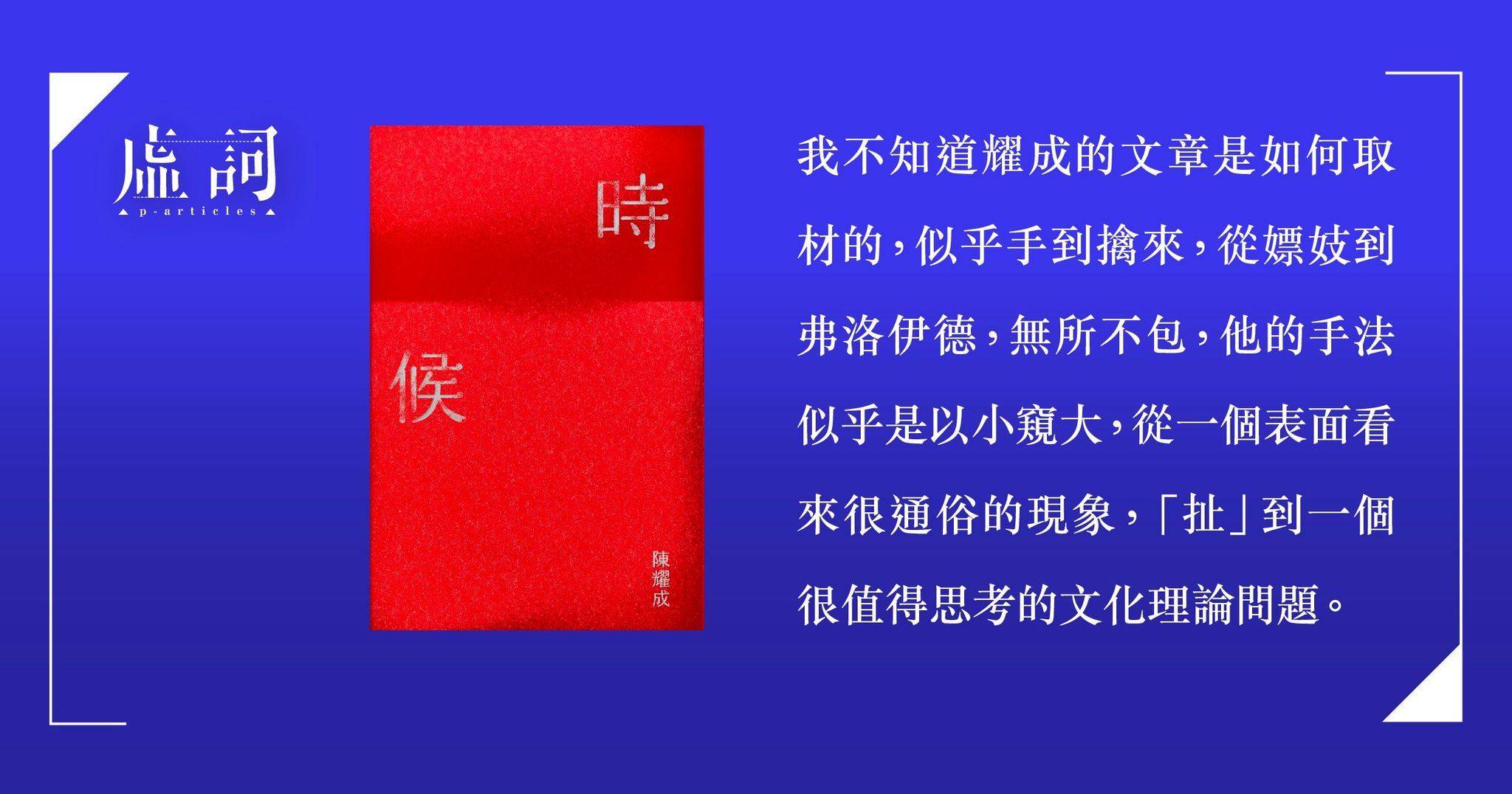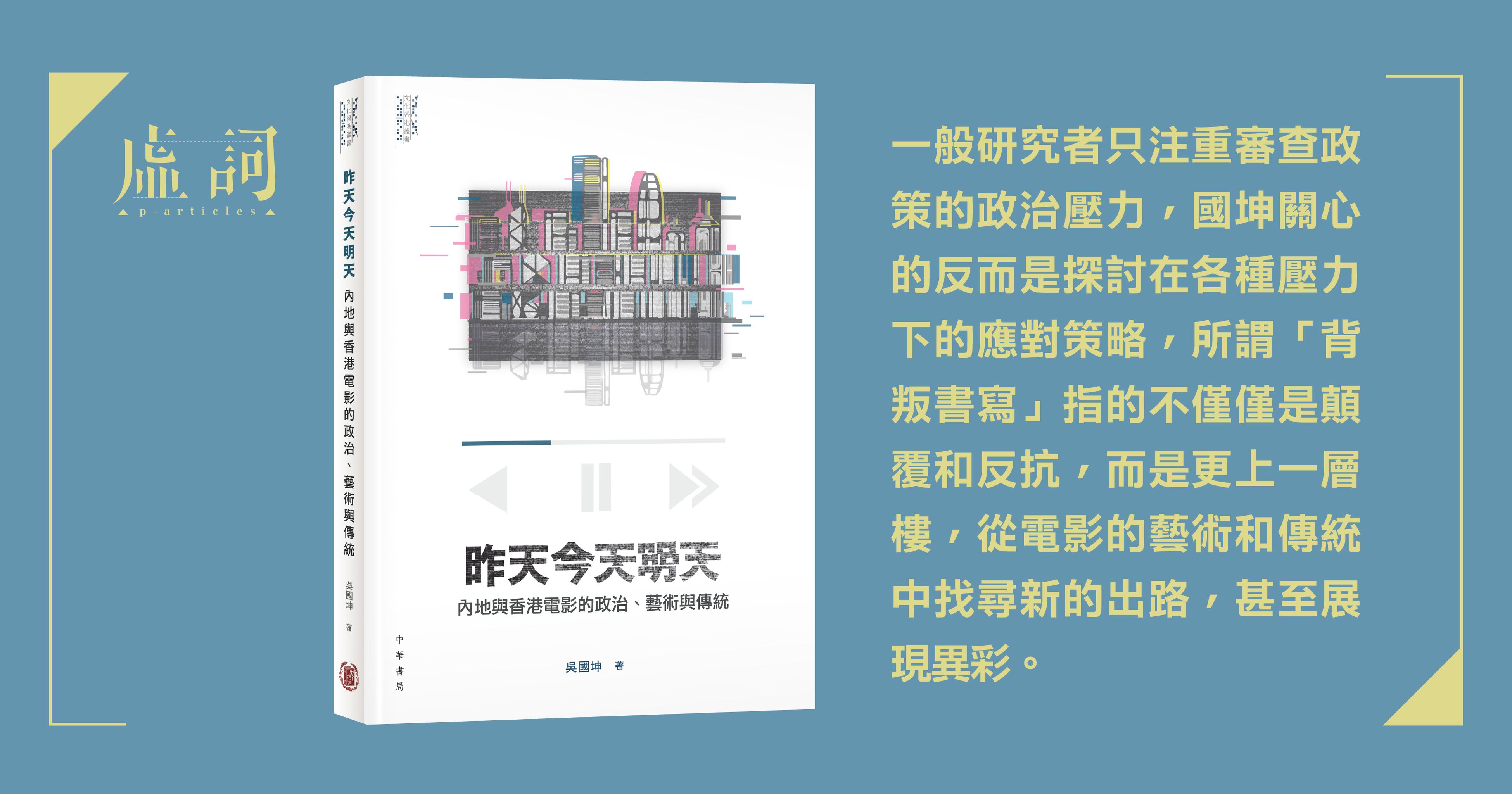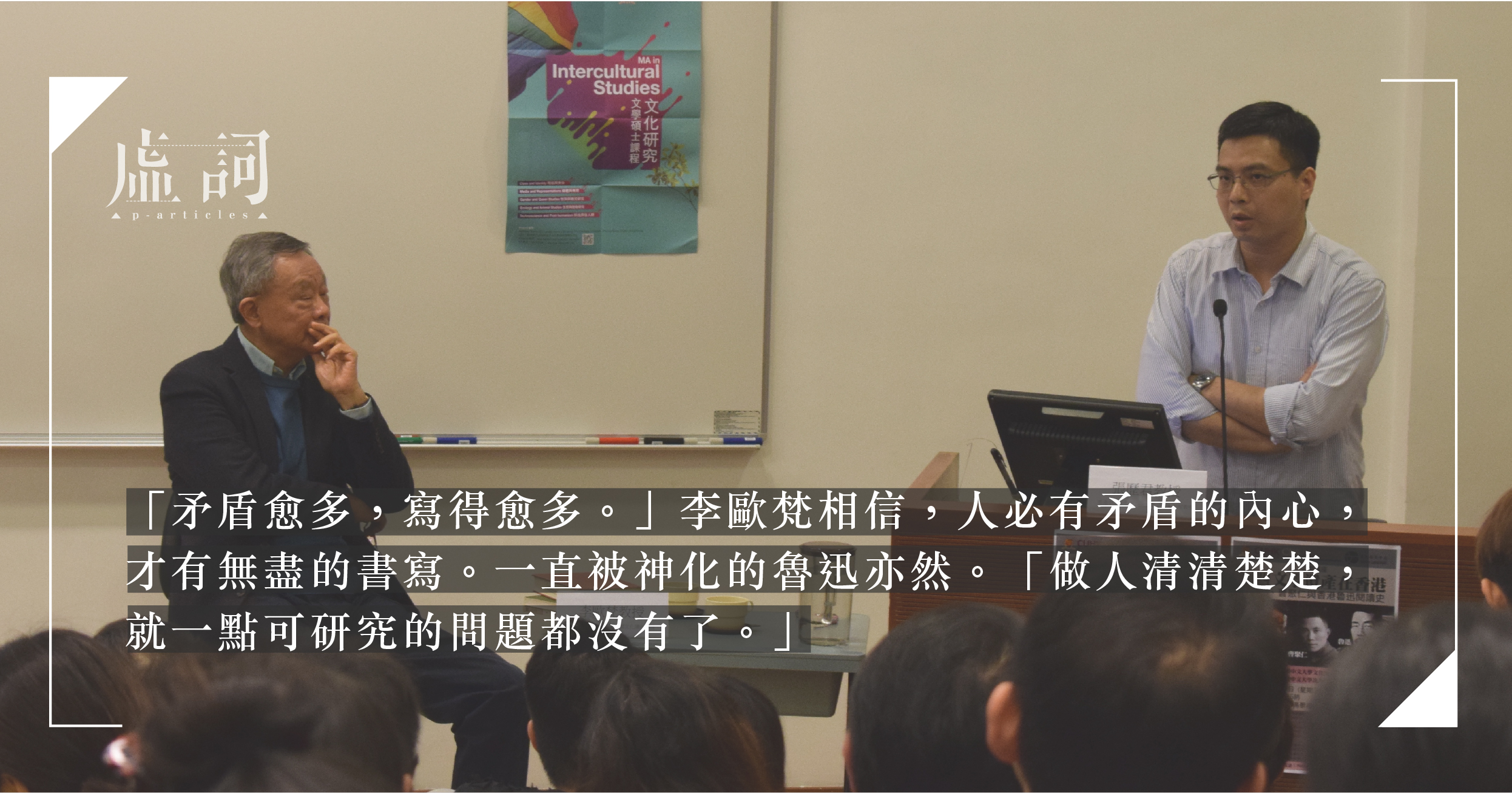SEARCH RESULTS FOR "李歐梵"

在李歐梵教授的客廳聽師母講起──那些「婆婆媽媽的故事」
散文 | by 陳躬芳 | 2024-05-27
香港史研究學者陳躬芳在疫情期間,時常拜訪李歐梵教授家,與師母李玉瑩聊起各種話題。當她讀到師母的最新著作《婆婆媽媽的故事》,發現她系統地講述了師母外婆的一生、記憶中的母親及自己的生命歷程,當中敘述了外婆關於纏足及束胸的記憶,也可見「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師母也在疫情間釋懷了往日母女間的疏離。如是者,她看見師母在一遍又一遍重述原生家庭的過去往事既療愈自己受傷的內在情緒,既在提起的同時,也放下了過往的執著,更看見師母與李教授兩顆「爛縵」的靈魂仍然結伴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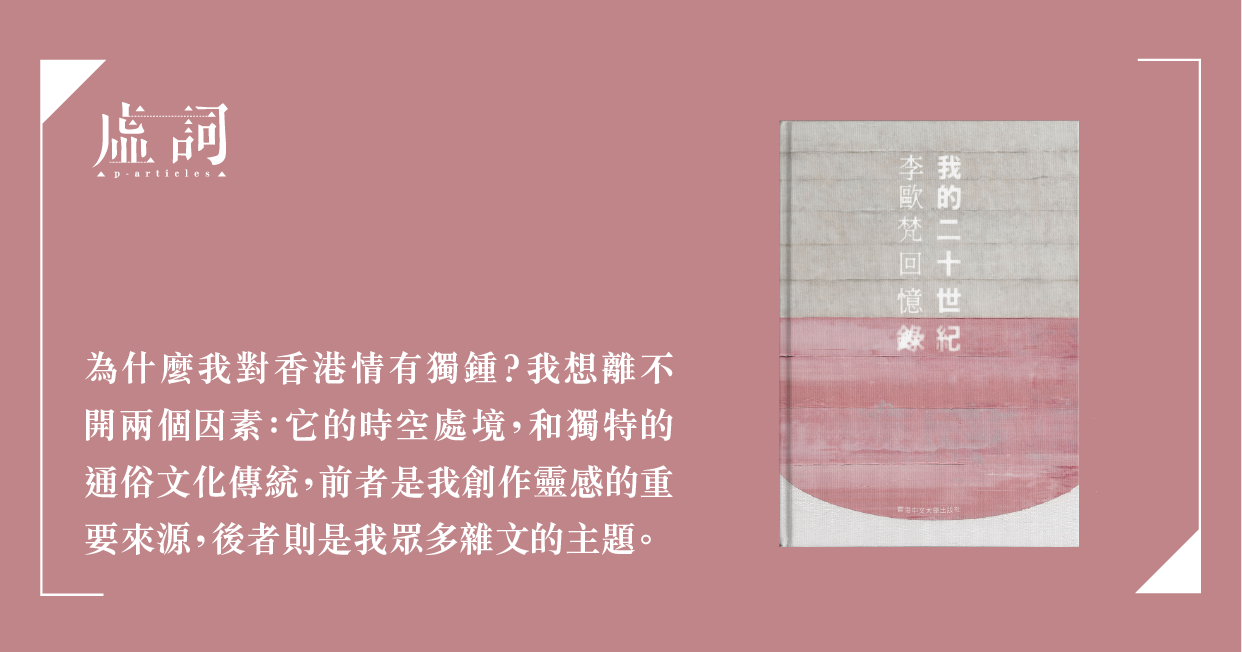
【新書】《我的二十世紀:李歐梵回憶錄》後記——我的香港
書序 | by 李歐梵 | 2023-07-28
為什麼我對香港情有獨鍾?我想離不開兩個因素:它的時空處境,和獨特的通俗文化傳統,前者是我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後者則是我眾多雜文的主題。我寫香港的都市不乏批判,特別對於它的建築,因為我對於「石屎森林」式的高樓大廈密集建築十分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因為它是人口和空間逼迫下的必然產物。也有美國朋友問我:為什麼我不在美國退休,搬到一個中西部的小城,買一棟房子,享受田園式的生活?我的回答是:這是我作為都市人必須付出的代價。香港的人口密集,然而恰是在這個密集的空間臥虎藏龍,人才濟濟,相互激盪,冒出火花。因此我願意把我的「作家」榮譽拱手讓出,獻給這些深藏於香港中西混雜的文化森林中的各路英雄。最吸引我的當然是港產影片,演藝文化也不遑多讓,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可惜的是,這些都成了歷史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