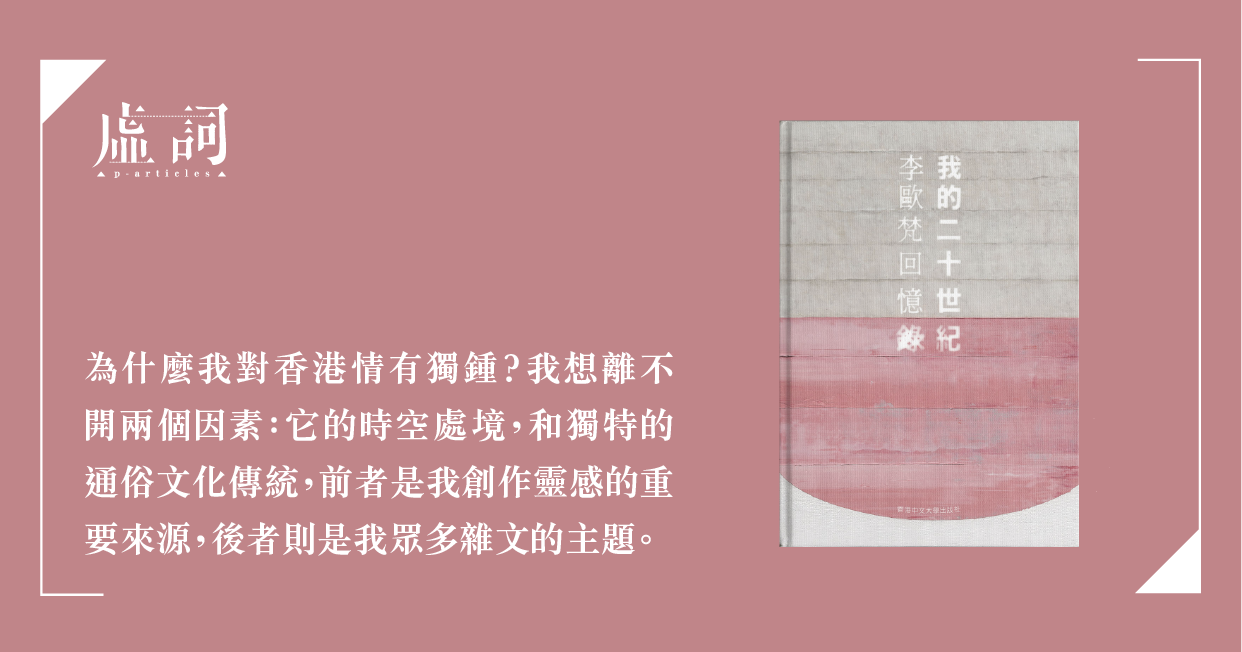【新書】《我的二十世紀:李歐梵回憶錄》後記——我的香港
書序 | by 李歐梵 | 2023-07-28
許多許多年以前,晴朗的一日白晝,眾目睽睽,浮城忽然像氫氣球那樣,懸在半空中了。頭頂上是飄忽多變的雲層,腳底下是波濤洶湧的海水,懸在半空中的浮城,既不上升,也不下沉,微風掠過,它只略略晃擺晃擺,就一動也不動了。
──西西:《浮城誌異》
寫完這一段個人成長和求學的回憶錄,深深感到我不屬於這個新的世紀,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已經無法面對將來的挑戰,我的心情沉重,覺得自己正在下沉,像西西故事裡的那塊巨石一樣。西西的《浮城誌異》用畫家René Magritte(馬格列特)的「超現實」圖,它充滿了象徵意義,西西拿來作為那個時代(八十年代)的香港的隱喻:暗示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小島的安定是暫時性的,將來隨時可以下沉到海底。仔細看會發現,巨石上面還有一個城堡,如果巨石突然下沉海底,城堡也會淹沒,那麼住在城堡裡的人不也會陪葬了嗎?如今連作者西西自己也隨風而逝了。
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左右,我開始對香港文化發生濃厚興趣,1997年香港回歸後,我特別從美國飛來香港,小住半年,返美後決定從哈佛提早退休,2004年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教職,不知不覺變成了一個香港永久居民。我的命運也和這個城市連在一起。
回顧最近這二十年的香港經驗,我認為這個城市賜給我許多,它提供了各種文化空間,讓我得以浮游於學院內外,最特別的是允許我用中英兩種語言寫作。作為一個學者,香港的大學要求我繼續用英語寫學術論文(書本已不重要),並且在歐美的一流學術雜誌發表,中文論文不過是次等。對我而言,這不是神奇的事,我早已司空見慣了。它甚至和我回歸的原意相反,我回到一個中英混雜、但華文讀者佔多數的地區,就是希望能使用中文寫作。在美國留學教書四十多年,我懼怕自己對中文寫作的能力越來越差,和對母語「陌生化」,所以要勤加練習,並且要擺脫美國式的學術英文文體,從中解放出來。別人聽了不相信,我卻認為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危機。訪港後我主動參與文化活動,向香港各報章雜誌的文化版投稿,並寫專欄。香港的副刊編輯限制我的字數,最多不能超過三千字,而且專欄限時交稿,因此我寫的文章大多是「急就章」,如此這般竟然寫出大量的雜文,大多是文化評論、樂評及影評,幾年下來也出版了二十多本文集,交給香港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因為該社的編輯林道群是我多年的好友。有人稱這種文體為「學者散文」,其實是高估了,嚴格來說,我的文化評論文章根本談不上學術,而是一個業餘愛好者(amateur)的產物。然而,不知不覺之間,我的一些學術研究的初步構思和探討,也夾雜在這類雜文之中。為什麼不可以身兼兩種角色?
這些非學術性的文章竟然受到部分讀者的歡迎,甚至香港書展當局也選我作為2015年的「年度作家」,我認為這是一種榮譽,卻之不恭,只好接受,不料引起網上一片罵聲:「李歐梵有什麼資格做作家?香港的作家很多,怎麼輪得到他?」我不禁好奇,到底「作家」是一種什麼動物?我自認不是職業作家,最多也不過是一個文化人。美國友人和哈佛的同事說我在香港如魚得水,一點也不錯,因為只有像香港這樣的多元又混雜的國際大都市,才給我這種機會。除了寫作之外,我還在兩部香港電影中客串演出:《十分鍾情》(2008)和《一個複雜的故事》(2017),名導演許鞍華還請我到她的一部影片中客串,可惜那場戲最終被導演剪去,但我已經感激不盡了。這就是我在香港做「業餘者」多采多姿的生活真實面,我不要名,更不要錢,只要滿足我的業餘愛好,就心滿意足了。
如今這一切早已隨風而逝。我有幸見證並參與了這個香港文化的黃金時代,是我這一輩子的榮幸。
二
為什麼我對香港情有獨鍾?我想離不開兩個因素:它的時空處境,和獨特的通俗文化傳統,前者是我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後者則是我眾多雜文的主題。我寫香港的都市不乏批判,特別對於它的建築,因為我對於「石屎森林」式的高樓大廈密集建築十分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因為它是人口和空間逼迫下的必然產物。也有美國朋友問我:為什麼我不在美國退休,搬到一個中西部的小城,買一棟房子,享受田園式的生活?我的回答是:這是我作為都市人必須付出的代價。香港的人口密集,然而恰是在這個密集的空間臥虎藏龍,人才濟濟,相互激盪,冒出火花。因此我願意把我的「作家」榮譽拱手讓出,獻給這些深藏於香港中西混雜的文化森林中的各路英雄。最吸引我的當然是港產影片,演藝文化也不遑多讓,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可惜的是,這些都成了歷史遺產。
香港的時空處境也很特別,它地處中國大陸的邊緣,因此「邊緣性」變成了它不可避免的立足點。香港無法與背靠的中國大陸分離,它自身就是嶺南文化的延伸,不過更多元而混雜。我以前曾對這個「邊緣性」理論做過分析,而我自己也特別喜歡站在邊緣瞭望中心,這本來也是文化研究理論的一個觀點。可惜目前自甘居於邊緣的人也不多了。
香港是今日國際大都市中鮮見的有「時間感」,從英國殖民時代的末期,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對「大限」倒數計時,1997年回歸祖國更是一個歷史性的時間座標,下一個關鍵時刻應該是2046年——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時代的結束,那時候我恐怕已經作古,不能見證了。
這些時間點讓我深受「世紀末」這個文化觀念的吸引。並非所有的國際大都市有資格被稱為「世紀末」的城市,在我的心目中,維也納自然當之無愧,還有巴黎和里斯本,這三個大都市的文化都有頹廢的一面,而頹廢在西方美學中指的並非道德觀念,而是文化上的過熟(overripe),因而呈現一種夕陽無限好的燦爛之美,在香港電影中,我覺得王家衛的《花樣年華》所要表現的就是這種味道,而張愛玲的小說如《第一爐香》和《傾城之戀》更是如此。因此我寫了一本小說《范柳原懺情錄》向她致敬,這本不成熟的小說的寫作契機——幾乎是一種突然的靈感,喬哀思稱之為「顯現」(epiphany)—— 是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歸的前夕,我特別從美國飛來見證,我感到張愛玲的鬼魂正浮遊於香港的天空,那個神奇的時辰預示了香港的「世紀末」。我故意把《傾城之戀》的時間點放在「九七」的前夕,男主角范柳原已經八十歲,早已遺棄了白流蘇,一個人住在倫敦,念念不忘留在香港的白流蘇,不停地向她寫情書。在他的第一封信中有這樣的字句:
流蘇,在這個歷史性的一刻,當香港的那一邊瘋狂地舉國同慶的時候,我終於了解,我們的文明是整個的毀掉了,我們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全完了。我們的時代終於結束,一個新的紀元即將開始。
范柳原所說的「我們的文明」就是一種世紀末的頹廢,在張愛玲筆下,它代表香港—上海「雙城記」最美好的時辰,如今連這個典故也過時了。
為什麼我的下沉感覺如此尖銳,甚至讓我覺得自己也到了「大限」,甚至覺得世界末日也即將降臨?聖經《啟示錄》中不是提到世界末日出現的四騎士:瘟疫、饑荒、戰爭和死亡嗎?如今樣樣俱備,2019年爆發的冠狀病毒Covid-19瘟疫席捲全球,香港自然不得倖免。我家禍不單行,妻子的憂鬱症在2018年復發,這一次與前不同,時間拖的很長,並且有莫名的驚恐症跡象,似乎預示了瘟疫的來臨!?我的心情頓時陷入谷底,怎麼辦?也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我的音響系統也失靈了,聽不到我摯愛的音樂,看不到我喜歡的老電影,周圍一片寂靜。幸虧兩位樂友適時拜訪,我據實以告,他們不久就送給我一個新的名貴擴音器(amplifier),我即刻決定搬家,換一個新環境,安定後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音響聽音樂。我開始聽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還有莫札特的弦樂四重奏,接著是浪漫無比的拉赫曼尼諾夫的《鐘聲》(The Bells),由此我想到希臘正教以及我崇拜的俄國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我終於復活了——是音樂和文學救了我,還有我的妻子李子玉,她的憂鬱病竟然及時開始痊癒了!
前幾天突聞西西離世的噩耗,於是我又想起《浮城誌異》中的那塊巨石。不知何故,這一次在我的想像中,城堡似乎吊在巨石的下面,而腳底下的巨浪不過咫尺之遙,當它快接近海水的時候,城堡裡面的居民突然鼓起新的勇氣,群起推起這塊巨石,使它不至於墮入海中,像氣球一樣,又冉冉上升了。
2023年1月27日
農曆歲次壬寅兔年
本文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我的二十世紀:李歐梵回憶錄》
李歐梵 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