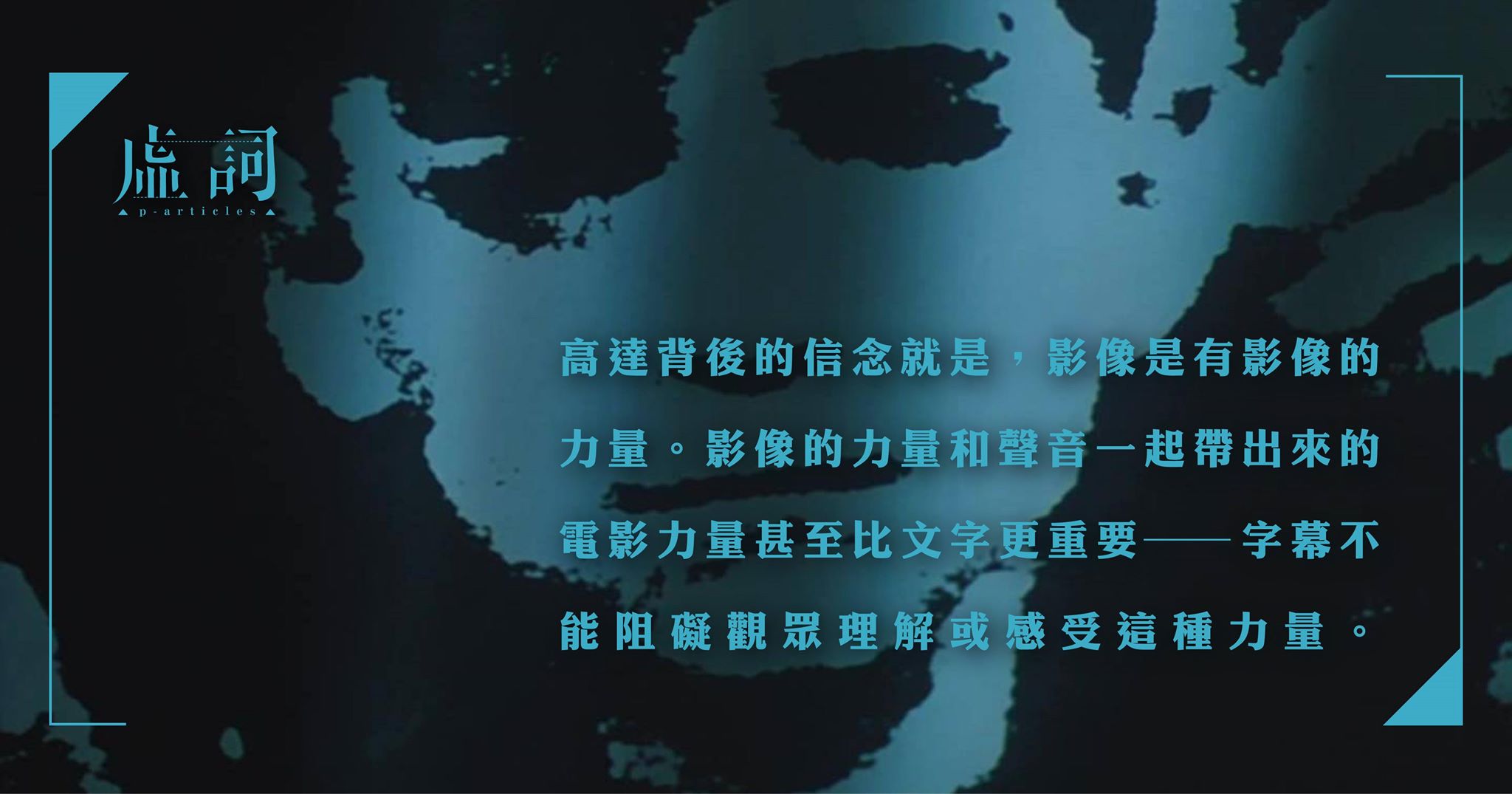「高達.電影.歷史」課程:2020年了,還看高達幹甚麼?
「一個故事應有開端、發展和結尾,但並不一定要依此順序來展現*。」 ——尚盧高達
系列電影是一個個獨立的宇宙,有著自己的一套內在法則——漫威是宇宙,星球大戰是宇宙,而知名法國導演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包括其本人及作品——其實也是宇宙。「高達世界」和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所不齒的「主題樂園」式世界有著某種令人驚訝的相似。要理解兩者的運行方式,皆必須以其世界觀作最高依據。不同的是,系列電影嘗試建構另一個現實,而高達則嘗試接近現實;系列電影的世界觀從一開始就以法則自居,由此假設好事物的應有位置。高達的電影則要看到最後,萬事萬物才會逐漸「fall into place」。
對於高達世界的伊始,我們再熟悉不過:除了多以「跳接」(jump cut)和聲畫不同步等效果來創作嶄新的電影語言、在著名影評人巴贊(André Bazin)推崇長鏡頭的年代肯定蒙太奇對電影的意義,高達更因奇特的個性與才情聞名:年少的他曾經竊取爺爺的珍藏古董書變賣,只為資助朋友拍出一部長達四十分鐘、毫無劇情可言的電影;早在其出道作《斷了氣》正式上映前,高達已因為即日創作劇本、寫不出就乾脆不拍的電影製作方式而引人注目。到了七十年代,高達給好友楚浮寫了一封四頁的信,狂批其新作《日以作夜》,指楚浮對導演的生活描寫不真不實,要求楚浮反過來資助高達本人,就同一題材重新拍攝,矯枉過正。
高達熱愛電影,向來執迷於自己對電影的既有看法。踏入九十年代至今,其狂狷的創作色彩開始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又一段沉著晦澀的哲思實驗。無論是《告別語言》還是《圖像策》,晚年高達順應著科技的發展,運用堆疊(superimposition)、殘像、3D技術編寫了一篇又一篇電影論文、詩文。那些抽象的影像堆砌成高牆;九十年代以後,世人好像忘記了高達在牆的另一邊。即使好好運用高達早年建構起來的世界觀,也似乎無法再觀其堂奧。
究竟,我們為甚麼還要看高達?香港國際電影節舉辦、以晚年高達的作品為重心的「高達.電影.歷史」課程剛圓滿結束,第二部分預計將於今年年尾面世。課程中放映了12部高達的晚年作品,包括《法國電影的兩個五十年》、《JLG/JLG︰高達十二月自畫像》及《世界電影(眾數)史》等,並設映後討論環節,介紹晚年高達的電影作法和切入點,鼓勵大眾重新觀看高達的電影。《虛詞》訪問了負責籌備及執行該次課程的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總監王勛先生以及資深影評人朗天先生,嘗試好好地回答這道重要的問題,一窺晚年高達的精神與意義。
晚年高達回歸「影像的力量」 或獲西方影評圈積極重審
從六十年代到現在,高達不曾停止更新觀看事物的方式。如今,經歷過「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的思考遞變,他要我們回到最純粹的起點。
「一般觀眾會覺得他的晚期電影抽象,但那只不過是拿它們和他新浪潮時期的早期作品比較,因而看不出那回歸具體的情狀。」朗天認為,晚期高達的藝術成就比以往的階段都要高,是經歷過「否定自己再回到自己的發展」。在《斷了氣》、《我的一生》、《法外之徒》等早期電影中,高達「用畫音分離中斷敘事逼觀眾思考」。九十年代初,高達真正進入晚年創作期,以《德國零年》、《新浪潮》等作品為界線,作品如《告別語言》與《圖像策》「根本沒有了敘事,字幕、畫面、人聲、背景聲有時詩意連結,有時相應論點拼貼,觀眾一開始便要投入思考以至超越思考,明顯比前期的舉措『前進』。」
由始至終,高達從來沒有放棄透過剪輯的力量來拓寬觀眾對電影的想像。只是現在,高達對於「具體」又有了不一樣的看法,似乎到達了一種「見山更是山」的思考狀態,要將電影減損至最本質。
「說貼切點,晚期高達是抽走了具體敘事之後,再超越形式的電影語言,回歸到最具體的光影與聲音及其變化。在其最近的兩部作品《告別語言》與《圖像策》,蒙太奇與剪接完全成為具體的藝術經驗,與觀影者的感官與直覺同步同流。由早期到晚期,初看是一場意識形態經歷與轉進,說到底是藝術的提升,電影精神辯證發展的見證。」
在3D電影熱潮來臨的時候,高達也去拍他的3D電影,但他並不是要賣弄真實——他不是要把追逐戰裡的車甩到觀眾席裡,不是要把路邊的鮮花弄成垂手可得的樣子。「我最喜歡的晚期高達作品暫時仍是《告別語言》。」朗天指,該電影對立體影像進行深刻的思考,開拓和更新了電影語言;八十高齡仍有如此創造力,實在令人驚嘆。
「到底看到立體影像,是不是就代表觀看事物的方式也變得立體?變得豐富?或是這只是假象?電影本身已經是假象,那這個是不是一個雙重的假象?」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總監王勛點出,高達拍攝《告別語言》時,用的是一部自己組裝的3D相機,從頭開始嘗試、研究,究竟3D帶出的是甚麼,人們看到的是甚麼,去辯證3D和人的關係是甚麼。「導演除了想自身或是世界上的問題,還有沒有嘗試將電影放回電影裡面?」王勛反問。「高達在創作的同時,無時無刻不在思考電影是怎麼一回事。這個世界上在做同樣事情的導演,一時三刻也想不起來還有哪一個。」
高達早在七十年代、《世界電影(眾數)史》(下稱《(眾數)史》)的籌備階段便將相機的使用類比為科學家的顯微鏡、望遠鏡等器材。他相信電影的存在是要讓他更深入地看見某些事情、哲理,而他的電影實驗就是要完成這種旨意。
但對觀眾而言,這種科學指的是一種觀賞精神,而不是分析技巧。這也是「高達.電影.歷史」課程希望能令參加者先理解的事情:要理解旁徵博引、意象紛呈的晚年高達,其實比想像中簡單,無需自亂陣腳。
「由《(眾數)史》開始,高達傾向將不同的舊片的片段剪在一起,配以不同的聲效、旁白,或影像,去作並置,以提出他的論點。但大家不應用認圖遊戲的方法去看——不要看見每一個電影片段都去想,這部戲我有沒有看過?這部是不是很有代表性?觀眾該將其影像和聲音所並置出來的效果看成一個整體。他用現成的片段做出可以服務他的論述。大家要去了解的是,即時所做出來的影像和聲音效果。」
數位影片初誕生的時候,高達便一度認為這是比菲林更優勝的媒介。菲林某程度上只容許連續性(sequential)的剪接,而數位影片則容許製作人直接在剪輯房裡將圖像堆疊、拼貼。
物像的同時顯現,是高達一直思考的問題。這從高達解釋為何自己最後沒有成為作家的話語中可以一窺:「⋯⋯當我寫出『今天天氣很好。火車到站了』這樣的句子的時候,我便會在案前坐上好幾個小時,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為甚麼我不將它寫成『火車到站了。今天天氣很好』?在電影裡,這就變得簡單得多。天氣好和火車到站是同時發生的。當中有著某種不可抗力。你一定要順著它走。」
王勛指,「高達.電影.歷史」課程的重點之一,就是要向觀眾傳授這種觀看高達的整體方式——放開懷抱感受影像的力量,是欣賞晚期高達的首要條件。這也體現於高達處理字幕的手法:即使是看The Criterion Collection所推出的權威版本,也不難發現,不少高達電影裡的字幕翻譯得並不齊全。「高達背後的信念就是,影像是有影像的力量。影像的力量和聲音一起帶出來的電影力量甚至比文字更重要——字幕不能阻礙觀眾理解或感受這種力量。」
其思想內涵之複雜,非常考驗觀眾的耐性。說到此我們彷彿記起,看電影從來不是一件速食的事,也不僅僅是電影放映時間內發生的事;電影正無時無刻地進行。「想要像看商業片那樣,一下子明白高達想說的話,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二十年後,人們似乎開始能追得上高達的腳步。孕育眾多法國新浪潮導演的重要刊物《電影筆記》去年發布2019十大推薦電影,高達的《圖像策》位居榜首,備受肯定。
王勛嘆道,高達或許實在走得很前,如今大家才開始慢慢明白過來。圍繞晚年高達的深入討論如今主要還是在集中在法國本土,但西方的影評圈如康城或是美國影評人協會(The National Society of Film Critics)亦越來越留意晚年高達的作品。王希望,當這個話題逐漸成形的時候,「高達.電影.歷史」課程能為香港觀眾打好基礎,讓他們也參與這個國際討論或思考過程。
「他一邊創作電影,一邊評論電影,一邊思考電影」
「唯一抵抗美國電影產業的——即抵抗一種統一性的電影製作手法的——只有意大利電影**。」——尚盧高達
在眾多晚年高達作品中,當數史詩式的《(眾數)史》格局最為宏大。高達早在七十年代中和和皮埃爾・高蘭(Jean-Pierre Gorin)談論電影的政治影響時,早就有了製作一部個人電影史的念頭。對他來說,這是電影的歷史和政治責任,因為電影就是紀錄——在《(眾數)史》1A中,高達認為電影之死源於有關第二次世戰的影像的缺失。早在六十年代初,高達就對真實地重現猶太人大屠殺有著迷戀,其偏執之至,令他甚至認為蜚聲國際《浩劫》(Shoah)也算不上理想之作。後來,《(眾數)史》3A《絕對的代價》開篇便對歐洲各國作出遣責,指斥其就前南斯拉夫內發生的大屠殺袖手旁觀。
法國新浪潮剛捲起時正值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高達曾因創作與時局脫節的《斷了氣》而遭受抨擊。但除此以外,高達一直是個投入時代激流的創作者。朗天指,「(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受到全歐學運和左翼革命失敗的衝擊,高達一度放棄電影,轉搞電視,原因是電影建制化的程度太根深柢固,積習難返。七十年代是電視黃金時代,讓不少知識分子產生暇想,跟九十年代中互聯網初普及的情況類似,搞了十年電視影像革命未果,高達於八十年代初重新投入電影創作,評論人會叫這時期的高達作「第二波」(Second Wave)。」
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人比高達對電影作出更狂熱的思考。除了電影的社會角色,高達還對電影的作法有著異於常人的執著。一度對霍華 ‧ 霍克斯(Howard Hawks)、奧森 ‧ 威爾斯(Orson Welles)等前期荷李活導演讚譽有加的高達,對逐漸公式化的荷李活製作也是毫無保留的作出抨擊。對於他來說,很多沒有思考價值的商業電影根本算不上電影。
「高達是一個藝術家。」王勛這樣形容,這種思考的習慣可以追本溯源至新浪潮時期養成的氣候。「其實很多法國新浪潮導演做這件事,他們本身很喜愛荷李活電影,但對法國電影歷史也十分熟悉。他們當時看世界電影潮流的時候,一方面看很多不同的電影,但另一方面也嘗試以不同的拍攝手法去突破很多成規,或是當時電影的一些拍法、想法,例如運用跳接(jump cut)、運用自然光、出街拍攝,又例在感情戲上作出不同的嘗試。世界各地都有有不同的新浪潮導演去衝擊當時世界的電影文化,但少有像高達這樣越鑽越深,將政治歷史、電影的本質、文化放進電影的文本裡面。」
到了1995年,電影誕生100週年的時候,世界各地的導演都開始開拍各地的電影史。而高達為此創作的《法國電影的兩個五十年》,又是另一場思考。「高達重要在於,當大家都使用同一種方式思考的時候,他就提供裡另一種思考方式。他在《法國電影的兩個五十年》裡詰問的是,為甚麼電影的誕生不是講菲林的發明?投影機的發明?而是將它定在第一次收錢放映的那一場戲?其實那一場戲大家慶祝的是拍電影搵到錢,是商業電影的可行。這就是他的思考方式。要思考甚麼電影是經典、該放進去之前,先要思考為甚麼我們現在要慶祝這個一百週年。」
《(眾數)史》就是他對歷史思考的結晶。「高達看的不光是電影拍得好不好,而是監製在電影中的位置。」王勛續指。「當荷李活或大製片廠壟斷了電影業的時候,新浪潮導演就提出『作者論』。提出作者論以前,導演似乎也佔頗重要的位置,但操縱電影業的其實是一些電影大亨(movie moguls)。那段歷史又是怎樣一回事?又,究竟二戰對整個歐美電影的影響在哪?」高達絲毫不諱將自己的觀點坦露人前,以電影寫就論文,王將之形容為「非常有代表性」,又影響了後人如馬克庫辛思的《電影的故事》,在電影歷史系列的紀錄片中加入個人思考,脫離以往「數白欖講經典場面」的「greatest hits」格局。
電影史本來就是主觀的。像班雅明所說的,「將過去當作歷史呈現,並不等於直接勾勒其『真實面貌』。『歷史性地呈現過去』的意思是,在記憶閃現於危急關頭時加以挪用(appropriate)***。」對高達來說,那個時代的危機就是思想的怠慢、戰爭、科技。於是他受之激發的記憶,展現一個屬於法國新浪潮導演的、深受後二戰思潮影響的影人之電影史。
「電影史有很多種寫法,有的是主觀的客觀(subjective objective),有的是客觀的主觀(objective subjective)。『主觀的客觀』指自以為客觀,但其實無論如何擺脫不了撰史者的主觀;『客觀的主觀』是指忠於自己的主觀觀察、紀錄和判斷,讓讀者意識到以至了解所撰歷史的適用範圍及限制,才是真正的客觀。」朗天如此指出。「高達的電影史就是後者,而我也寧取後者。」
人們應當習慣談論高達 「之後有沒有高達也不重要了」
「在電影面前,我們不思考——我們都是被思考的****。」——尚盧高達
推廣高達,尤其在香港,有何難度?王勛說,暫時覺得最大的難度是,大家不習慣討論高達。
「(課程中,)大家不是很敢於提出自己的想法或者困難,或許是因為怕覺得自己不夠料去理解高達。如果有更多的討論——先不說明不明白,只說感受也好——便對事情更有幫助。希望大家可以習慣討論以後,越辯越明。」
在電影面前,我們都是被思考的——要奪回思考的主權,就必須當個積極的觀眾,在電影所傳遞的信息以外進行批判。在高達看來,觀眾和電影創作者必須共同努力,才能成就一部電影。
因此,朗天表示,雖然他認同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所說的,高達的電影都是拍給影評人看的,「但觀眾不都該同時是影評人嗎?電影論文也並非止於傳遞思想,它更有利於刺激思考,導引出新觀念。帶著腦子去看電影,這是高達一直對觀眾的期許,從早期到晚期,從來如此。」
高達對電影的看法和思考幾近一種信仰體系,朗天卻不同意。「信仰體系很多時都是封閉的。但高達的作品恰好相反,看多了便會發現它的開放性,刺激觀眾覺醒、思考和開放感官。他的電影有很多參考和指涉,我們對彼有所了解當然不錯,但那也並非必要的。保持主動性和自發性,不斷讓自己開放接收新觀念新體驗,是我們看高達晚期作品的基本主觀準備吧。」
用電影寫論文、散文這回事,真的能夠有效傳播所希望表達的內容嗎?引文式(citational)的電影真的有意義嗎?對希望理解晚年高達的人來說,這些問題都不是重點。
「高達、電影與歷史這一課題,對我來說,只有一種切入方法,就是直接面對高達提供的影音本身,經歷他在創作所經歷的過程,電影和電影史都是他的電影和電影史,但謹記他個人遠遠小於電影和歷史。我們是通過他進入電影和歷史,得魚忘筌,之後有沒有高達也不重要了。」
現在,高達對我們最大的啟示是,電影原來可以這樣拍。多年後,當電影和影視娛樂的界線越來越模糊,高達將會是這道界線之存在的最大見證。王勛在對晚年高達電影的讚賞中,少不免流露出一種期許:「希望下一代不會把電影當作只是另一個娛樂媒體,和看YouTube片沒有分別。既然有一個這麼難得的藝術家一邊創作電影,一邊評論電影,一邊思考電影的時候,至少大家不要那麼快就把他晾在一旁,應該嘗試一下了解他對現在這個電影世界有甚麼思考。這可能可以影響一些觀眾,或電影工作者。」
如前所引,「一個故事應有開端、發展和結尾,但並不一定要以此順序來展現。」或許反過來看,晚年高達是開端,法國新浪潮才是終結。不管如何,高達是少有能從年少時當白紙當到老的人;很多人年屆耄耋,便已懶得從頭來過。許多人在等待改革、偶遇改革、參與改革,而高達正在改革,一直都是進行式,從未間斷。
請珍惜高達。
*原文為「A story should have a beginning, a middle and an end, but not necessarily in that order.」
**原文為「The only film, in the sense of cinema, which resisted the occupation of the cinema by America, which resisted a certain uniform way of doing cinema, was the Italian cinema.」這裡的義大利電影指《不設防城市》(1945)。
***摘自班雅明的《歷史哲學論綱》。原文:「To articulate the past historically does not mean to recognize it ‘the way it really was’. It means to seize hold of a memory as it flashes up at a moment of danger.」
****原文為「At the cinema, we do not think—we are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