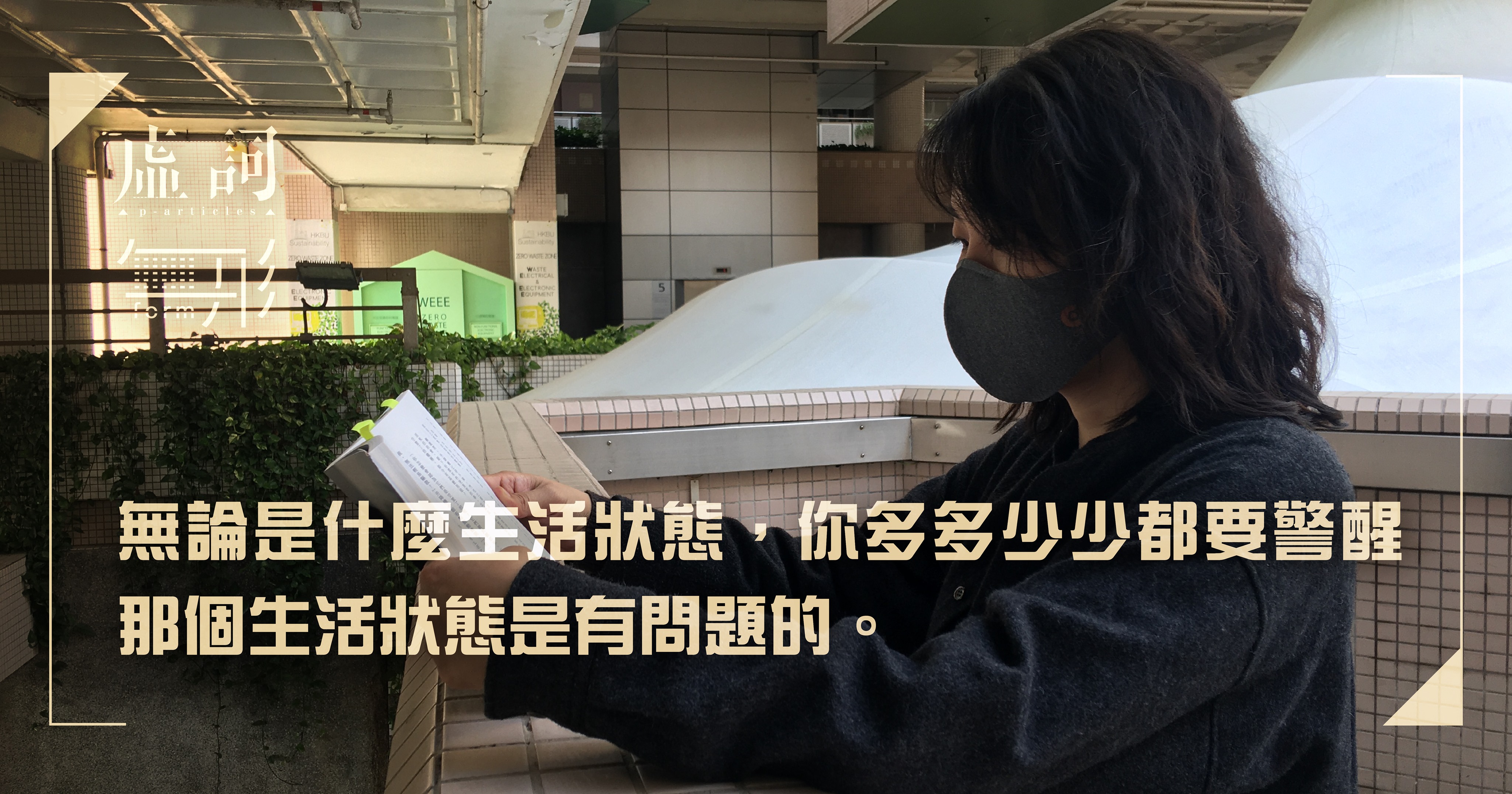【無形.初登無形也不驚】無限接近實的幻——專訪謝曉虹《無遮鬼》
在謝曉虹的世界裡,天空會露出疼痛的樣子,蓮藕會滲血;相愛的人會抱著彼此的斷臂輕掃對方的背,記得相愛;少年會在袋子裡摸到自己的身體,落荒而逃。
從二零零三年的首部短篇小說集《好黑》,到去年的長篇小說《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到今年的《無遮鬼》,謝曉虹的世界在不緊不慢地堆疊、增生,在讀者的指尖前翻繞十七年,最後總是會碰到。然後她也會告訴你,這裡沒有世界。
「我覺得,我只是用一些方法嘗試去接近我經驗過的那件事。」
謝的故事往往懸浮在生活邊緣,輕輕的一敲一槌勾出經驗的線。懸浮是排斥力,也是吸引力,她的文字同樣——被現實吸引,也排斥現實,永遠無限接近著地面。《無遮鬼》如它的先驅般,再次從這種無限接近的空隙中飛脱;但這次動盪的社會局面中,逃逸路線的終點竟折返城內,和裡面的人留在一起。
書的難題︰無意義的「喂喂」
「有沒有看過《好黑》?」對於某個讀者群來說,這道問題是個暗號,問的是一個階段。如果你有,代表你被震撼過,懂得一種濕滑而溫暖的黑暗。謝曉虹的出道小說至今還要說,因為它在《鷹頭貓》出版前定義了她一段很長的時間,現在讀起來像是她一切作品的輔文(paratext)。
即使《無遮鬼》是她在香港最水深火熱的這兩年出版的第二本書,「謝曉虹出新書」這五個字還是讓一眾老讀者激動不已——喜歡謝曉虹就像長久地看著她的背面,因為她如此不介意把故事揣著那麼久,卻某天慢條斯理地轉過面來。甚至是這次收錄在新書、十年前完成的〈月事〉,她一開始也覺得「不一定要交到讀者手中」。
「我有時覺得,有意義要出版的東西不是那麼多。……我有時覺得,大部分說話都是無意義的。」謝坐在記者對面,有點不好意思地大笑。「其實寫嘢很多時候是對我自己很重要,我需要去寫。——老實說,《好黑》出版的時候,我知道有人在寫評論,但其實我不想看。」
但十多年後,來到《鷹頭貓》和《無遮鬼》,有種私密流瀉出街道上,寫作和出版已不僅是謝對自己的交代。「這次有點不同,我想聽一下別人怎麼看這件事,因為是一些大家都經驗過的事,我想知道其他人怎樣投入他們的經驗去看.....其他人的解讀有時候會幫我去想,那件事我該怎樣去消化。」
《無遮鬼》的寫作與出版,某程度上像拿起電話說「喂喂」。「其實『喂喂』是沒有意思的,你不是想要表達什麼,你是想知道有那個人還在,他還在你身邊。我其實出這本書其實有頗強烈的感覺是這樣,想表示,我也在這裡。」
我側著身子讓出過道,在他擦身而過時,便看到一座熟悉的島瘤長在他一邊的肩胛骨上。……「你也揹著它走了很遠的路嗎?」——〈大腿上的島〉
情感作為史實
書中〈逝水流城〉部份最早構思的故事是〈甩繩洋娃娃〉,「我」駕著二手車,在深夜時分無人公路上前進,經過等待拆卸的工廠區。這和《永生情人》裡兩隻被時代遺忘的吸血鬼在底特律的黑夜中駕駛的畫面幾乎重疊,一路的蕭條風景和荒屋廢墟。只是戲裡的主人翁尚有力氣批判社會,「我」卻只能眼巴巴看著那些「神奇的表演者」攀爬過大閘,看著情人的臉「像一個水中的泡沫消融於夜之大海」,變成「妹妹」。
謝回想起故事在腦海裡成形時,那種抑壓的心情。「在社會運動裡,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樣的體驗就是,你跟家人的政見未必一樣。然後我自己駕車一個人走的時候,就會有一種感覺,不知道怎樣跟他們對話。」
在《好黑》裡,謝曉虹也寫過家庭。最為人知的莫過於〈旅行之家〉,她寫過一種並非為了掙脫牢籠的離家——只是別處有更令人嚮往的空間在。〈風中街道〉、〈理髮〉、〈關於我自殺那件事〉等故事中,「親人」在社會所規範的狹隘角色中斡旋,卻又感覺同時被剝去血緣的糖衣,回到人最會彼此顧忌的狀態。當年謝筆下的家庭正正因為沒有赤裸裸的反叛,而顯得非常反叛。
但在《無遮鬼》中,特別是〈逝水流城〉部份,對傳統家庭敘事的「反叛」似乎已不是基調。「這個運動期間,無論是自己的學生、身邊見到的人是和家人有很大的衝突。我自己也是。所以調轉頭說,我將家人放在裡面,其實是在想找一種方法去理解他們。有一些經驗是和我自己的經驗有關,但重新把它們放在一種想像的空間裡面,其實是想思考一下,你怎麼去理解這些和你想法很不一樣的人,然後可以跟他們共處。」
一不小心就會走進電視的父親、把腳掌降落在「我」肩膀上的爺爺、若無其事地喝著滲血蓮藕湯的雙親……比起批判,更多的似乎是悲哀,與一種不解中的諒解。而在這些「家人」中,最突出的角色之一,必數在〈月事〉和〈逝水流城〉中皆反覆出現的妹妹。
妹妹老早就逃出了我們的生活,像一個從窗口逃去的皮球,在白日反光看不清楚前方的蒼白馬路上,僅遺下一拍一拍彈動的聲響。——〈甩繩洋娃娃〉
「我希望她邊緣一點,可以幫我們反思現實狀態。她不是一個自己說話的人,就像一個——怎麼說——她好像一面鏡子,她站了在一個不同的位置,可以讓我們反省我們自己現在身處的狀態,我頗想我的角色是在一個這樣的位置。」
「妹妹」和「我」在〈月事〉中總是彼此憐愛、又彼此折磨——「妹妹」會自嘲不知自己他日會賣得什麼價錢、會堅持自己是狼的後裔、會慢慢漂浮起來......這一切都讓「我」或憤怒、或不知所措、或故意冷待。這種痠軟的脫力感,令十年前的故事現在讀起來仍然非常熟悉。如果預言所預測的不一定是事實,那麼〈月事〉就如一種情感上的預言。
有關「妹妹」的描寫延續到反送中運動期間完成的〈逝水流城〉,則演變成一種無限的緬懷,而那種緬懷,甚至在「妹妹」消失之前已經開始。在那段煙霧彌漫的日子裡,我們身邊都有曾有過「妹妹」,他們無比敏銳、矯健、充沛,終究在謝的故事種變成「鳥書」,繼續努力嘗試告訴我們,他們因為年輕而尖銳地感受到的一切。
「我不是想要紀錄這件事,而是我要紀錄我某一個時刻的某一種感受。......(歷史事實)是有很多東西可以追認的——發生過什麼事、在哪裡。但是你當下那一刻的那些感受、和其他人的互動,你自己的經驗,其實那些都是某一種 facts。......我那時候有一個迫切性——不說出版——就是寫下,因為那些會消失的,你某一種的狀態。那件事讓妳經驗到的精神、感受,是怎樣,我需要在那個時候寫下。」
魔幻如何 現實如何
我很好奇,謝曉虹有「失語」過嗎?事後想來,這種好奇大概是源於覺得她沒有。畢竟她在人人傷心得都只能用同一種腔調哭喊的時代,寫出了《無遮鬼》這樣紛紜的作品來。
她只是笑笑,「我其實在想什麼是『失語』。我平時也不是特別多話說啊。」後又認真地思考了一陣,「我覺得失語就是,其實有很多話你想說,但你找不到一個方法去講。而這個找不到方法,就是因為你的經驗超出了你平時日常的語言,可以表述的範圍。」
她說不上來是什麼時候找回用語言包覆經驗的能力,也說不上來何為「找到」,只能回歸到文學對她來說很重要的一個特質:「如果你從這樣(所謂「失語」的角度)去看,其實寫作還是想挑戰 convention。因為你要挑戰 convention、要去挑戰我們現有的語言模式,去問一些我們還未講到,還未表述到的事情。」
拓展我們的語言,就能說述更加多的事情。有趣地,這樣看來,謝曉虹的文學是「樂觀」的,因為某程度上,她在透過創造文學來相信,那些未能言喻的瞬間,只是未找到所屬的語言。
那多年來,謝的語言是什麼呢?——殘缺的肢體、蓮藕、氣球一樣輕、忽地發現自己在船上,這些都是能在她的作品中反覆看到的符號,它們的交集並不特別嚴謹,卻在不斷的流動變奏中形成了一組辨識度非常高的意象群。例如是出現率相對高的「氣球」,她便嘗試解釋說,那是和一種「只有一個表面、容易被刺穿」的想像有關。「那多少是我對權力的想法。我有時候覺得,權力是一種很搞笑的東西。它是很假,但它——怎麼講——一笑置之的話你就會發現,它根本不是一些可怕的東西,它是一件很滑稽、無內容的東西。」
但謝的文學中,意象彷彿並非供人解讀,而是供人閱讀的。那種一物生一物的環扣感和延伸力,讓人不捨得分拆賞析,有不容細想的動人。謝說,在處理某些修辭的時候,會「prefer寓言(allegory)多過象徵」。「它不是一等於二,A 等於 B。而是,那個意象是可以延伸,觸發其他的想像。所以我會這樣去想,那個意象它本身有很多可能性,但它其中一面是和現實某些東西是可以 touch到的。」
在謝的創作裡,事物無一秒不是在流動、變化,等待新的際遇。就如她說自己喜歡德勒茲「becoming」(生成)的說法——反對二元、去中心化、反樹狀思維的「塊莖」(rhizome)觀,正正就是她的「魔幻現實」,也是她觀察外界的方式:流變而容許鬆動。在她的文字裡,最近常被談論的「共同體」也有很多重新想像的方式。「我自己覺得共同體不該是一個很有邊界,固定下來的一種想像,那是會很可怕的,會侷限了我們很多。......即是,人和人的距離和連結應該是怎樣——它不一定要一種國族,或是地域的形式去想像。」
我們坐在浸大的某處平台,旁邊的是模樣過目即忘的教學大樓,講述著內容足以讓這些周遭都崩塌的書。長年的學院生涯讓可曾讓她感到厭倦?還是正正是這種地方,才能讓她維持一種隨時準備逃逸的思維?
但她沒有要去哪裡,只是靜靜的坐在那裡,以一種專注的神情說,「其實我自己的立場就是,無論是什麼生活狀態,你多多少少都要警醒那個生活狀態是有問題的。」像是把逃逸的姿態留了給文學,自己還要待在這裡,對抗無限接近幻的實。
謊言像氣泡一樣被戳破後,房子便一所接一所的倒塌。突然暴露在空氣裡的人,沒有一個不是瘋狂的。——〈一月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