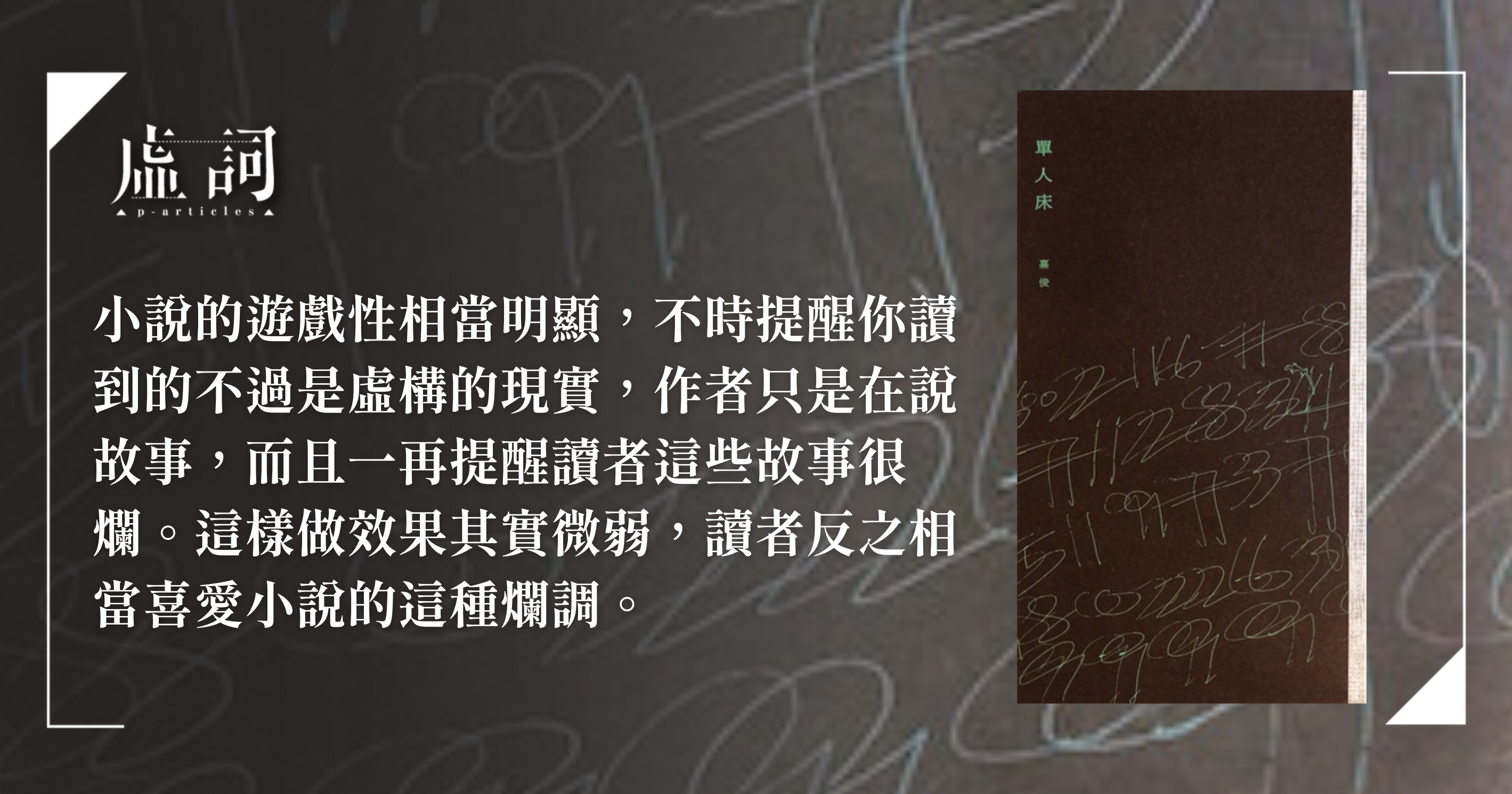床上讀《單人床》
《單人床》應該算是一部「社會小說」,十八、九世紀以來,英、法、德、俄的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大師已經貢獻了無數經典作品,把一個一個大時代的社會民生呈現在往後世世代代的讀者眼底,讓他們同歌同哭。這類小說講求營造典型環境、典型人物,以豐富的細節、生動的筆觸,立刻就讓人意識到那是現實中的某一人,某一處地方,甚至某一個角落。《雙城記》記裡那甘為愛人的愛人步上斷頭台的偉大的青年,在現實中雖然不大可能存在,但他走上斷頭台的每一步都是踏實的,可信的。
可是第二次大戰以後,一切秩序徹底打破,理智邏輯蕩然無存,典型再不能成為社會的參照,超現實主義大行其道,百花齊放,沒有甚麼是不可能的。連時間也不是線性發展,圖書裡出現了扭曲的時鐘。當你周圍的人都變成犀牛,你卻撐持著人類的形體和思維,不消說,你才是異類。這樣的現實才是真實。
嘉俊應該熟讀現代主義作品,不知道他有沒有注意到卡爾維諾的一個說法,他說因為輕,才能承載重。他以水桶比喻:水桶要空,才可以盛水。他的《一個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是歐洲魔幻寫實主義的先鋒,足與南美的魔幻寫實比美,其實都是現實一種,並不魔幻。當嘉俊寫扭著個北京姑娘睡了一晚而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跟讀到某甲一天早上醒來發現自己變成甲蟲同樣覺得不可思議。嘉俊很小心,經營自己的故事,處處提醒讀者那不是真的。比方去蒙古、新疆一去就幾個月,但甚麼景點也不去,就躲在酒店房間裡翻鹹網;與海鷗對話,那海鷗據說就是他父親;在公司只侍服個伯父同事沖咖啡;在南美無所事事,想泡妞又不夠膽;在圖書館地圖室只管回答某瀑布今天幾多度、去那兒那兒要搭幾多號巴士的問題。這些都相當「超現實」,寫來的目的是甚麼?難道就只是博讀者一粲?
比較貼近現實的,是應徵面試的一幕,又或者,一群同事集體外出午膳,卻有人落了單。當然,讀者(包括我)會認為「我」面試的情節相當現實、真實,我只覺得,作者寫這些的目的,不在呈現現實人生和現世職場的荒誕。職場裡的集體,都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隨時會給人忘記。主持面試的人對應徵者頤指氣使,這些都令人感覺真實而有共鳴,如果因此而從閱讀中感到滿足,也未嘗不可,但故事的結局可不僅限於此。不止一次,作者總讓故事留一下個反高潮的結局:我和她一星期後拍拖,三個月後分手,她十年後……/我和以色列女孩如果結了婚,十年後我在她家門前給炸死……可以完美的結局變得不完美,雖然沒有和以色列女孩結婚反而是完美。
嘉俊處理文字也很小心,他有用廣州話,但相當克制。屎尿的不時出現,以致有讀者懷疑那是肛門期慾念的遺留。作者的文字流暢輕逸,但顯然不想文字去得太滑,或變得太「文藝腔」。書中人物沒說過一句粗話,但出現屎尿,應該會令一些高雅的讀者說一句:乜咁架?在編輯過程中,我保留了作者一些不規範的用語,如「熟識」應是「熟悉」,希望保持全書文字一種casual輕鬆隨意的狀態。
比較費解的是最後一篇,這篇沒甚麼故事性,只是帶出幾首音樂和歌曲。作者或者有他自己的意圖,我的猜想是,他要把整部小說作最後的拆解,他怕這還不夠,最後還說這麼悶的小說你大概會感到不耐煩。事實上在整部小說中作者不時走出來向讀者喊話,說作者太沉悶太無用。在古典小說中,作者會不時走出來自我解說,評論情節,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現代小說承襲了這傳統,並名之為後現代/後設小說。這裡的所謂作者,可不就是blood and flesh真實的作者本人,只是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是作者的假身,所以說讀者準悶壞了的人,並不是嘉俊,小說中的「我」,不應等同嘉俊,嘉俊是嘉俊,作者是作者,嘉俊只有一個,作者的面目儘可不同。
這又牽涉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許多讀者都把嘉俊當作小說中的我,說他在現實中換女友無數,所以小說中的主角也,總是不乏女伴。這都可以是讀者反應理論的案例。讀者理論認為,讀者才是一部作品的最終擁有人,有最終解釋權,一部作品,也有待讀者的演繹而完成。正因如此,一部作品有不同的內涵,不同的意指,橫看成嶺側成峰,其中的不同,源於讀者而非作者。讀者全情投入,用他們的方法闡釋作品,讀《單人床》完全可以讀出性/無能,旅遊樂/不樂,親情冷/暖,階級感情/隔閡,諸如此類。嘉俊會得認為,這些都不是他想過要寫的,幸或不幸,作品落在不同讀者手上,就有不同的生命,這是文學作品奇異之所在。
回到《單人床》要拆甚麼解甚麼的問題,錢鍾書說,雞蛋好吃,沒必要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同樣,雞蛋好吃,更沒必要認識雞蛋的化學成分。無論作者搞怎樣的花款,《單人床》是好看的,相當entertaining,讀者看了覺得輕鬆愉快好笑,那便好,那管他甚麼策略不策略。但我當編輯,伍淑賢之後,很久沒有讀過這麼令人愉悅的作品,雖然讀者理論把作者放在一邊,倒想仔細看看作者的意圖,看看這類小說可以放在文學的哪一個位置。
嘉俊似乎正是害怕給放進文學的框框,我想這正是他把屎尿放到作品裡的原因。小說的遊戲性相當明顯,不時提醒你讀到的不過是虛構的現實,作者只是在說故事,而且一再提醒讀者這些故事很爛。這樣做效果其實微弱,讀者反之相當喜愛小說的這種爛調。嘉俊失敗了嗎?當然不,至少當一些正兒八經的讀者說他粗鄙俚俗的時候,他就有堂而皇之的說辭,說他這是以遊戲對抗嚴肅,以無賴對抗道學,這是把小說(或文學作品)從沉重的道德囹圄中解脫出來,面對人生不如意,以嘻笑代替昔日作品常見的嘆喟。這,不也恰好對應了讀者心理投射的方向?
在內容上,嘉俊卸下的道德重擔,寫的都是普通人遇到的事情,無關世道人心、社會倫理,沒有驚心動魄的人事鬥爭,生死相許的男女感情,都是人與人之間一些善意但沒有結果的關係,無所事事虛耗光陰的所謂流浪。小說單線發展,情節簡單,有時純以對白帶動。但這裡正好顯示嘉俊駕馭文字的能力,如與海鷗父親的對話,是十足海鷗父親的放任不羈,與北京和台灣姑娘的對話尤其精采,北京姑娘有京味,台灣姑娘有台味,我不得不自甘落入敘事者即作者的窠臼,認為此必嘉俊經驗累積所得。
如果說《單人床》有甚麼社會性,那就是作者總站在小人物立場說話,這些人物,都有各自的掙扎,有在酒吧賣藝而希望晉身娛樂圈的歌手,或在火窩店工作每天開工前喊口號喊得特別起勁的小伙子,或內蒙那幫幾乎無惡不作的好漢,都有他們各自生存的理想,俗套一點說,都有他們的尊嚴。
《單人床》真是一部讓人各取所需的小說,有些讀者是認識嘉俊的,說從中找到了他們相熟的朋友,另一些因愛見山,因而也愛見山出版的小說。我自作聰明,無中生有,會稱《單人床》為「新流行小說」,novel popular,這個novel,是新穎、新奇的意思。小說有「流行」的元素,文字輕盈,內容輕巧,鋪排流暢,不避俚俗,又糅合旅遊、音樂、異國語言,但正如作者要拆解嚴肅書寫,他一樣不想自己混入流行的行列。小說沒有公子美人、洋行小姐、空中少爺,沒有他們永遠快樂在一起的結局和幻想。《單人床》會流行,但不會是橫掃市場的那種。能夠有這一路新鮮可笑可感的小說,我很感快慰。(今按:小說2021年8月出版,兩年來保持銷售,據說現已所餘無幾。)
最近又讀到嘉俊的三篇小說(刊《明報‧星期日生活》),一讀就知道不會有第二個作者。小說場景設定在辦公室,都是小職員交往的小情節,一個男職員忍不住瞄了女同事的低胸裝幾眼,那種卻瞄又止的情態,相當傳神。又寫到一女孩夜裡做夢,夢到一男同事從後摟著她,撫摸她身上各部位,最後把一根食指塞進她的嘴巴。我告訴嘉俊,讀到這裡我幾乎笑到碌地。嘉俊似乎不明白我為甚麼會有這麼大的反應,是不是我想多了呢?但不是說讀者有他的解釋權嗎!
後記:這篇文章寫於2021年9月底至10月中在醫院留醫三周期間,住院為的肺炎導至肺積水。家庭醫生後來說,我的發炎指數很高,可以「瓜得」的。但除了背後長時間插一條放水喉管,不很舒服,精神並不覺萎靡,閒來讀讀書,前後又寫了接近兩萬字,這是第一篇。因沒帶書在手,不知關於小說的細節可有誤差,現在抄錄,也不特別查證了,雖不中也不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