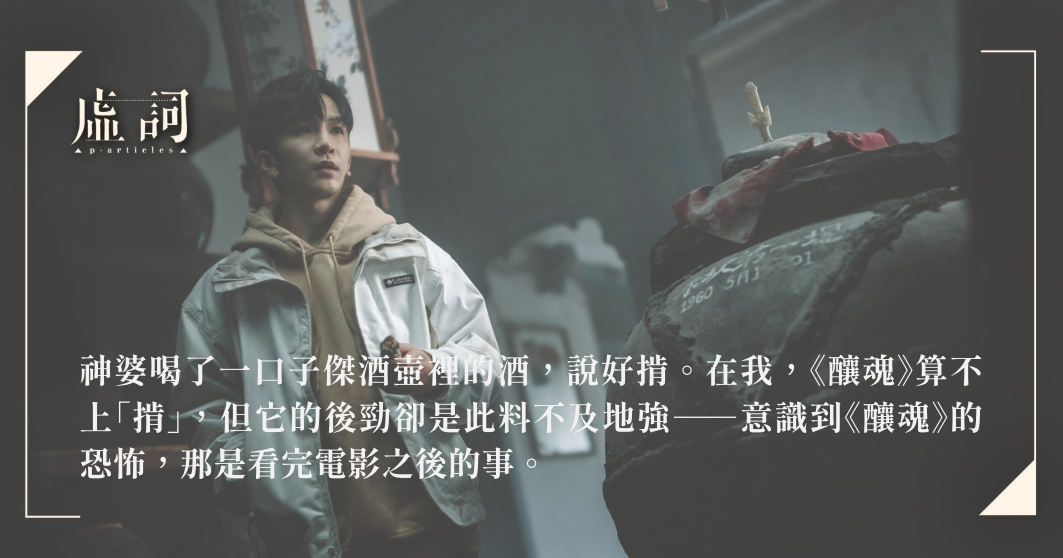人噬魂與鬼晝行——《釀魂》的埕裡埕外
首先,假定人物所說的都是實情,也就是說,網上流傳著赤坎村的喜慶繁盛(浩天說的),但其實二十年前華哥已經把村給滅了(小晴說的),他從此獨自「鎮守」此地,以釀武魂,使之永不超生;這個地方與世隔絕,以致二十年前的村莊彷彿自成一境,沒有任何現代來過的痕跡,甚至全村無人生還也無人問津,但同時赤坎又以玉冰燒聞名(華哥說的),據說還給南村北村供水(也是華哥說的),還有個只要十分鐘腳程就能到的碼頭、有每兩天一班的船期(浩天說的),又同時是個無人島,以致子傑一行人走來走去都只是徘徊在碼頭和赤坎村之間……想來這四人行的旅程就很像穿越,只是,是穿越到過去(但如果是過去,「現在」村應已經被滅了很久,應該不會能在網上查到,查到也大機率不會錯過曾被滅村的歷史)還是未來(但如果是未來,村莊怎會依然故我地一點都不現代)?
我意思是,假定人物所說的都是實情(就是說後來的阿武不是現在的華哥的第二人格),所有鬼也是真有其鬼(而不是集體幻覺),那麼在我看來,在阿武之外、在鐵槌和開山刀之外,還有更厲的鬼、更血的暴力,它不但能橫行在失序、恐怖的夜,還可以安然曝露於陽光的規矩底下。
I. 嘉露:電影中第一個死者
嘉露(袁澧林飾)一出場就死了,能不能說是子傑(盧瀚霆飾)害的呢?這當然是可資討論的,不過我倒認為重點在於,他的悔恨是指向那一次(最後一次)個別的、孤立來看的沒交帶,抑或是一直以來的「結構性沒交帶」(「成日都係噉」、「連一句sorry都冇」——嘉露說的,而在她說出後一句話後,子傑依然沒有say sorry)?如果是前者,悔恨之情就更像是一種錯付,也可以看出他毫無長進,毫無反省,純粹內疚——也是,連五週年慶祝這種事也能忘——而且不是要求他給她甚麼驚喜,是兩個人一早約好的——那我還能說甚麼呢?
既然不能說甚麼,那麼總之,就是子傑對嘉露念念不忘。後來,他在口袋找到她的金髮夾,又收到她的來電,在這個收不到訊號的島。她是在找他嗎?但是後來阿武(林耀聲飾)對珈豪(朱栢康飾)說,是自己幫你們一行人面對了心魔(雖然面對不等於解決),現在輪到你們來幫我了。先不理這番話合不合邏輯、有沒有契約效力,他到底是怎個幫法了呢?子傑「看見」(引號表示可疑)的嘉露是真的嘉露嗎?如果是,那阿武也太神通廣大了吧,即使被釀在酒埕依然可以隨意調動亡靈。但我偏向認為不是這樣,因為神婆(郭翠怡飾)作法沒有招來嘉露的魂,表示她不在這裡。說到神婆,她為甚麼曉作此法呢?
II. 神婆:四人行中第一個死者
很有可能,她用過來接通女兒。死去的胎兒,大概算是鬼魂的其中一種類型吧,不少作者——不少女性作者——都書寫過這種「嬰靈想像」。這樣看來,嬰靈想像是普遍的——換一個說法就是,嬰靈是被為數不少的人所信仰的。母親對於跟自己在真正(而不是比喻)層面上連理雙飛、共為一體的胎兒有著深切連結,這自然是毋庸置疑的真情實感(五四女作家沉櫻的〈妻〉就寫到了母親對於嬰兒的心心念念),但當它被提升到一種糾纏報復的信仰,這就不免有點可疑了——嬰靈想像可會是一種文化建構嗎?嬰靈的存在本身並不是不辯自明的,對於胎兒的存在方式也不只有一種想像:
在《我推的孩子》(推しの子)裡面,小愛的主診醫生死在阿庫亞出生之時,遂轉生成後者、小愛的孩子——言下之意,胎兒在出生前都是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狗」——胎動不是因為有靈,而是機械使然。[1]
胎兒有靈與否,或者,靈在哪一時刻生成/進入,這本來就是一些高度政治化的問題。
在四人行中,浩天(吳肇軒飾)為被阿武附身的珈豪擋刀而死,即使如此,珈豪也不免被殺,子傑則(似乎是)為了讓阿武無處容(附)身而自殺,而神婆,她早就死於跟「女兒」玩的捉迷藏——在各人的死裡面,神婆之死的因果報應意味最重,甚至只有她、的死有因果報應的「寓意」[2],而這種寓意,在我看來也甚為可疑,因為它、的因果報應向來不太公允——這種孽力通常只會顯現在母親眼前、作用在母親身上。
電影中有五個主要女角,在神婆和她的「女兒」之外,還有珈豪的母親和子傑的女朋友嘉露。女兒→女友→母親,這好像就是電影裡面女性的唯一存在、成長形態了,能夠從這條「生命線」中逃逸開來的就只有小晴(陳紫萱飾)——以自殺為方法。
III. 小晴:赤坎村的第一個死者
電影中有兩組人物對照:「神婆—子傑」,以及「小晴—子傑」。在我看來,子傑因為嘉露而自責是有理由的——對於「結構性沒交帶」以及過去的毫無歉意的歉意以嘉露的死為聚光點(focus)燃起,而神婆為了「女兒」自責是可以理解的,但把「神婆—子傑」組成對照,這組對照在我看來是有點奇怪的。不過,更難以理解的是「小晴—子傑」這邊。小晴跟子傑有甚麼可比性呢?出車禍死的又不是他——出車禍死的可以是任何人;子傑的悲傷雖然深刻,卻是微小,是時間(而、不、是、酒)能解決的事。相比之下,小晴之於她所面對的暴力是何其微小?她總是無言、被動、無選擇餘地,她唯一的選擇就是從「禮法」(婚禮和婚法)中逃逸——在婚宴上,村長向村民致謝辭:「喱門婚事,你哋個個都係媒人!」看來,阿武是帶上了全村人去逼婚,以致於村長會說出這一句真心話。禮法、權勢和庸眾使小晴和華哥(姜大衛飾)一家在村中處於徹底孤立,如果是這樣,小晴的死就是所有村民都難辭其咎的——全都是吃人(正如魯迅說的禮教吃人)噬魂(吃人吃得徹底,魂也不放過)的「造惡者」,當中的阿武當然最罪不容誅——如果說阿武沒有殺小晴,那麼華哥也沒有殺阿武——「非我也,兵也」(《孟子》),是開山刀的錯。
其後,華哥殺盡了村民。
不過,華哥的復仇並沒有讓小晴釋懷,反而讓她繼續魂困於此,徘徊廿年,而她還為村民的死而懺悔、為神婆的死向子傑致歉。對此,子傑回答說:「唔係你嘅錯,冇人估到會變成噉。」用「冇人估到會變成噉」來解釋「唔係你嘅錯」聽起就很奇怪,阿武和華哥的行為引致的後果同樣是「冇人估到會變成噉」;整個事件的起因完全是因為阿武,但這位子傑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還順著這個話題來作出說教:「我都係,我都原諒唔到我自己……但係喱個係藉口!我同你一樣,都係唔敢去面對,最重要嘅係,我哋要知道,唔好再停喺過去。」子傑清楚明白小晴的連環不幸,但他竟然還能說出「喱個係藉口」、「我同你一樣」這樣的話——我想到蘇朗欣在《水葬》裡說到,「在真切的暴力和壞滅面前,那些屬於個人的私情,一個人的屈辱、犧牲、躁動都被壓縮到了最低層」[3],而這位子傑,他甚至談不上有什麼屈辱、犧牲——難道他沒有這個自覺嗎?難道發生在小晴身上的暴力、創傷就是可以、而且應該被放下、被忘記的嗎?他對酒的耿耿於懷有什麼資格與小晴之於血的念念不忘相提並論?還「我同你一樣」!這已經超出了所謂的「直男癌」範疇——他根本就是毫無同理心,這與讓女朋友在街上乾等一小時之後sorry都冇聲同質、而又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現在,如果電影的「寓意」就正如子傑的「說教」那樣,是「我哋要知道,唔好再停喺過去」,神婆就是因為沒有move on,沉溺於過去而死(她死在酒埕裡,這倒有點意思),而小晴被子傑感(?)化,轉世離開,那麼子傑也差不多是時候好好放低了。
IV. 子傑:電影中最後一個死者
子傑本來有望成為唯一的生還者——他在最後表現出了反制阿武附身的潛力,但他最後還是死了,死於自殺。對於他掙扎著拿起瓦片狠下殺手的理由,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令阿武失去可供操控的身體——雖然不知道釀了廿年之後反而像修行了幾百年,至今已神通廣大、可以隨意附身的阿武會有些什麼下一步行動,但子傑的犧牲也是無可指責的吧。然後,死後的子傑與嘉露會合——這倒有點出乎意料了,明明之前一直在說要放下——也就是完成哀悼(mourning):接受已失去的所愛之物已失去——此前子傑處於憂鬱(melancholia)[4],因為他潛意識中還有嘉露的魅影,金髮夾、來電都可以被視為其具體顯現。而在結局,解決這個「已失去的所愛之物」和「未接受已失去的所愛之物已失去」兩者之間張力的方法,竟然是讓「已失去的所愛之物」本色奉還(而不是變體回歸)——這的確是解決了一切(情節上的)問題,但同時什麼(道理上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啊。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然後又想起電影開頭對於《地藏菩薩本願經》的引用:「是閻浮提,行善之人,臨命終時,亦有百千惡道鬼神,或變作父母,乃至諸眷屬。引接亡人,令落惡道,何況本造惡者。」所以,子傑「眼中」的嘉露,可是「引接」他的「惡道鬼神」?他的結局就是被「令落惡道」,不得善終?引文最後的「本造惡者」,在電影中就讓人很直接地想到阿武——「何況本造惡者」,那他怎麼死了廿年靈魄還在人道,還能活蹦亂跳地Here’s Johnny(他以珈豪之身用鐵槌破門而入,就很讓人想到《閃靈》[Shining, 1980]那經典一幕)?
也許只能說,上天本來就不公平。
V. 《釀魂》的後勁
神婆喝了一口子傑酒壺裡的酒,說好掯 [kang3]。在我,《釀魂》算不上「掯」,但它的後勁卻是此料不及地強——意識到《釀魂》的恐怖,那是看完電影之後的事。
回應上一節的問題:子傑的成仁有成功嗎?
想必沒有。
後來我讀到一則短評,有這樣的句子:「沒有怎去發言自辯的阿武(林耀聲飾)不是甚麼大魔頭,只、是、霸王仔二世祖而、已,在、生、時、他、沒、有、殺、過、人」、「阿武的確強姦了華哥女兒小晴(陳紫萱飾),然而他負、責、任、娶、她,這頭婚事華哥是同意的」[5]。《釀魂》裡的惡鬼,我清楚明白是映畫的、演出的、虛不真實的;相對而言,電影評論當然是「實」的。「只是」。「負責任」。這些藏在細節裡的鬼也未免太過觸目驚心!
註:
- 雙雙:〈和夏宇三首.一〉賞析(每天為你讀一首詩,2023年9月14日),https://www.instagram.com/p/CxLELnKNu5Q/?igshid=NzZhOTFlYzFmZQ==;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pfbid023H9NAKLbzFJED8BccjVbmmAbqZ9qQQ9PcXoLBcHCDcwRR6cAikjeKqak42yaRM3Zl&id=100044209895196&mibextid=Nif5oz。
- 頓號當著重號用,下同。
- 蘇朗欣:《水葬》(香港:水煮魚,2020年),頁130。
- 關於哀悼與憂鬱,參見Sigmund Freu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XIV.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7): 243-258.
5. 張偉雄:《釀魂》焦點短評(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23年9月1日),https://www.filmcritics.org.hk/zh-hant/node/3195。著重號(頓號)為筆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