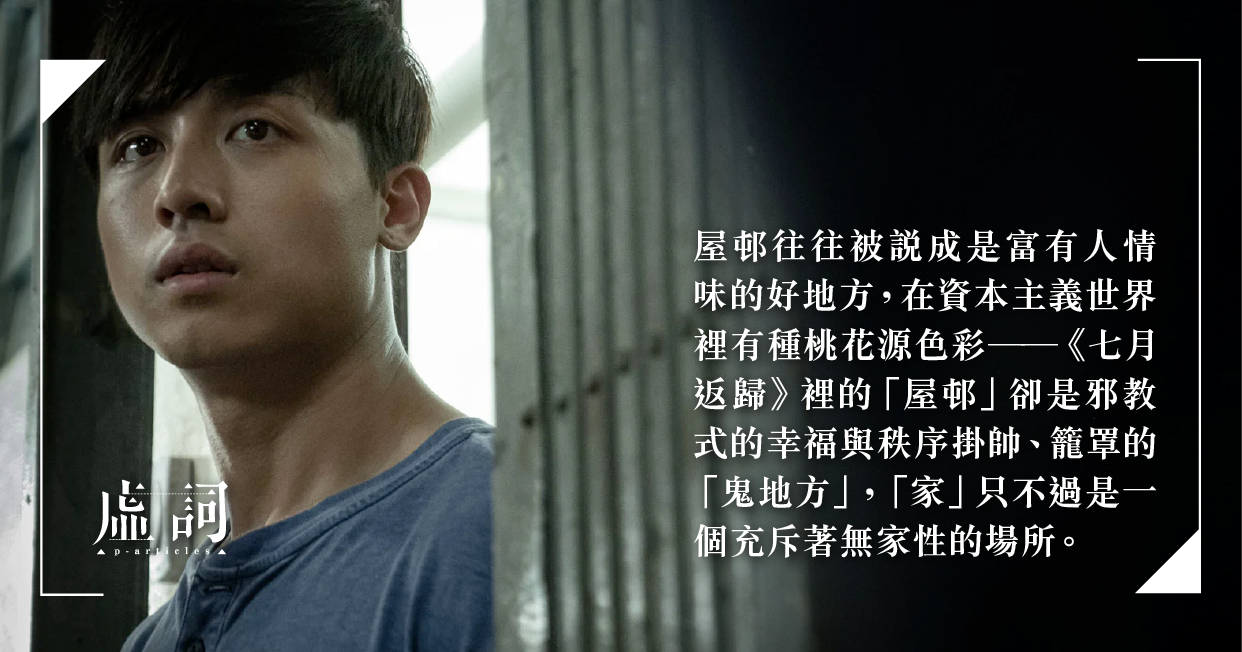七月、第七天:《七月返歸》中的東方、西方和希望意象
自幼有陰陽眼、不斷受朋輩排擠的向榮(Anson Kong飾),某日收到母親(白靈飾)自殺不遂入院的消息,被迫從加拿大返回香港,並回到舊居暫住。
(以上是《七月返歸》[Back Home] 的劇情簡介第一段,摘自維基百科。)
I. 返/反桃花源
向榮回家的結論是,這裡是反烏托邦 (dystopia)。
提到「烏托邦」(作為中文詞語),我們往往首先想到「桃花源」。那是個怎樣的地方呢?武陵人行舟迷走,「忽逢桃花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初極狹,纔通人」,過後豁然開朗,別有洞天,「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我聽過一個〈桃花源記〉的解析,說桃花源其實是墓園:「山有小口」是隧戶,「初極狹,纔通人」是墓道。主要理據是郭璞《葬經》:「門前桃桑,為大凶。」而桃花源人自言是避秦而來,與世無交,「男女衣著,悉如外人」,就很可疑:從秦到晉,服飾變化理應不少。所以「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大概近於極樂——桃花源人是當代亡靈。
這種說法未嘗沒有斷章附會之嫌,比如把「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解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就是意無意地剪掉了「往來種作」——「悉如外人」的應該不是作為名詞的「衣著」,而是作為行為的「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意思是,她/他們會耕作、會穿衣,雖在法外之地,卻非化外之民。不過,恐怖故事的意思,本來就是:聽過了就回不去——因為故事而來的恐怖與理性無關,恐懼一旦被召來、喚起,它就「在那裡」了,於是,每次看到〈桃花源記〉,我都會想到這種不可能的雙重閱讀的可能:那裡在我變成了好地方與「鬼地方」(引號表示雙關,「鬼」作為名詞或作為表示惡劣、糟糕的形容詞)的疊印之地。
屋邨往往被說成是富有人情味、街坊鄉里的好地方,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就有種桃花源色彩/濾鏡——不過,《七月返歸》裡的「屋邨」倒頭來卻是邪教式的幸福與秩序掛帥、籠罩(反烏托邦的特徵)的「鬼地方」(dy/ghostopia)。「鬼地方性」一旦被揭而示之,這小節的第一句「向榮回家」是否準確即顯得可疑——「家」只不過是一個被命名為「家」,卻充斥著無家性 (homelessness) 的場所。
II. 公屋怪異
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在《馬克思的幽靈》(Spectres de Marx) 中以「變/斷時代」(a time out of joint) 形容1989年國際秩序變天,並借鬼魅/幽靈 (spectrum) 比喻「新世界」中死而不去的馬克思主義。張美君借其「變/斷時代—鬼魅/幽靈」以類比1997年的香港回歸處境(註1)——「變」不言而喻,「斷」則是在於家(香港)即將變成「家不似家」(謝安琪〈臨崖勒馬〉)的「家」而青黃不接的前後斷裂,這種現實中「陌生」(unheimlich) 的焦慮轉化成映畫中的「詭異」(unheimlich),正如陳果執導的《香港製造》(1997)裡面,公屋空間的「鬼影幢幢」。
《香港製造》本意不在鬼,所以其間的「公屋怪異」毋寧說是一種微度而來的鬼趣氣氛,氣氛沉殿成形,形成不只可感而且可見的實體,則要到麥浚龍編導的《殭屍》(2013)和這套《七月返歸》。
從文本互涉 (intertextuality) 的角度看來,《殭屍》通過錢小豪(及其它元素)上追《殭屍先生》(1985),而清水崇的參與引入了如《呪怨》(1999)的扭曲肢體之類日式恐怖 (J-horror) 成分。《七月返歸》則有不言而喻的一套外文本(exterior text,這個「文本」的指涉範圍包限但不限於:廣闊而抽象的文學、社會和文化體系),而向榮的「下沉」很容易讓人橫向地想到《Get Out》(2017)裡的 “Sunken Place”——這一斑表徵了《七月返歸》與作為推想恐怖 (speculation horror) 類型的《Get Out》以及Jordan Peele的其它同一線路電影《Us》(2019)、《Nope》(2022)等的匯合。有別於單純感官的、spectate(觀看)的恐怖片,引導觀眾對對於文本內部(情節)和外文本(現實)的speculate(推想)成為恐怖的另一重意義——怪異背後存在一種思辯特性強烈的敘事,觀眾穿過這層敘事,從而獲得回應當下的社會意義(註2)。
《七月返歸》與《殭屍》的另一點不同在於,雖然兩者的取景空間相近,但後者的怪異——殭屍——是這個空間/人間的異質;到了《七月返歸》,異質的卻是主角——觀眾所認同的角色——「世界」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怪異,恐怖的來源由突發驚嚇 (jump scare) 或詭/鬼異,變成了類似對巨物的恐懼 (megalophobia),主角(觀眾所認同的角色)在此面前的渺小就接通了觀眾的渺小。電影最後,照遍夜空、映滿向榮眼眸的花火和背後的「風調雨順」花牌作為「新世界」的喜慶成為佔滿畫面的巨物——一如《香港製造》最後的廣播對於聲軌和大氣電波的佔領:「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也是你們的⋯⋯」
III. 異物
聲音/話語 (discourse) 的存沒與「自我」的存沒之間存在密切關係——《七月返歸》裡的「割舌」,意義本來就不言而喻。我想起的,是魯迅也曾經被人說「真該割去舌頭」(作為反話,因為他「把國民的醜德都暴露出來」),對此,許廣平說:
我聞閻王十殿中,有一殿是割舌頭的,罪名就是生前說謊,這是假話的處罰。而現在卻因為「把國民的醜德都暴露出來」,既承認是「醜德」,則其非假也可知,而仍有「割舌」之罪,這真是人間地獄,這真是人間有甚於地獄了!(註3)
在「人間有甚於地獄」的這「屋邨」裡,被割下的舌頭起初只是spectate意義為主的身體血肉,後來就被speculate地揭示成為建構反烏托邦秩序而必須加以賤斥、割捨的異物。
更大形的異物就是不肯割舌的向榮這個人。正如簡介所言,他「自幼有陰陽眼、不斷受朋輩排擠」,連蕙蘭也稱他為「畸胎」,而他採取的行動,就是他告訴宇仔(黃梓曜飾)的「扮睇唔到」——「他永遠和這個世界保持一些距離」(註4)。以成為局外人(置身事外)作為應對局外人(被排在外)身分的辦法。回「家」以後,他依然不脫局外人的命——他「不安於室」,試圖追查割舌、七樓、怪異的真相,這使他成為了「屋邨」裡的異物、正常人之中的「狂人」,一如《狂人日記》(1918)中的「某居昆仲」。
關於《狂人日記》,我也聽過一個解析。余/我由始至終都沒見著「狂人」,「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此人說其弟「已早愈[癒],赴某地候補矣」;余/我讀「狂人日記」,覺得所載「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但,「荒唐之言」可會如《出埃及記》(2007)說的那樣,是無人相信的真事?「狂人」的結局,會不會就是變成醢羹、屍骨無存,以致余/我訪而不遇?在《七月返歸》裡,荒唐真實不虛,而其結局,也未嘗不呼應《狂人日記》第十三、也是最後一節的語句——語句只有兩行,彷彿是急就之章,來不及多寫: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IV. 成了
「成了」來自十架七言第六句、耶穌斷氣之前的最後遺言:“Τετέλεσται” (It is finished),傳統上這被稱為「勝利之言」(The Word of Triumph)。《七月返歸》的結局,在我看來即充滿宗教意象。
人祭之初,宇仔「豎著」進場:他被固定在站籠,頭後面是一個帶著指向圓心的刺的金屬圈——這看起來就是荊冠與聖光 (halo) 的合體。維拉斯奎茲 (Diego Velázquez) 的畫作「在十字架上的基督」(Christ Crucified, 1632) 裡面,荊冠戴在耶穌頭上,一圈淺淡的聖光映照在後。
後來,向榮把業已「橫著」的宇仔抱出。那個姿勢就讓人想到米開蘭基羅 (Michelangelo) 的雕塑「聖殤」(La Pietà, 1497)。
宇仔這個孩子就像聖子。聖子是世界、人間的救贖。
順著上面的基督宗教意象聯想下來,電影的七天分節自然也大有發揮的空間——計上休息日,萬物造齊之日﹐神造世界就是七天。七天裡面發生了甚麼事?向榮「某日收到母親自殺不遂入院的消息,被迫從加拿大返回香港,並回到舊居暫住」——回到舊居,暫住,客居,街坊鄉里見之,紛紛「問所從來」——他是這裡的訪客、「異質存在」。反烏托邦不允許異質存在,「我」(作為有個體意識的個體、有自我主張的自我)與「我們」勢不兩立,一旦存在異質、異識的「我」,「我們」中就會出現裂痕、隱憂。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對面的男人、跳樓的女子,一個一個割舌、自毀,消滅「自我」;到第七天,剩餘的「自我」都在喝下鍾婆湯之後紛紛剪脷,融入了「我們」這個家,最後就是宇仔的獻祭儀式,以及向榮的徹底絕望——至此,萬物造齊,「新世界」成了。Τετέλεσται。宇仔的血成為了救贖「世界」、「我們」的寶血,一如十架上的聖子;通過荊冠、聖光、悼基督這些符號,「邪教」(cult) 轉化成正教 (orthodox) 的存在;背後的「風調雨順」花牌除了是對於腥風血雨的反諷,它同時上接蕙蘭的「女吊」形象(註4)和「農曆七月」的儀典,顯現為一種可資背靠的東方傳統,然後以基督的、西方的方法作為正教化的路徑,最後以花火——而不是尋常與花牌配搭的花炮——作為第七天、萬物造齊之日的標記。兩種對立、互相違和的元素統一、合謀,構成了「新世界」的勝利。
不過,這些宗教意象同時為失敗的向榮/我們留下了希望——眾所處知,聖子在被釘死後三天復活。不過,更有依憑的希望毋寧在於「電影的七天分節」:日期由「第七天」開始倒數,到「第一天」結束。
為甚麼不是由第一天順數七天,而要倒數呢?
在我看來,如果採用順數、以第七天作結,那第七天的下一天就只能是「第八天」,是然後沒有然後。現在電影以「第一天」的字樣作為電影的最後一幅畫面,就很巧妙,因為我們都有一種傾向、或者說習慣,習慣先看到標題,再看到內容,即,我們的預想是先看到「第一天」的字樣,再看到第一天發生的種種。於是,「第一天」之後出現映後字幕,就讓人有點措手不及——巧妙的也正是這種措手不及,因為由此,「第一天」產生了雙重指涉的可能:第一天可以是祭典之日(如果「第一天」指的是「第一天」字樣前的情節),也可以是映畫闕如未播之日(「第一天」指「第一天」字樣後的沒有情節)——電影於焉結束,然後電影院燈光灑落——這光就是「第一天」的日出,「第一天」就是現在——映畫的、向榮的倒數業已完畢,我們的、現實的「第一天」從現在開始。第一天的下一天就是「第二天」。
宇仔之死在映畫裡、在「新世界」的她/他們,意義是「救贖」,在(映畫外的)現實裡、我們這邊的意義是——如同《狂人日記》裡面,「彷彿是急就之章,來不及多寫」的「救救孩子……」的呼告。電影裡作為第七天的「第一天」,既是我們的第一天,也是「新世界」「成了」的第一天,但是歸根結底也是我們的第一天。
英語裡面有一句諺語:“The best time to plant a tree was 20 years ago. The second best time is now.” 種樹最好的時機是20年前,如果錯過了,至少我們還有現在。
V. 第一天就是現在
(全文完)
註釋:
Esther M. K Cheung, Fruit Chan’s Mad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譚以諾:〈恐怖片的新轉向〉,https://www.instagram.com/p/Cw1ivU4rl9p/?igshid=NzZhOTFlYzFmZQ%3D%3D(2023年9月26日瀏覽)。
魯迅、景宋:《兩地書》(香港:南國出版社,1966年),頁64。
mm2 Studios Hong Kong:〈七月返歸 製作特輯 - AK x 白靈 x 導演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vv19YghKfc&ab_channel=mm2StudiosHongKong(2023年9月26日瀏覽)。
魯迅在〈女吊〉中寫到了「女吊」這個戲曲形象:總是伴著「悲涼的喇叭」出場,是「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魯迅:〈女吊〉,《且介亭雜文末編》,《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頁614, 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