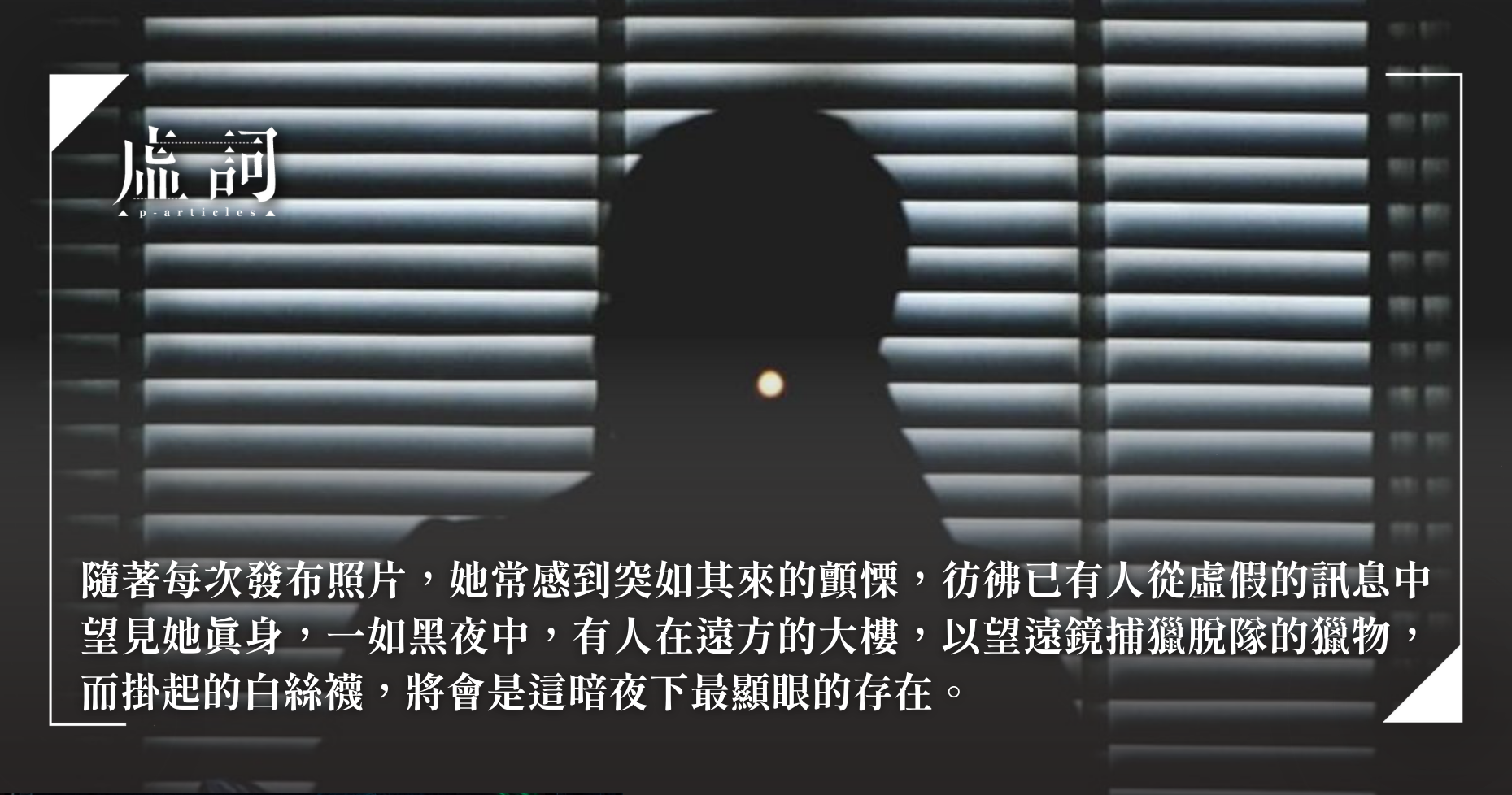對「自我」的爭奪
小說 | by 苦橙蒿 | 2025-12-25
苦橙蒿傳來小說,書寫張清作為一名普通女性,置身於充滿社交媒體與文化活動的環境,感受到自我認同的疏離與焦慮。她從表面模仿他人姿態,逐步深入探索性取向、無性吸引及酷兒身份,經歷嫉妒、反思與混亂的歷程。張清在詞彙爭奪與身份標籤中尋求歸屬,卻面臨真實歧視、內心衝突與虛無感。 (閱讀更多)
第三者
小說 | by 勞國安 | 2025-12-24
勞國安傳來小說,書寫觀塘協和大廈發生一宗情殺案,謝永森因提出分手遭女友黃靜宜刺傷身亡。黃靜宜認定男友移情別戀,而謝永森生前確實沉溺於與「琪琪」的完美關係中。琪琪溫柔體貼,既是他的精神支柱,更教唆他與女友攤牌。然而,當謝永森的姐姐整理遺物時,卻在手機中發現琪琪的真正身份⋯⋯ (閱讀更多)
聊聊
小說 | by 蔡傳鎮 | 2025-12-19
蔡傳鎮傳來小說,書寫「我」在舊同學婚宴後樓梯上,遇到昔日同窗梁證恒。藉由一支矯情的捲煙,「我」開始審視梁證恒從大專時代起便極力堆砌的虛假「人設」,從對風雲人物周航生的拙劣模仿,到如今展示妻兒照片以博取認同的庸俗。在煙霧吞吐間,回憶與現實交錯,同儕間基於利益與階級的虛偽連繫,以及那份雖近在咫尺卻無法逾越的心理疏離。 (閱讀更多)
鴨腳過粉雨
小說 | by 黎柏璣 | 2025-12-12
黎柏璣傳來小說,書寫「我」年近三十、領著微薄薪水的兼職文員,在 Duolingo 的五百天里程碑前,仍面對著人生的道道困境。「我」曾因情傷想學優雅的探戈,卻在性別角色和身高問題上遭遇錯位的尷尬;獲過寫評獎,卻被機構勸說自願放棄;努力將心血化為 Zine,卻又無助於他對抗原生家庭的疾病與期待。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