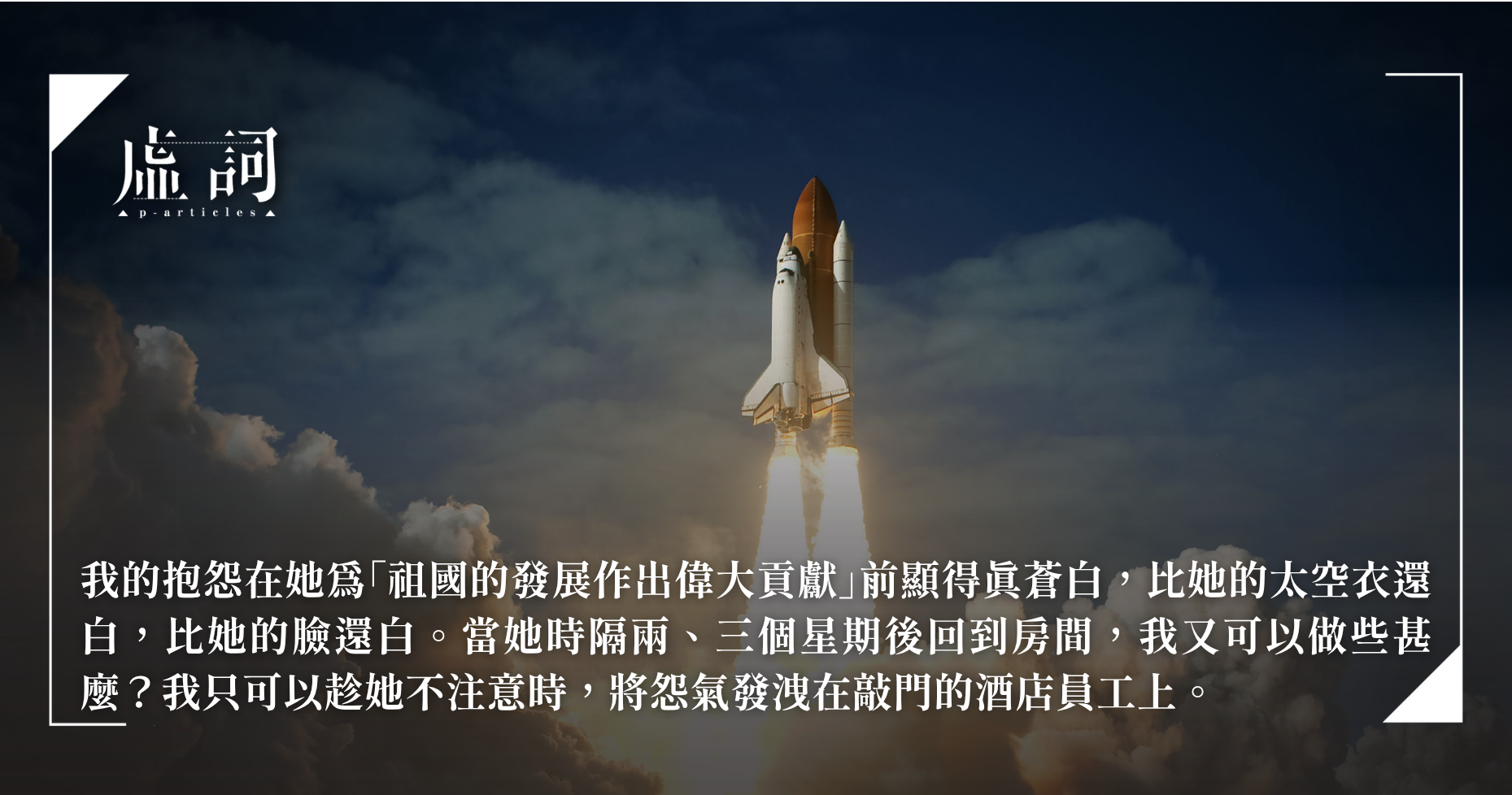地震還未結束
小說 | by 楊焯雋 | 2025-10-10
楊焯雋傳來小說,書寫一場地震撼台灣,震央附近的「他」看似無恙,卻在餘震中迷失。遠離災區的「你」,與「他」共同準備二二八事件報告,卻發現「他」因「地震尚未結束」而未作任何準備。「他」提及聽不見的地鳴與餘震,甚至開啟直播,捕捉水杯中隱形的顫抖,只為證明地震尚未結束。 (閱讀更多)
懸
小說 | by 蔡傳鎮 | 2025-10-03
蔡傳鎮傳來小說,書寫應屆高中畢業生陳榮軒,在圖書館的暑期工中,對將圖書排架至「處女座般」整齊的形式主義深感不解。這份重複耗力的工作,加速了他對社會價值觀和未來升學道路的巨大焦慮。他觀察同事們的「慢哲學」,並對看似油膩卻是心理學系畢業的上司梁永生產生複雜情緒。在辭職前的最後一天,陳榮軒壓抑住向梁永生傾訴自己對體制化、對成人世界困惑的衝動,將滿腔質疑化為一場無聲的心靈獨白。 (閱讀更多)
白頭翁
潘逸賢傳來短篇小說,書寫一場初夏的黑雨,浸透了城市的護土牆,也沖刷著人心底的憂愁。在繁華都市的半山小平房旁,一顆老榕樹見證了悠長的歲月與變遷。「我」在雷雨中再次爬上親手種下的老榕樹,檢查新築的白頭翁鳥巢。一名樣貌酷似故人的管理員前來檢查房屋,喚起「我」如何將這遍無垠的沙丘化為綠州的回憶。 (閱讀更多)
光之帝國
周丹楓傳來純粵語書寫的小說,以超現實主義畫作《光之帝國》為題,書寫Mina在待拆舊樓八文樓中咖啡店工作時,與同事Dora、Janet,以及熟客Sunny閒談。而Mina工作的咖啡店成為了各種慾望、迷惘和人生哲學的交匯點,使他從中窺見了嚮往的自由、金錢的誘惑,以及婚姻與家庭的現實重擔。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