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
小說 | by 方狗 | 2024-1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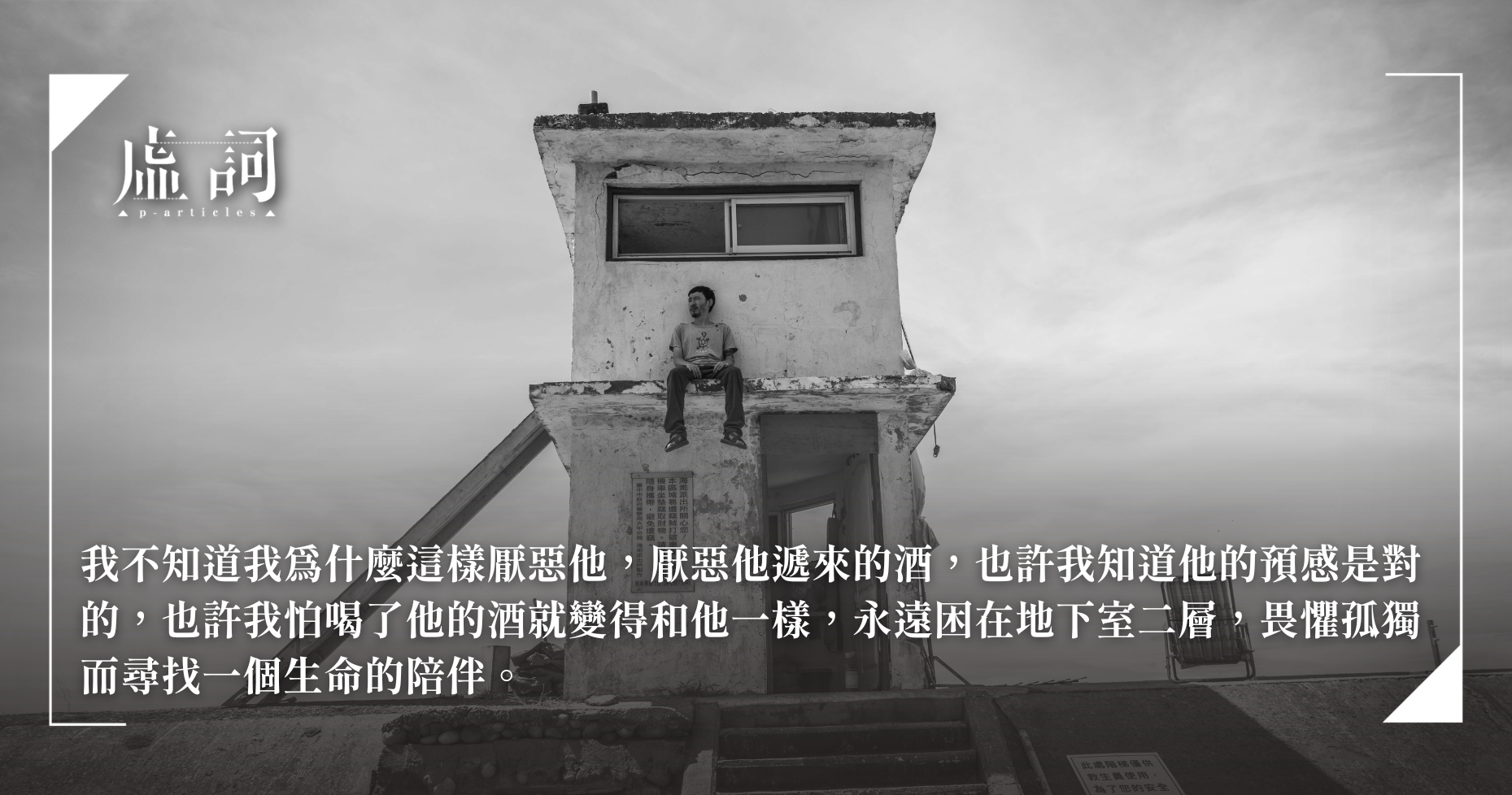
虛詞無形FB (41).png
儘管我和他們住在一起,但我知道我和這些人不一樣。
(一)
高考那年我的成績還是爛得不可救藥,老師把我的父母叫到學校去,推薦我走專業上大學。可是我一無所長。
我羸弱的身板勉強支撐呼吸這項運動,所以學不了體育;大概因為講話太少我甚至不知道唱歌需要五音俱全,所以也學不了音樂。班主任和平時完全不同,一臉關心又帶著同情和一點兒惆悵望著我,她本就細長的眼睛隔著薄薄的鏡片眯起來,遞了一張宣傳單給我的父母,上面寫著「光明教育—美術培訓」。我說我不會畫畫,她說不用基礎,交上錢就能過,然後她可能覺得這話太像提前準備好的,尷尬地抿了抿嘴,可我還是看到了。
結果第一年我還是落榜,學美術的錢浪費了,連同我父親珍貴的耐心也一齊浪費了。他的酒瓶越來越頻繁地向我擲來,有時候運氣好,撞在牆上,只需要花幾分鐘撿起破碎的的玻璃;運氣差點,砸在身上,淤青也會在幾天後散去;有幾次點背,剛好碎在腦袋上,要幾個月才能勉強遮住紅腫的印記。
第二年我剛剛過了線,但也沒什麼太多的選擇,可我知道他們已經不會再供我讀第三年。於是復讀一年後,我來到北京一所專科美術學院上了一個三流學校,並且打算再也不回那個地方。
(二)
我在那個所謂的大學里什麼也沒有學到,因為我厭惡酒精所以也沒有任何朋友。大部分時間我就在陰冷的圖書館消磨時間,幫學校的圖書管理員打卡上下班:一方面他可以更專注於倒賣二手手機,我還可以獲得一些零用錢。然後晚上回到一地啤酒瓶和泡面桶的宿舍洗漱、睡覺。
父親拒絕給我生活費,他說有錢給我還不如買瓶酒喝,至少還能刺激膀胱讓他撒泡尿,而我還不如一泡尿。但母親每個月還是會偷偷給我往卡里打生活費,後來金額越來越少,我想應該是被父親發現了。有次她來看我時我看到她頭上也有沒遮住的紅印,便告訴她不要再給我打錢了,我打工的錢足夠生活。
四年里我談了一個女朋友,她也常常待在圖書館,我們常常很浪漫主義地在一起沈默不語,其實只是沒有任何有意義的話題。
高芮很漂亮,漂亮得讓我總懷疑她和我在一起是有什麼目的,然而我實在是沒有任何可以被索取的東西。我問過高芮為什麼和我在一起,她說我們是一樣的人,可我知道我們之間有差距,並且有預感這種差距會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大。
高芮在畢業前夕找了一家小設計公司的美術編輯工作,給我們兩個都投了簡歷,底薪兩千,每張成品額外提成百分之二十。這樣的待遇對於我們這種學歷水平算很優渥的,但這不足以支撐在這個城市生活,好在這份工作不需要出勤率,用設計公司老闆的話來說就是只要按時完成任務,甚至都不需要用公司的辦公桌。我們兩個都通過了面試,只是公司只剩一張辦公桌,所以我不需要按時上班,只需要按時完工,後來我看到招聘廣告上也只寫了招一個美術編輯,可我也沒有多問。那個禿頭老闆看高芮猥瑣的神情讓我感到氣憤,這種氣憤大部分出於正義感而非佔有欲,而我也沒有任何底氣和能力表現我的不滿。
然後我只需要找一個晚上可以住的地方和一個白天可以賺錢的去處。於是在圖書館管理員的介紹下找到了一家電子廠上班,原因很簡單,一來廠裡包吃住,我可以把租房子的錢省下來;二來電子廠的工作不需要任何技術基礎,只要有手就能做。
電子廠開在郊區,距離我的正式工作單位有兩個小時的路程,需要轉三次地鐵和兩次公交車。
廠裡的工人都住在對面的一座爛尾樓里。樓蓋了三層的樣子,像個小別墅。第三層沒收頂,成了一個大天台,曬著幾床油乎乎的被褥,刮大風的時候,那些被褥隨著繩子擺動而直挺挺的前後移動,像一張張發污的鐵皮;一般的時候它們都是死一般的靜止,微風是揚不起來的。
只有一二層是封過頂的,一樓的牆四周都倒塌的倒塌,腐爛的腐爛,破爛的窗戶殘口伸出雜亂的藤蔓,茂盛地瘋長著,下面是粉碎的玻璃渣子。所以從外面看似乎只有二層是剩下完好的。後來我知道玲姐住在那一層。
(三)
玲姐是廠裡的財務會計,是我在電子廠認識的第一個人,廠裡的人都叫她玲姐,而她看起來只有三十五六的樣子。
那天她穿一件紅色的緊身短夾克,一條豹紋打底褲,勾勒出大部分男人在晚上意淫中的身材。燙著一頭蓬松的大波浪卷,有幾縷懸在淺綠色眼皮上面。看到我之後她似乎有點驚訝,隨即拍了下大腿笑起來,
「我沒想到還是個小帥哥!」
她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拍了拍,拿開手的時候指尖輕輕碰到了我的耳垂,我的頭皮瞬間酥麻了起來,這股兒勁從上而下傳到了腳後跟,像一陣急而淺的電流。
「我先帶你去放下行李吧。」
她朝一個方向抬了抬下巴,我看到有個通向地下的樓梯,
「地下室。」
我沒想到這棟爛尾樓竟然有兩層地下室。下了第一層,有一道長長的走廊,兩側有很多個隔間,由於那些單間都沒有門,所以都掛著一層薄薄的破布,當作私密的空間。狹長的走廊只有一盞燈,不足以照亮所有的角落,但總比沒有強。
「二層空間可大,比這舒服。」 她沒有回頭,一邊往下走著一邊說道,我知道她這話是在催我趕緊往下走。
地下二層沒有多餘的牆分割單獨的隔間,看樣子本來應該是停車場,果然是很大的空間。同樣的,地下二層也只有一根燈管顫巍巍地懸在天花板,空氣中瀰漫著比一層更腐敗的味道。
她指了指我身後,我轉過去看到兩個並排的小房間,沒有門,也沒有破布遮擋,所以裡面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個是空的,另一個裡面堆著東西,門口散落著許多空酒瓶,有的碎了,有的完整著,讓我想起那些被擊中的痛感和僥倖躲開的竊喜瞬間。
我走近那間屋子,滿是酒瓶的房間里探出一隻狗的頭,隨即是一聲沈重的咳嗽,彷彿滾動起那人肺里厚厚的濃痰。
「老李,你在啊。」 玲姐喊了一聲,踩著高跟「噠噠」地走過去。
房間里一陣擠壓床板而發出的痛苦呻吟過後,一個五六十歲的男人顫顫地走出來,有意無意地踢倒了幾個酒瓶,在平坦的水泥地面上朝著四面八方滾動起來。
「這是廠裡來的新人,和你住這兒。」
她又一次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但這次沒有碰到其他地方。
男人拖著一件肥大的軍綠外套,竪著的領子遮住了下巴,頭上套著一個污黑的毛織帽子,看不清他的臉。那只狗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他腳邊了,有條後腿拖拉在地上,沾著骯臟的灰泥,瞪著一雙圓滾的狗眼看著我。
他點點頭,又拖著身子走回他的屋子,從他走動時起伏幅度過於大的肩膀看來,老李的腿是跛的,說白了他是個瘸子,那狗也是。他轉身的時候又踢到幾個瓶子,空曠的地下室回蕩著玻璃擊中水泥的聲響。
「老李以前在廠裡上班,幾年前瘸了條腿,你說人家畢竟在這兒幹這麼多年了,現在殘了,我們能不要人家嗎?」 玲姐把雙臂環在胸前,扭著胯往前走說,「我就讓他打掃廠裡的廢品,讓他住著,順便還能賣廢品掙幾個錢,就當是我養著他了……」
我跟在她後面,邁完最後一階樓梯,地下室傳來一聲嗚咽的狗叫。我下意識朝樓梯深處望去,
「這狗也是,不知道怎麼有天就跑到車間,竄到發動機底下,結果壓斷條腿,不過算它命大,」
玲姐嘆了口氣,
「一人一狗,也是惺惺相惜了。」
(四)
就這樣,我白天在廠裡上班,晚上回到地下室修改畫稿,每周給設計公司遞交成品。
電子廠有三四十號人,年紀最大的頭髮花白,看起來有六十多歲,最小的看起來只有十六七。然而這裡的人是不能靠外表判斷年齡的,那些六七十的也許只有五十出頭,而那些看起來十六七歲的也許更小。
不管怎樣,他們在我眼裡都是灰色的,沒有靈魂的,我確信我和他們是不一樣的。
而在這一眾灰色的人里,只有玲姐總是彩色的。
廠裡的女人們當面都對玲姐畢恭畢敬,私下裡三五一群對她嗤之以鼻。年輕點兒的,說她打扮過時、沒有品位;年紀大點兒的,說她生活不檢點、勾三搭四。可我看到好幾次,那些議論她的女人們偷偷往眼瞼上抹廉價的眼影,把自己的眼皮塗成和她一樣的淺綠色。
我明白她們不屑的根源是嫉妒,也許所有人都明白,她們沒有和玲姐一樣的肉體就換不到彩色的靈魂,玲姐房間亮著的燈和廠長停在爛尾樓前的車讓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白。
玲姐知道我是畫畫的,經常打趣說讓我給她畫一幅寫真,有時候她說這話時看起來像認真的,甚至邀請我去二樓坐坐。我從來沒有去過她的房間,玲姐也知道我是有女朋友的,她見過高芮,打量高芮的時候,帶著一種羨慕又同情的眼神。
我們單獨相處的時候,她總會說一些很有隱喻的東西。她的捲髮披在肩上,環抱著胳膊,嘆了口氣對我說,
「你們是不一樣的人。」
雖然我也有這種感覺,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玲姐也會這麼說,她見我愣在那裡,就笑了笑走開了,說,「年輕真好。」
一開始高芮大概一周來看我一次,帶著我畫稿的提成,我們並排坐在潮濕的地下室,仍然像曾經那樣沈默不語地對視,然後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公交車站,誰也不說下次再見。
每次她來找我的時候,老李都會帶著他的瘸腿狗離開屋子,第二天早上,他就用一種嫉妒又可憐我的眼神看我,彷彿對能預感我們分手結局而感到自大,我恨透了這種眼神,那和我父親當年看我時的眼神幾乎一模一樣,都透露著一句,「我早就知道你不行。」
後來她大概兩周來找我一次,最長的一次有一個月。有幾次高芮沒有在這裡睡,她只給我帶了錢,等到她走了以後,老李就回到他的屋子,向我遞一瓶酒。我搖搖頭說我不喝酒,他就把酒瓶放在我的門口。
他大部分時間在整理那些舊箱子,那只瘸腿狗跟在他後面,艱難又活潑地討好著什麼。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這樣厭惡他,厭惡他遞來的酒,也許我知道他的預感是對的,也許我怕喝了他的酒就變得和他一樣,永遠困在地下室二層,畏懼孤獨而尋找一個生命的陪伴。
(五)
有段時間我感覺很久沒見過老李,他的屋子還是擺滿廢舊的破爛,外加一地散亂的酒瓶。晚上下班的時候,只有那條瘸腿狗會在我下到地下室時從他的房間里探出頭看看我。由於我要改畫稿,所以我囤了一些泡面和火腿腸在屋子里。那只狗被香味吸引,站在我的門口等著圓滾滾的眼睛望著我,拖著那條瘸腿,搖著沾滿塵土的尾巴。
我經常熬一個通宵,它就在我的門口趴著,也不睡覺。有時我會給它一根火腿腸,但並不出於對它陪伴的感激,我不畏懼孤獨,也不需要陪伴。雖然這樣的生活讓我有些吃不消,但想起那些擁擠在地下一層的人們,想著他們和我的差距就隔著我手上的這張破舊的畫板,便很有了動力。
然而我們這張隔著我們差距的畫板在某天事故中轟然倒塌。車間設備的機油量不足,老舊的機器沒有足夠的潤滑,崩出了一枚齒輪。橙紅色的火星匯聚成洪流在我眼前像煙花般炸開,我的雙眼頓時感到一陣劇痛,周圍的嘈雜聲在我耳邊變成了巨烈的轟鳴,像是無數個酒瓶同時撞上水泥牆後發出破碎的崩裂。
我的右眼失去了辨別色彩的功能,左眼也幾乎失明,我在設計公司的工作自然就丟了。
高芮來看我,那是她最後一次來找我。我坐在床邊,她站在門口,我們沈默不語,但一點兒也不浪漫主義。
她把一個信封放在房頭,我知道那裡面裝的不是信。她的頭髮燙成了波浪卷,在充斥著腐爛味道的地下室里,她的彩色顯得很乍眼。
這次我沒有送她到公交車站,因為她坐著設計公司的老闆的轎車離開的,看著他猥瑣的神情,這次我一點兒也不氣憤,沒有正義感,也沒有佔有欲。
玲姐從二樓下來,和我一起看著載著高芮的車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她拍了拍我的肩,在我的耳邊吐出一口氣,
「我說過的。」
那晚我坐在玲姐的房間里,依稀看得出金碧輝煌的裝飾與溫暖明艷的燈光,她穿著真絲睡袍半倚在沙發上,叼著一根煙,
「你知道,你還年輕。」
「我瞎了。」
「你還能看見。」
「對我的工作來說,和瞎了沒什麼區別。」
我始終堅信在電子廠的工作只是維持我生活的一份兼職,而我真正的工作是需要一雙辨別色彩的眼。
「誰年輕時候還沒有夢想。」玲姐淡淡地笑了,這話應該是嘲諷,但我覺得她不是這個意思。
畫畫是我的夢想嗎?我從高三開始接觸美術,我不喜歡,也算不上討厭,但這一定不是我的夢想。夢想應該是崇高的,而我只想活成和自己厭惡的人不同的樣子,這麼低微的想法不能算是夢想,如果我沒有夢想,那是不是證明我從來沒有年輕過。
「老李,年輕的時候是練長跑的……年輕的時候,誰也沒比誰差。」她說。
那條瘸腿在我腦海裡又清晰起來,我想起他的眼神和他遞來的酒,以及那只同樣瘸腿的狗。
「可我的眼,也沒法再檢修零件。」
我說不清自己是在盯著她嘴裡的煙還是她胸前的一片灰白。即便我鄙夷這個骯臟的電子廠,我還是得活著。
「是,而這廠裡,也沒法養個閒人。」
她緩緩坐直,起身,朝著我的方向挪過來,把她的煙遞進我的嘴裡……
第二天中午我從二樓下到地下室,走入陰冷又潮濕的空氣里,進屋時撞倒了許多個放在門口的酒瓶,空了的發出幽長清脆的餘音,滿著的則是短促而沈重的尾聲。我定在那裡,低頭看著散落的酒瓶,緩慢地滾向不同的方向,莫名感到一陣釋懷。
我撿起一瓶酒,抬起頭一股腦灌進嘴裡,清苦又回甘的氣泡融進我的喉管,一飲而盡後,我用盡全身力氣把酒瓶扔向房間的水泥牆,玻璃破碎在水泥牆上裂成無數的碎片,模糊而晶瑩的綠色散落在這間屋子灰白的地面上,我聽著清脆的崩裂聲回蕩在整個空曠的地下室,感覺渾身充滿了力量。於是我把酒一瓶又一瓶往嘴裡灌,一次又一次狠狠地摔碎那些空了的玻璃瓶。
那只狗拖著那條多餘的後腿走進我的房間,像在嗚嗚咽咽地低語,它瞪著那雙圓滾滾的眼睛,露出那種對我可憐又可悲的神情。那雙眼睛那麼亮,圓鼓鼓的落在四周毛絨絨的眼眶里,像嵌在一朵盛開的花上的玻璃球,那麼亮!那麼亮!
我握著瓶口,反手把酒瓶猛地砸向床板,瓶身破碎了一地,剩下瓶口鋸齒般的殘缺,我死死盯著它的那雙圓眼,想著把那鋒利的玻璃鋸齒插入溫熱的眼眶,如果血如瘋狂搖晃的啤酒泡沫般溢出,那將是它最後看到的顏色……
一瞬間我又看到它的瘸腿,同樣的瘸腿,意外的事故,想起那句「一人一狗,惺惺相惜。」,突然感到脊背一陣寒涼,巨大的恐懼隔著我與那狗的距離席捲而來,我整個人癱軟在地上,嘔出一堆胃酸和酒的混合物,失聲痛哭。
(六)
我的工作從車間到了辦公室,負責進貨和出貨,其實也就是幫玲姐打下手,分擔她的工作。我每天要聯繫各種各樣的人,每天要講很多話,我覺得我這輩子講的話都沒有坐辦公室時多,我甚至感覺到了五音的存在。
過了一段時間我攢夠了錢,從地下室搬了出去,在離廠子不遠的地方租了一個帶窗的房間,想著也許有天能把母親接過來。我大部分時間住在那裡,偶爾在會在爛尾樓二樓過夜。廠子里的人對我畢恭畢敬起來,一聲一聲經理的叫著,但我知道他們私下會說什麼。我不在乎。
我再也沒見過高芮,再也沒下到過爛尾樓的地下室里。老李再也沒出現過,有人說他喝大了死在外頭了,有人說他回老家了。他和那條瘸腿狗,彷彿從來沒來到過這個世界上,不再有人提起。
儘管我不再和他們住在一起,但我知道其實只要活著,所有人都沒什麼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