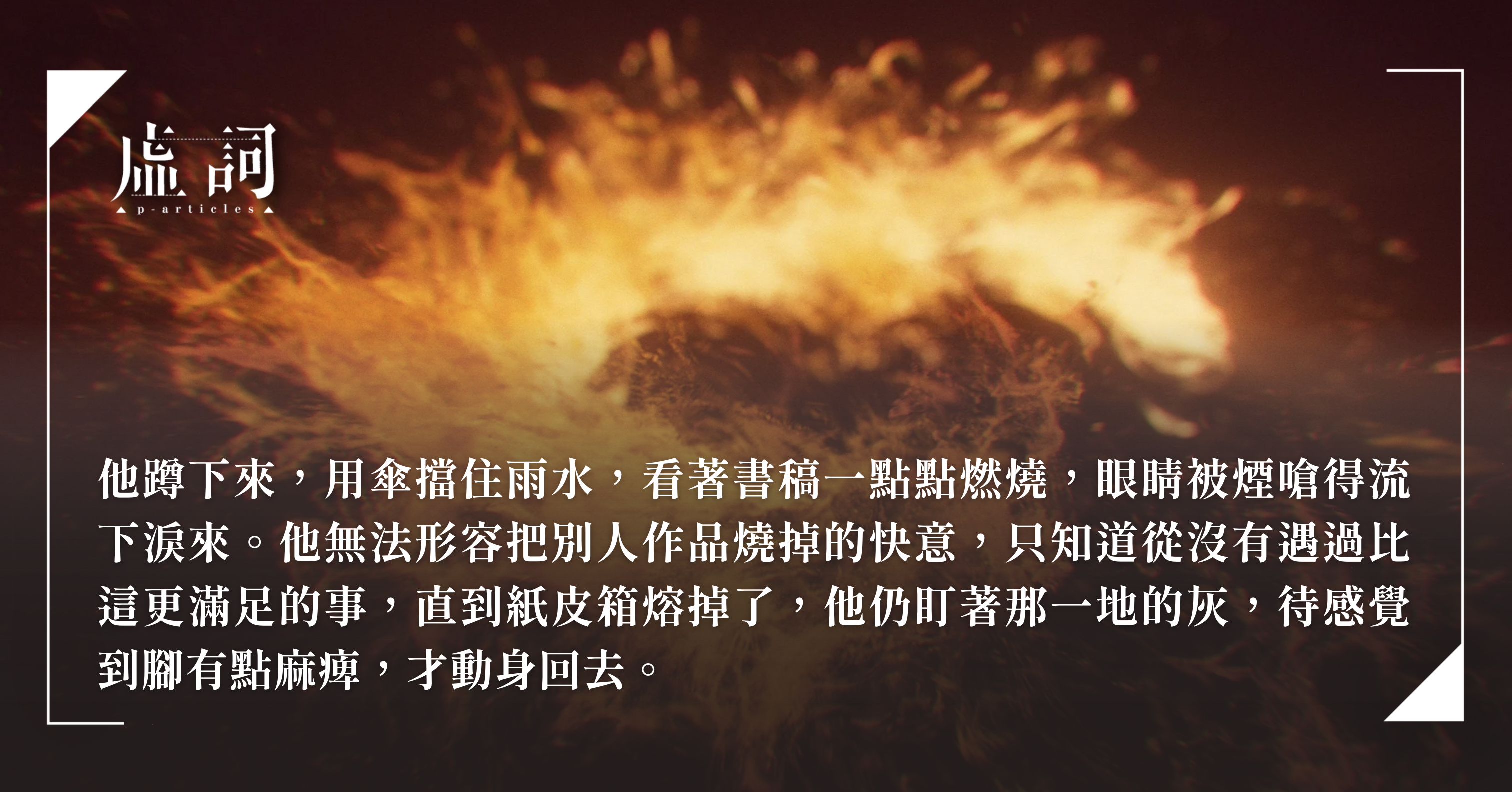誰偷走了我的意象
一整夜,阿回都維持著《後窗》男主角的姿勢,套上黑色支架的左腳伸得僵直,擱在書桌雜亂的文件與書本之間,雙手拿著望遠鏡,在那小得可憐的觀景窗內,緊盯對面房子的連治先生。
連治先生在一個多小時前便開始在廚房忙東忙西,就像一隻忙於摘取農作物的土撥鼠一樣,最終從農田裡炮製出一大盤普羅旺斯燉菜。用膳期間,連治先生用手巾抹了三次嘴,喝了兩杯蘋果汁,看了一會兒環保雜誌後,就去洗碗、清潔廚房,然後把又把洗碗水端到花園裡灌溉植物。這樣的人生,真教人看不出半點兒漏洞,但阿回知道,這個人實質是個卑鄙的小偷。
連治先生是個幾乎不製造垃圾的人。每週丟垃圾時,他手裡的垃圾袋總如發育不健全的狗隻般細小,有次,阿回因為處理前妻遺下的過期食物,狼狽地拖著兩大袋海狗般的癡肥垃圾到收集站,連治先生就看不過眼了。他不屑地對阿回說:你應該要注意一下,多做回收。阿回敷衍回應兩句,心裡卻想著:垃圾!是人存在的痕跡,沒有製造垃圾的人根本不像是個人。誰料隔天清早經過垃圾站時,他看到自己那袋垃圾竟變小了。他於是懷疑,連治先生翻了他的垃圾,幫他做起分類來。
阿回由此確認,這個侵犯人私隱的慣犯,極有可能偷了他小說裡的意象。是的,被人偷走意象,這個誰人聽了都覺得荒謬,甚至可成為另一部小說題材的事,竟發生在阿回身上。二十四小時以前,本是阿回創作事業上另一高峰、足以被紀錄在阿回的維基百科專頁內的一個重要日子,因為事隔二十年,這個十九歲便被譽為下一個費茲傑羅的天才作家,終於推出全新的長篇小說。阿回在凌晨五時完成最後一次審稿,把稿件傳送給編輯後,就倒上床心滿意足地睡去,誰料午後就被編輯的來電吵醒。
編輯:阿回,您的小說…
阿回:嗯,有甚麼感想儘管說吧。
編輯:你傳來的是最終版本嗎?
阿回:那當然,我讀過那麼多次,怎會有錯呢?
編輯:是這樣的,你那一百三十七個空白處,到底在表達甚麼?我們根本看不懂。
阿回:空白?你在說甚麼?
編輯:是的,這種寫作手法固然十分有實驗性,但會不會有點過於新穎?我們也擔心讀者的反應,而且排版時如何處理,也需再與你討論⋯⋯
阿回按耐住掛斷電話的衝動,笨拙地讓左腳降落,撐著拐杖,一拐一拐走到書房:你到底在說甚麼?你打開文檔,我解釋給你聽⋯⋯咦?怎麼可能?
阿回打開電郵附件,只見書稿的第一句是這樣的:
在他醒來以前,————已經在那裡。
除此以外,小說還有其他類似的空白處。好端端一部作品,竟像個頭髮脫落的中年男人般貽笑大方,阿回一邊摸著自己稀疏的頭頂,一邊拿著滑鼠,激動地向下掃,心裡越來越慌。所有空白處都是阿回為小說精心設計的意象,卻通通消失不見,而最糟糕的是,無論阿回怎樣想,都想不起那個意象。
編輯:喂?你聽到嗎?
阿回從喉頭生硬地擠出一聲「唔」。
編輯:我剛才說,你的第一句,在他醒來以前,到底甚麼已經在那裡呀?我要提醒你,你已經耽誤了出版日期了。
阿回並沒有聽進編輯的話,一片空白的腦袋,突然冒起一個念頭:我的意象被人偷了。一想到這裡,阿回差點就要對電話咆哮,但他憑著最後一絲理智,壓制自己的怒火,說:你們為甚麼要偷走我小說裡的意象?
還未等編輯反應過來,阿回已沉不住氣,冷笑一聲:我也當過編輯,我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編輯:偷甚麼意象?你亂說甚麼?我們還有校對排版一連串工作,無法再延期了,你最好在週末前將完整的稿件寄過來。
阿回:哼,不要再裝模作樣了。我做編輯時也與你一樣,曾把作家寄來的手稿燒得一乾二淨,事後再假裝說收不到,所以我知道你們這些骯髒的伎倆,只是我不知道你們怎樣做到的,連我的電腦原檔也刪得一乾二淨。(阿回懷疑地打量四周,打開窗簾,但不見窗外有人。)還是你們出版社搞的鬼?我說過了,若要審查的話就不要合作,想不到你們的手段那麼卑劣。
話至此,阿回但覺忍無可忍,直接把電話摔到地上。
阿回記得,他把作家手稿燒掉那天,下著連綿大雨。那個星期像是下了八天的雨,街上途人的模樣,都被籠罩在一把把雨傘下,人們低頭趕路,誰也不認得誰。當天阿回收到了作家寄來的信件,那是一篇中長篇小說,阿回一口氣讀完後,但覺動彈不能,又重新讀了一遍。那真是優秀得讓人猝不及防的作品,文字就如傍晚時亮起的街燈一樣,散發著平實卻溫柔的力量,深深探進了人存在的內核。阿回盯著這份書稿,但覺體內有甚麼被磨損耗盡了,良久以後,從椅子上站起來,把書稿塞進外套口袋,提著紙皮箱與傘,離開了辦公室,走到公司附近的球場。
因為暴雨的關係,那個球場一個人也沒有。阿回把紙皮箱置在球場中央,從褲袋掏出打火機,點起書稿的一角,然後拋到箱裡。他蹲下來,用傘擋住雨水,看著書稿一點點燃燒,眼睛被煙嗆得流下淚來。他無法形容把別人作品燒掉的快意,只知道從沒有遇過比這更滿足的事,直到紙皮箱熔掉了,阿回仍盯著那一地的灰,待感覺到腳有點麻痺,才動身回去。
一星期後,那個作者來電問及可有收到書稿,阿回便作驚訝狀,說:我甚麼都沒有收到。此後阿回比以往更積極上班,繼續校對更多稿件,接下更多文字評論、廣告文案工作,偶爾也出席講座,安安份份以資深文化人自居,再沒有想過創作的事。
所以,阿回完全理解一個妒忌的編輯可以幹出甚麼事。回想起來,在構思這部小說時,這個編輯便一直在題材情節上說三道四,一時說這種手法已經過時,一時又說這樣寫不符合如今讀者的口味,百般刁難,必定是為了阻止小說出版。但阿回轉念又想,要飄洋過海來到這裡至少需要十六小時,編輯又如何在我交稿後幾個小時內,來到我家把我電腦的存檔刪改掉呢?
這時門鈴響起,打斷了阿回的思緒。防盜眼外竟是連治先生。如靈光一閃,阿回立刻把此事懷疑到連治先生頭上。
阿回審慎地只開了一點門縫,看到連治先生露出了幾顆潔白的牙齒,以一口地道的澳洲口音說:我來徴收下星期的年度燒烤大會費用,你之前說過會參加吧?看到阿回撐著拐杖,又說:咦,你的腳怎麼了?然後露出一臉惡意的關懷問:現在只有你一人嗎?
阿回劈頭質問連治先生的卻是:你何時開始學懂中文的?
連治先生露出不解的表情,這讓阿回更覺討厭。阿回續說:你這個小偷,快把我的意象還給我,不然我就把這件事告訴這個社區裡的人。
連治先生看起來更迷惑了。然後又重複一次關於收取費用的事宜。
阿回卻繼續連珠炮發: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多管閒事處理我的垃圾,侵犯我的私隱,算了,平日總是說三道四,要我們配合社區各種規則,也算了,但偷意象這個行為實在太離譜了。我不明白這對你有何用處,是惡意報復嗎?
連治先生的眼神由困惑轉為同情,搖搖頭,說:你看來心情不好,我下次再來吧。然後就走到隔壁房屋去,途中還回頭看了看阿回。
阿回本想追出去,轉念又覺當面追問下去沒有結果。他必須用更迂迴的方法,揭發他懂得中文的事實。
這天正是收集垃圾的日子,阿回於是想到一個方法。他胡亂把一些廢紙、文藝雜誌、校對書稿、啤酒罐等塞成一大袋垃圾,然後一拐一拐提到垃圾收集處。回家後,阿回從兒子房間翻找出望遠鏡,待傍晚時分連治先生回家後,便維持著《後窗》的姿勢,監視連治先生的一舉一動。阿回等待連治先生煮飯、吃飯、看雜誌、洗碗,到晚上九時多,連治先生終於出門扔垃圾,明明只是兩三分鐘的路程,連治先生足足花了半小時才回來。
阿回走到垃圾站一看,果然,連治先生翻了他的垃圾,那個垃圾袋上,明明用螢光筆寫著「內有病菌」四個中文大字。
阿回縱不甘心,也只能暫時把連治先生的嫌疑排除掉了。那到底是誰偷走了我的意象呢?阿回把電腦重啟,打開文檔,看到書稿依舊充斥著一個個寒酸的缺口,這些坑洞顯得比今早更擴大了些許,彷彿是被巨大的毛蟲蛀蝕,再也無法回復原狀,嚇得阿回馬上把文件關掉。他一再試圖回想那丟失了的意象,但始終想不起那是甚麼,就像有誰從他記憶庫裡撕走了一頁一樣。
翌日,阿回與兒子見面時,一見到前妻雷,幾乎眼前一黑。阿回想:我怎麼想不到是她搞的鬼!就在阿回開始撰寫小說那天,雷致電說她要離婚,然後話筒就像是穿過某條埋在叢林深處的隧道一樣,發出把周邊聲音都吸進去的沙沙聲。阿回不知道她說了甚麼,只知道她就是莫名其妙地,不喜歡他寫小說。更何況,她留著我家的鎖匙,又知道我電腦密碼,小偷必定是她。
雷一如既往板著臉,告訴兒子飯後就會來接他走,便轉身離去。阿回馬上叫住雷,把雷拉到一旁,低聲問她為甚麼要做出這樣的事。
雷回頭,表情閃過一絲疑惑。甚麼?
阿回只好說得更明白一些。你為甚麼要這樣對待我的小說?
雷睜大雙眼,活像一隻受驚的貓頭鷹。你的小說與我有甚麼關係?
阿回不想讓場面變得難堪,盡力保持客氣:當然與你有關。要不是你偷走我的意象,我的小說早就出版了。我不明白,為何你要不惜一切阻止我創作。
雷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原來你還未寫完你那本小說?說實話,從你說要開始寫的那刻,我就知道你無法完成它。這是你的問題,不是我。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已經失去了你的寫作才華,卻一直用各種藉口來自欺欺人。我以為分開的這段時間,你會想明白甚麼,想不到你還是那樣,只懂把自己的失敗怪罪他人,真讓人失望。話畢雷頭也不回離去,獨留不懂如何反應的阿回。
阿回折返餐廳座位的時候,兒子阿初已在吃他點的漢堡。
阿初看到阿回的腳,皺了皺眉,問他是如何弄傷的。
阿回腦海一片混亂,還未恢復過來,但又不想破壞與兒子難得的見面。在混沌中,他的腦海閃現一隻獨腳的鴕鳥,在沙漠裡痛苦地站立,腳掌被沙粒灼傷。又聽到阿初再追問,喂,你的腳到底怎麼了?阿回便說,我是為了追逐一隻會飛的獨腳鴕鳥,不小心從橋上跌下來。然後擠出一個僵硬的笑容。
阿初狀甚質疑地說,騙人,鴕鳥怎會飛?
阿回半真半假地說,真的,那隻鴕鳥就在我們家附近那條橋,起初牠在橋上如不倒翁般搖搖擺擺,他唯一的腳已受傷了,顯然是疼痛難當。於是牠開始拍翼,一直拍一直拍,突然縱身躍下,飛了起來。我好想看看鴕鳥飛行的模樣,跟著牠,結果就從高處掉了下來。
阿初笑了笑,說。你傻了?你也不會飛嘛。
你想去動物園看鴕鳥嗎?你明天不用上課吧,我們現在出發還來得及,然後可在那邊睡一晚,明天才回家。阿回不禁幻想雷來接走兒子時,發現他們不見了的表情。
阿初搖搖頭說:我也想看看鴕鳥跑步,但今天不行。我吃過飯後要去田徑隊練習。
阿回有點失望,靜默了一會,又問阿初,你覺得你還未醒來時,有甚麼東西已經在那裡?
阿初皺了皺眉,問,一個人還未睡醒,又怎會知道有甚麼在那裡?
阿回但覺頭痛起來,他按了按太陽穴,又問,你的母親...平日有提起我嗎?
很少。
有提起我寫的書嗎?
你有寫書嗎?是怎樣的故事?
很難解釋。要不爸爸下次帶給你看?
我想還是不用了。
為甚麼?
總之就不用了。
不用做閱讀報告呀。就給你看看而已。阿回更大力按揉太陽穴。
不要,我覺得爸爸寫的東西很無聊。
阿回呆了呆,問。你有看過嗎?
有次在你書房,看到你寫的一個故事,但我看來看去都看不明白。你寫的這些東西,真的有人喜歡看嗎?
阿回只好支吾以對地說,也許吧。
離開餐廳後,阿回但覺頭骨深處冰冷刺痛,這才察覺到已經入秋了,空氣中結起了一層薄膜,穿透而行時寒意滲入毛孔,街道兩旁的樹葉逐漸退綠並將脫落,再過一回,日照漸短,人的神經就會如冬天的枯葉那麼脆弱。阿回想起四年前與妻兒初到此地時正值炎夏,蒼蠅周處飛,又大又黑,在烈日下穿插纏繞,永無止盡。
巴士駛進了彎彎曲曲的山路,搖晃著阿回的意識。沿路盡是陌生的風光,他開始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為了甚麼來到此地,又為了甚麼依然留下。這些年的生活如重影般在他面前搖晃,他嘗試辨析那些映像,卻只看到妻子年輕時的臉,兒子開始學行的模樣,以及一堆堆寫過的、校對過的、閱讀過的文字,一切都如下雨天時泥地上的鞋印一樣,溶爛卻又重疊起來,掩埋著他曾經所擁有的,最珍視的某種東西。而那東西隨著年月過去,就如脫軌繼續前進的火車一樣,火車徑自駛進某個山林裏的隧道,只餘下一堆疑幻疑真的蒸氣。那架火車走了多遠?它真的存在過嗎?一切都無從稽考。
阿回越想越覺難堪,心內翻滾又翻滾,但覺快要痙攣、嘔吐,他想叫停這樣的自己,心裡卻只重複著:無法自處,無法自處!就像推翻了一大盒童年時用來串手鍊的廉價膠珠子一樣,那些膠珠子從盒子裡併裂出來,大規模地、各自各地滾落下坡,而阿回只能蹲在坡上,抱頭聽著那一堆如噩夢般的、無孔不入的撞擊聲音。
阿回回家以後,把那篇牙齒漏風的老婦小說逐張列印出來,影印機的聲音,也如彌留之時大口大口地吸著氧氣的病人一樣,在凌亂不堪的書房裡迴盪。列印完成後,阿回拿著一大疊書稿與一盒火柴,一拐一拐,走到早已棄置的後花園,把書稿丟進抽乾了水,滿佈落葉殘骸的小小游泳池裡。一根又一根,他耗盡了所有火柴,濃煙升到半空,但阿回還是覺得很冷,心裡空蕩蕩的,如漫無目的地扭動的火光一樣。他緊盯著越縮越小的紙團,像是要確保意象的二度死亡,連連治先生隔著籬笆呼叫他不要放火影響社區的吵鬧聲也聽不到。
有些意象只會在生命裡出現一次。這場火燒了很久很久,最後池底被燻黑了一大片,就像一個火的影子,從此被釘在池底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