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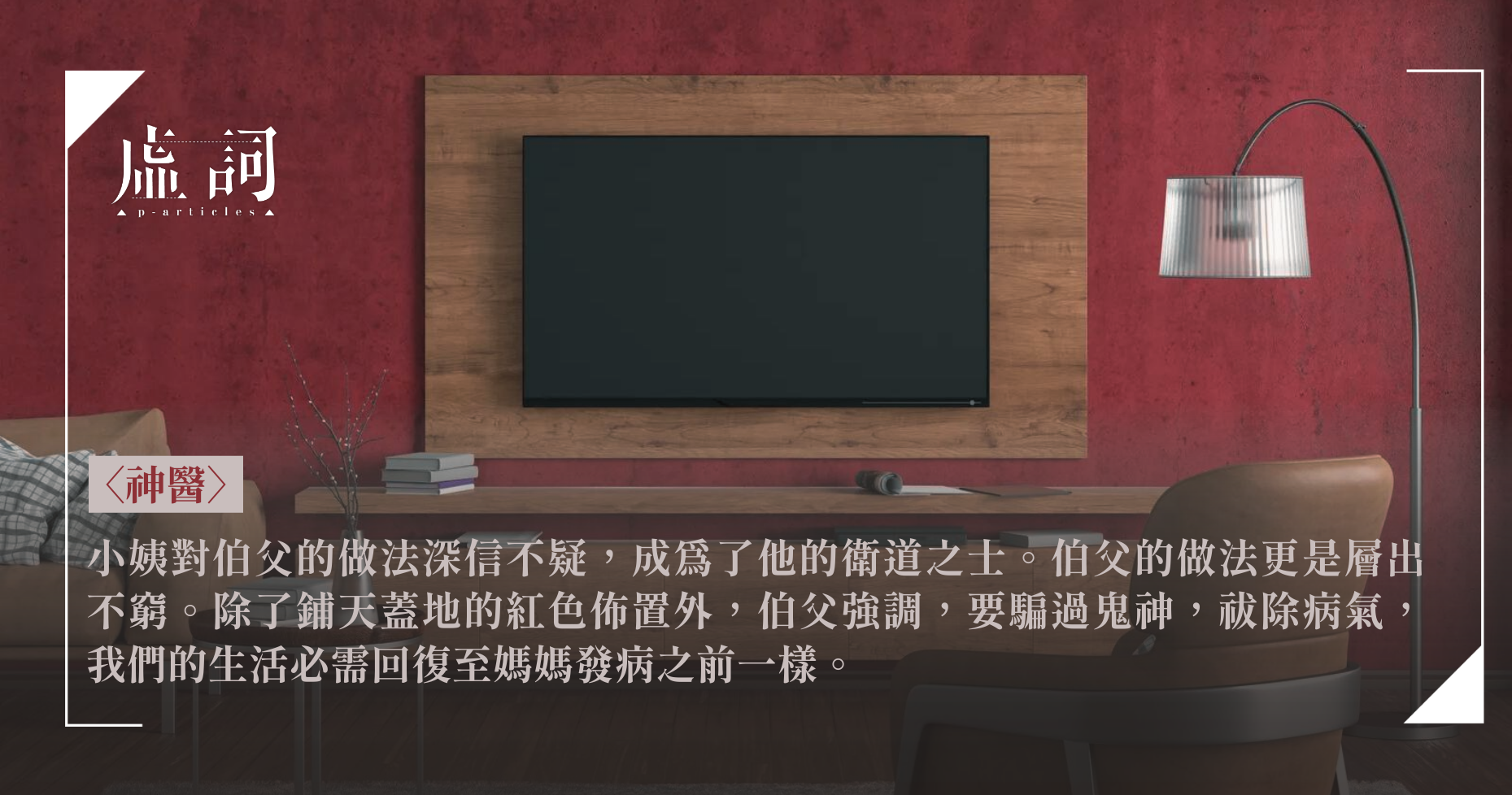
虛詞無形FB - 2024-08-18T183515.451.png
「你媽媽附了魔!你知道嗎?」
小姨突然奪門而入,雙手揪著購物袋,衝進房間。
面目猙獰,目光銳利,額頭青筋暴現,滿臉通紅,小姨像附了魔一般。
我跟小姨同居多年。她這樣子,我也從來未見過。
除了我之外,在床邊的醫生也給小姨嚇了一跳,嚇得他不慎把手上的聽筒也扔到地上。
在小姨進來之前,醫生坐在媽媽床邊的摺椅上,正拿著銀色聽筒為媽媽作身體檢查。
房間裡,只有媽媽表現冷靜,異常的冷靜,木然瞪著慘慘白白的天花板。
她的臉同樣慘慘白白,神態散渙,臥在病床上,像個動也不動的人偶。
三個月前,媽媽仍是個精神抖擻的半職家庭主婦。早上,她會到樓下茶餐廳充當清潔員。
下班後,她還有力氣打理家務,為我和小姨準備晚飯。
閒時,媽媽會製作她的拿手小菜,咖哩魚蛋,簡單而不花巧,卻比街上吃到的多了一份風味。
除了我和小姨外,左鄰右里都是媽媽的捧場客。
身兼多職的媽媽總會自誇,她的這份能耐是早年在工廠裡工作「挨」來的。
洗衣、打掃、燒飯,換來一額熱汗,她依舊氣不喘,色不變,只是偶爾抱怨身體不舒服。
起初,我們都以為她只是操勞過度而已。囑咐她多點休息,多點喝水,身體便會漸漸好起來。
可是,媽媽的精神與日漸減,動不動在喘氣,就連外出逛街的興致也沒有,終日待在家中。
四堵白牆,三十六塊階磚,大概成為了她的世界。
手機的螢光幕便成為媽媽的窗子。她只能透過這扇窗子窺探外頭所發生什麼事。
後來,媽媽連下床的力氣也沒有。家務煮飯的工作都落在我和小姨肩膀上。
「不如,我向公司請假,帶你看醫生吧…」
那時候,媽媽搖一搖頭,伸手至床前的茶几上摸索。七彩斑斕的藥丸散落在茶几上。
她隨意撿起三粒藥丸,二話不說,咕嘟咕嘟,以水送藥。
媽媽寧願到藥房購買非醫生處方的「成藥」,也不願花錢求醫。
那時候,媽媽的身子經已十分虛弱,意識迷糊,倒是還有力氣催促我快把家務完成。
那時候,我並沒有想到她的情況竟然還會變差。
有一天,我如常地敲她的房門。久久聽不到媽媽的回覆,我便推門內進。
媽媽躺在床上紋絲不動,猶如一座停擺的時鐘。不論我說什麼話,媽媽也沒有反應。
自那天起,媽媽的視線並沒有離開她頭頂上的天花板。
於是,我聘請了一名醫生專程上門看診。沒料到,醫生的出現令小姨反應異常。
小姨把手上的購物袋隨便扔到一旁,指着床邊的醫生問:「他是誰?」
「醫生是我帶來的。他會為媽媽治病。」我連忙向小姨解釋。
聽了之後,小姨更為激動,大聲疾呼:「快趕他離開!你的伯父快要來了!」
刷剌剌…話音未落,小姨身後便傳來鐵閘拉動聲音。玄關位置站著一位似曾相識的大叔。
我定神一看,那位是我長居內地的伯父。
「我把你母親的情況告訴伯父。伯父便知道事態嚴重,馬上由北京趕來…」
小姨一面向我解釋,一面揮手示意醫生離開。
可是,醫生還未及反應,伯父已經伸出肥大的指頭指著他問道:「這傢伙是啥?」
小姨正打算開腔,但我搶答說:「他是我帶來的醫生,為媽媽治病的。」
伯父馬上板起臉孔,義正詞嚴說:「你母親是附了魔,西方醫學救不了她的…」
說完這話,伯父便別個頭去,到屋各處查看。
與此同時,小姨拉著我衣袖,苦口婆心地跟我勸說。
「伯父本領高,在內地享負盛名,不要害他白走一趟,先讓醫生離開吧…」
醫生禮貌地跟我笑一笑便識趣地自行執拾東西離開。
我反問小姨:「你說伯父本領高。他在內地也是當醫生麼?還是當中醫的?」
小姨臉有難色,支吾其詞。
此時此刻,伯父神色凝重,搖著頭,從廚房鑽出來,喃喃自語。
「這單位的風水果然差到不行!你兩個還活著也算是命硬了…」
小姨慌張地走到伯父身邊,問道:「她母親有救嗎?」
伯父掐指一算,回答道:「她母親八字天剋地衝,破軍落疾厄宮…不過,她還有一線生機…」
小姨馬上面帶笑容,恭恭敬敬地向伯父合掌求助:「那麼…求求伯父盡力拯救她一命…」
「這裡最大問題是了無生氣…」接著,伯父叮囑小姨以紙筆作記錄每一個要跟進的地方。
我眉頭緊皺著,越聽越感到不對勁。因此,我主動質問他:「請問伯父是從事什麼職業的?」
伯父趾高氣揚地別過頭去,沒有理會我的打算。
小姨又笑著說:「你伯父是個本領相當高強的道長!」
伯父立時更正她:「龍虎山天師府正一派弟子之一,北京天安觀道長!」
伯父說話時看來對自己的地位十分自豪。然而,我聽得一頭霧水。
「那麼,我還是再把醫生請來好了…」我說。
可是,伯父怒吼一聲,又說:「那些醫生只懂收錢,不懂得醫你母親的病!」
「他們都是外人,幫不到手的…」小姨也從旁附和。
翌日,我下班回家,推開家門,赫然發現全屋的佈置都變了樣,感覺相當陌生。
按照伯父的說話,小姨特意在家中擺設風水陣。
為解決「了無生氣」的問題,她大費周章把家中的佈置都換上紅色,像個染血的屠房。
牆壁是紅色的,不是髹上紅漆,就是以紅色的海報所覆蓋著。慘白的天花板也被髹上紅漆。
桌椅、書架、吊燈、衣櫃也改用紅色的。所有窗戶掛上象徵吉祥的紅旗。張燈結綵。
除了紅色之外,這裡容不下其他顏色。
安放祖先神位的位置本來就是紅色的。那裡成為全屋唯一不被換色的地方,幸免於難。
小姨一面捶著自己的肩膀,一面感嘆說:「勞累了一整天,總算及時撥亂反正了!」
胭紅、朱紅、緋紅、桃色、褐紫紅……
我指著容廳牆壁上深淺不一的紅漆,問道:「為什麼會這樣?」
小姨摸一摸後腦,傻傻的笑著,說:「原有的紅漆髹光了。我唯有用其他紅漆取代。」
她輕輕拍一拍我背,安慰我說:「只要能醫好你母親便行了。我知道,這樣不太好看。不過,日子長了,我們便會習以為常的…」
傍晚時份,我在入睡前經過媽媽的睡房。房門是虛掩的,從門縫中透出微光。
我好奇,輕輕推開房門,乍見房內燈火通明。
媽媽床前茶几上的藥丸通通不翼而飛,取而代之是一盞紅色的小枱燈。
我正想把枱燈關掉,好讓媽媽休息,卻被小姨從後拉扯著,試圖阻止我。
她說:「那盞是長明燈,特別為你母親而設的,使得她睡房不再沉寂,日夜也繽紛…」
可是,事與願違,媽媽的身子沒有因此而變得健康起來。
她的面色一天比一天難看,比以前更為慘白,了無血色。
我質問小姨:「媽媽的情況比以前更差。不如真的請醫生回來吧…」
沒料到,小姨竟回答說:「你母親身體很好,漸漸有了起色,伯父的方法果然有用,只要持之以恆,假以時日,她必然恢復過來的。」
數天之後,伯父再次來訪。
媽媽依然神智不清,呆若木雞。更甚是她的身體開始發臭,房間瀰漫著酸霉霉的氣味。
伯父倒說這是由病至康的必經階段。
「由於你母親體內積聚太多毒素。這種臭味就是她身體開始排毒的兆頭,是個好兆頭…」
我終於耐不住了,指著伯父的鼻子說:「正常人身體不會無故發臭的!那顯然不是她的身體變差了嗎?」一如以往,伯父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
在他身旁的小姨反駁指:「這是你的問題。年輕人怎可以那麼悲觀呢?」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開始發現跟小姨和伯父強辯已經沒有意思。
裝睡的人只懂得強詞奪理、捩橫折曲地向人提出反駁。
小姨對伯父的做法深信不疑,成為了他的衛道之士。伯父的做法更是層出不窮。
除了鋪天蓋地的紅色佈置外,伯父強調,要騙過鬼神,祓除病氣,我們的生活必需回復至媽媽發病之前一樣。
一天,我又下班回家,經過鄰居陳伯家的門口。陳伯坐在摺椅上,從屋內叫喊著我的名字。
我在他家門前躇足,留意到他手上拿著一碗咖哩魚蛋。
陳伯主動問及媽媽最近身體如何。
我如實告知之後,陳伯頓時擺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略帶點黯然神傷。
「雖然你的小姨不斷否認你母親身體出了問題,但我老早便料到了…」
他又向我展示他手上的咖哩魚蛋:「這是你小姨拿來給我的,說那是你母親的心意。可是…這些咖哩魚蛋失卻了從前的味道…」
我心想,小姨和伯父的做法,連左鄰右里都騙不了,那麼所謂的鬼神呢?
我無法再邀請醫生到訪診症,因為小姨已辭退了酒樓的兼職,日夜守候在媽媽床前。
此外,我曾私下到多間診所求助。醫生們都不約而同指,在跟病人斷症之前,不能胡亂開藥。
無計可拖的我只好到媽媽購買「成藥」的藥房去,把媽媽的症狀告知老闆。
藥房老闆砍頭便責問我何以不帶媽媽到醫院求診。
知道我的困難後,藥房老闆開了幾袋藥丸給我。
「這些藥丸只是緩和病情,不能夠徹底治病。你還是想方法帶母親求醫比較好…」
小姨和伯父教曉我做人不能過份坦白。因此,我要偷偷把藥運回家中。
如果藥丸被他們發現了,我便會說那些藥丸是我自己的。
夜裡,待小姨的房燈熄滅了,我才竄進媽媽的睡房去。
媽媽的臉變得乾乾瘦瘦,雙頰凹陷,顴骨突出,面如死灰,吐氣如絲。
我勉強打開了媽媽的口,把藥丸塞進她的口裡。
不料,小姨驀然闖進來,一手搶走我手上所有藥丸,把我趕出媽媽的睡房。
那天之後,媽媽睡房房門多加了一把鐵鎖。
於是,我報警求助。未幾,兩名警員接報到場。
我指著小姨,指控她企圖禁錮我的媽媽。
小姨卻辯稱:「我根本沒有違反你媽媽的意願。在她同意下,我才加裝鐵鎖。鐵鎖只是為了她的安全而設。防止有人趁機毒殺她!」
起初,兩名警員都以為這不過是普通的家庭糾紛案件。
然而,媽媽睡房傳出陣陣惡臭,惹起了他們的懷疑。因此,他們要求小姨解鎖,進房查看。
床上骨瘦嶙峋的媽媽氣絕了,全身肌肉僵硬,張開口發出無聲的吶喊。
半年後,死因裁判法庭宣判媽媽死於疏忽照顧。然而,照顧家人不是法律責任,尤其是成人。
因此,小姨無需揹上任何罪名。及後,小姨也搬離這個單位,移居內地。
伯父也從此在內地消聲匿跡,人間蒸發。
至於,我…
每天晚上,我會來到亡母的房間,坐在她的床上,獨對四面紅牆,血色的旗幟下,懺悔。
09/08/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