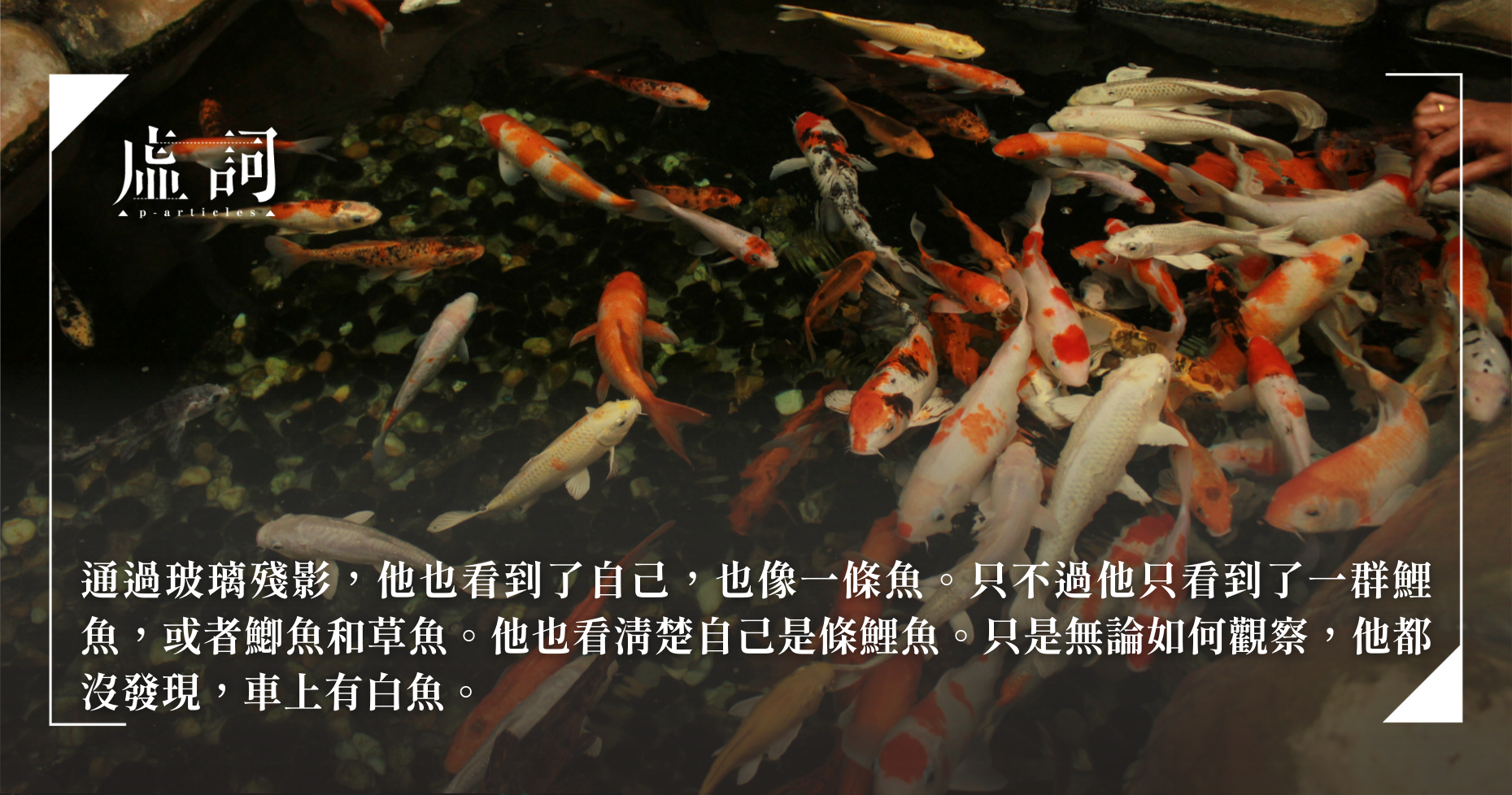等一個人
小說 | by 阿元 | 2025-08-22
阿元傳來小說,以文字與聲音尋覓在記憶深處的那個「她」。無形的聲音誘惑他以靈魂作尋找摯愛的交易,回憶停留在那夜與「她」的交纏,時間成為傷口,令歲月盡成餘波,聲音自稱是「尋找鳥的鳥籠」,擁有無限能力卻有顯得空洞無力,渴求以故事填補荒蕪。 (閱讀更多)
De Profundis
小說 | by 黎柏璣 | 2025-08-16
黎柏璣傳來小說,書寫一位飽受容貌焦慮煎熬的年長小說家與年輕俊美的時裝男模,展開了一段充滿張力與自卑的戀情。在一家象徵頂級品味的購物藝術館,小說家購買Serge Lutens香水「De Profundis」而被羞辱引爆了他內心積壓已久的慾望、嫉妒與不安。在階級勢利、尷尬發音失誤,以及嫉妒與犧牲的赤裸告白中,小說家為愛而卑微到扭曲。 (閱讀更多)
易過借火
周丹楓傳來短篇小說。小說中「我」憶起表哥憶起表哥兩度創業的起伏:初時在九龍城賣天價漢堡慘澹收場,婚後抵押「上車夢」在旺角開刨冰店爆紅卻最被其他店鋪跟風與加租,最終於時代吞沒。而「我」亦因經濟不景到了快餐店工作。某日在玩遊戲時,「我」突然回想起同在快餐店工作的年輕同事的一番話,令「我」在時間漩渦中甦醒過來。 (閱讀更多)
盡頭
小說 | by 黎喜 | 2025-08-08
黎喜傳來短篇小說,書寫遙遠的未來,美國太空總署因一篇論文的出現,宣布因「物料」的關係令到人類無法在外太空生存,繼而煞停火星移民計畫。人類歷史只能逐漸邁向終結,世界各國只能默默接受,人們看似在日常生活中前行,但失去了真正前進之途,在龐然的宇宙之中茫然徒勞。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