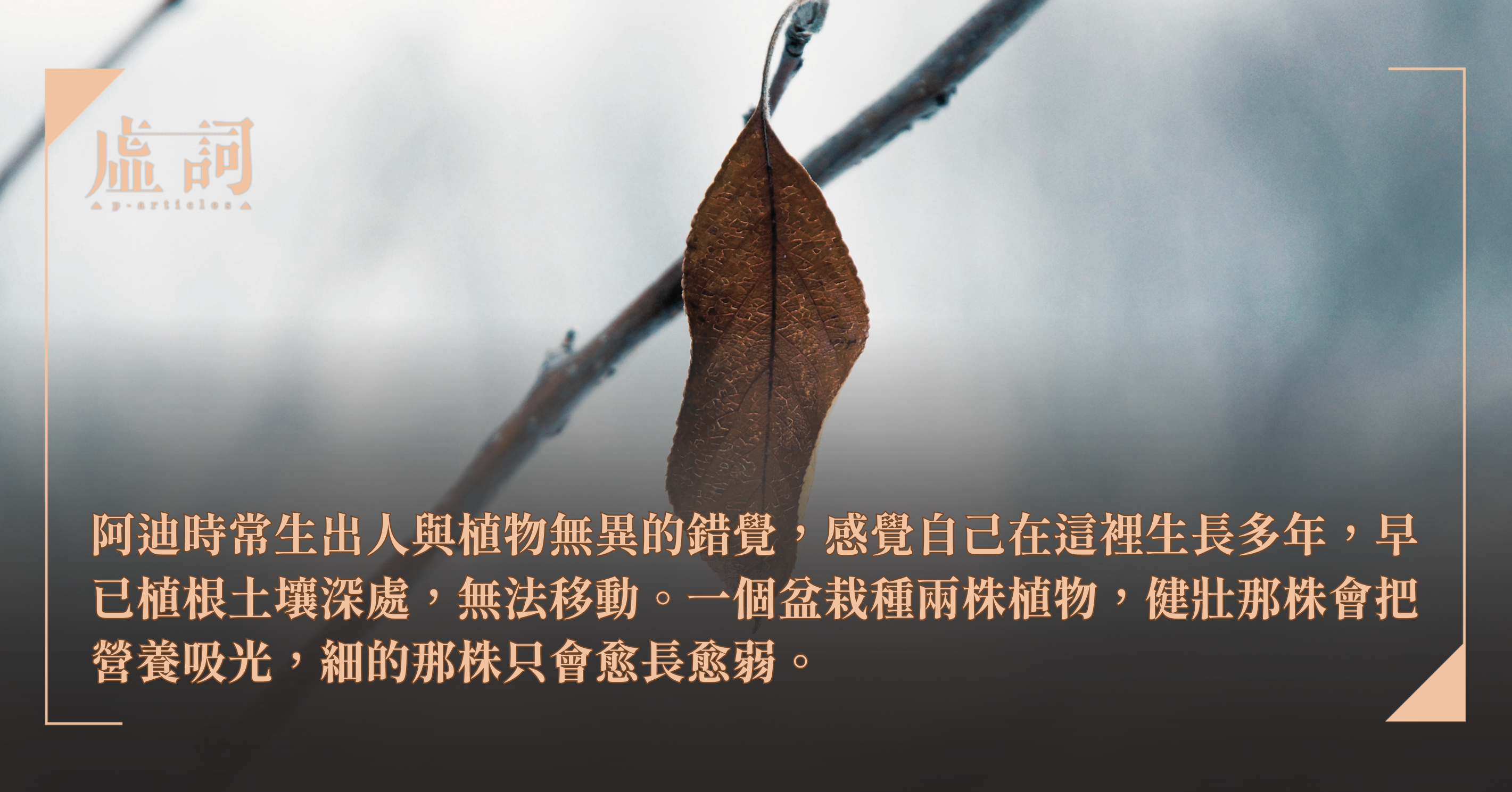堂郎
球場失修。地面坑窪不平、畫線模糊,球架有框無網。處處俱是侵蝕之痕,無皮肉,只有赤裸的骨頭。阿迪站在一條虛幻的線上,手臂彎曲呈L形,肩膀夾緊,雙腳微蹲,一切標準。籃球脫手而出,畫出一條漂亮的弧線,然後「噹」一聲,卡在籃框之中。非但沒有命中,還陷入最尷尬的境地。
阿迪下意識轉頭,看往另半場,張了張嘴,才想起,這球場早已關閉。現在只有自己這個偷獵者,沒有人能幫忙。他抿了抿嘴,但想到偷獵者這詞,又禁不住苦笑起來。如果他是偷獵者,象牙、犀牛角那些又在哪裡呢?荒廢的農莊尚有野草,這裡只剩死寂。苦等多年,這球場終現於區議會議程之中。卻沒有迎來阿迪渴求已久的翻新工程。
「呢區人口一日比一日多,唔好介意為別人犧牲少少。」議員當日的嘴臉,是他此生無法遺忘的畫面。
犧牲、犧牲,如此沉重之物竟能這麼輕易說出。阿迪把目光投往球場外,一棟又一棟的舊式公屋林立,就像是一塊豐裕的稻田。無數人被種下、培育、結成稻穗,可惜一把米只能養活一群人。這些年來隨著政府的各項計劃,人群流水般從各地湧過來。過載的農田、有限的營養,總要有人作出犧牲。這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則,如螳螂性食同類般,只有將雄螳螂吃掉,才能有充足的營養。但雄螳螂亦非心甘情願被吃,它們在交配前,小心翼翼接近雌螳螂,待到距離合適則從雌螳螂背後一躍而上,交合後儘速逃離。如果有選擇,阿迪也會逃離。
阿迪時常生出人與植物無異的錯覺,感覺自己在這裡生長多年,早已植根土壤深處,無法移動。一個盆栽種兩株植物,健壯那株會把營養吸光,細的那株只會愈長愈弱。本來這裡的球場已經不多了,那年少一個,那年又少一個。一株一株逐漸變黃,然後蜷縮成一團。阿迪也不知道現在還有甚麼剩下來,以及剩下來的還存在甚麼意義。
事實上,無論阿迪怎樣去想,重建的巨輪都不會因他而擱淺。他能做的只有把握僅有的時光,投好他的球。他往球場的出口走,說是出口其實更像邊界。球場的門早已被鐵鏈鎖上,他自然沒有開鎖之法,但用力推動門,讓鐵鏈伸展至極限,還是會露出一道一人寬的空隙。他低頭,躬身,像鑽狗洞一般鑽了出去。這種進出之法更讓他生嫌,他嫌棄的並非是低頭,生活在此再高傲也早已習慣卑微,而是這條毫無作為的鐵鏈。粗重的鐵鏈確是無法剪開,但過長的鐵鏈不如一個五金店十蚊鎖。這似乎與他所看過的種種事物過分相似,追求儀式而非效用,畫面墟冚而毫無建樹。
球場對出是一間士多,專做球友生意。老闆文哥今年七十八,看著阿迪由「口靚」仔(1)變為鬍鬚佬。「整枝可樂黎。」文哥瞥了瞥他,然後從雪櫃拿出一枝玻璃瓶裝可樂,開蓋、遞上。阿迪對很多事情都很執著,比如說喝可樂,一定要有氣,無氣可樂不如不喝。而文哥這裡賣的又是最多氣的玻璃樽裝,阿迪自然便是文哥的「忠粉」。文哥年紀雖大卻健談,兩人也算是忘年交。
阿迪仰起頭,張大嘴巴,把可樂一口氣灌進肚子。可樂滑過舌頭,酸爽而痛快,一切外部苦難似乎在瞬眼間煙消雲散。隨即沿著食道流入胃部,在胃中消解生成過量的氣體,氣體不斷翻滾,混雜阿迪的鬱結上逆,最終化成一個響亮的嗝。「文哥,想問你借個波,我果粒卡左係個框到。」文哥瞧了瞧阿迪,從櫃底拿了一個籃球給他,又說「坐多陣啦,冇幾多日可以坐㗎啦。」
對於文哥所說的日子無多,阿迪也不是太清楚他指的是︰球場動工後不會再來士多、沒有球場後文哥會搬、還是上了年紀、老去的感言。似乎都有可能,似乎可以是多選題。「文哥你金槍六十咁款,大把日子啦,不過坐多陣吹下水都好既。」阿迪笑道。文哥隨手拿出一疊報紙,卷成棒狀,往阿迪的頭上敲。「笑笑笑。你隻屎忽鬼淨係識笑。」
阿迪立即抱頭,裝痛「哎呀,哎呀,腦震盪啦。」文哥看著他做作的神情,想氣又想笑「有冇咁悶」。阿迪也覺得這樣的玩笑很無聊,但這樣的生活卻是最舒適的,無聊日子是主軸,沒有傷心的新奇事。「文哥,諗住遲下搬去邊?」「搬?冇諗住搬啊。」
關於搬遷,文哥也曾掙扎過。他也清楚地盤動工勢必灰塵漫天,一把年紀的他多半難以承受。但搬遷也並非易事。士多每月入不敷支,慶幸多年前買下鋪位,無須交租,加上生果金幫補,尚可度日。搬遷先要把舊鋪轉手,但香港老得愈來愈快,曾經無數人瘋搶的金磚頭,不再炙手可熱,加上鋪位鄰近地盤兼無人流,就算賣出去文哥也不心安。況且就算搬出去也付不起日益昂貴的租金。這種情況就像是嫁接一樣,這裡太冷、太乾、枯死是必然的,但營養不良的枝條接合往別株,也不成活。留在這裡是死,離開這裡也是死。
「唔搬?點做到落去呀?」「日子都係咁過姐。」「即係點?」
日子都是這樣過的,「這樣」又是怎樣?文哥也不清楚。很多事情都無法記下,像是日子。年輕時文哥是東九龍大力水手,後來不知道怎麼開可樂蓋後、手會發抖。文哥想過退休,但退下來又不知道要去哪裡,或者說可以去哪裡?兩天不工作,文哥就會周身不自在。一輩子的勞碌命,大概就是說文哥這種人吧。
「得過且過囉。」
比起年輕人,像文哥這類人往往能把一切看得更輕。他們的腦袋是跟螳螂一樣的,都不是長在頭部,而是長在手腳裡。被母螳螂咬掉頭部的公螳螂不會立即死亡,刻在基因裡的慾望會化成他們行動的新支柱,繼續與母螳螂交合。行屍走肉,似死非死,這樣就是得過且過。
「你份人咁求其架。」
「你理得我。」
文哥清楚所有事物都將老去,然後被新穎的替換,而新穎的又會隨年月漸長老去,所有事物都是環環相扣的,生命的進程就是周而復始。包括球場、包括自己、包括阿迪。
「你仲唔去拎返粒波?」
「是但啦。坐多陣。」
(1)原文為正寫,因網頁字型所限,以「口靚」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