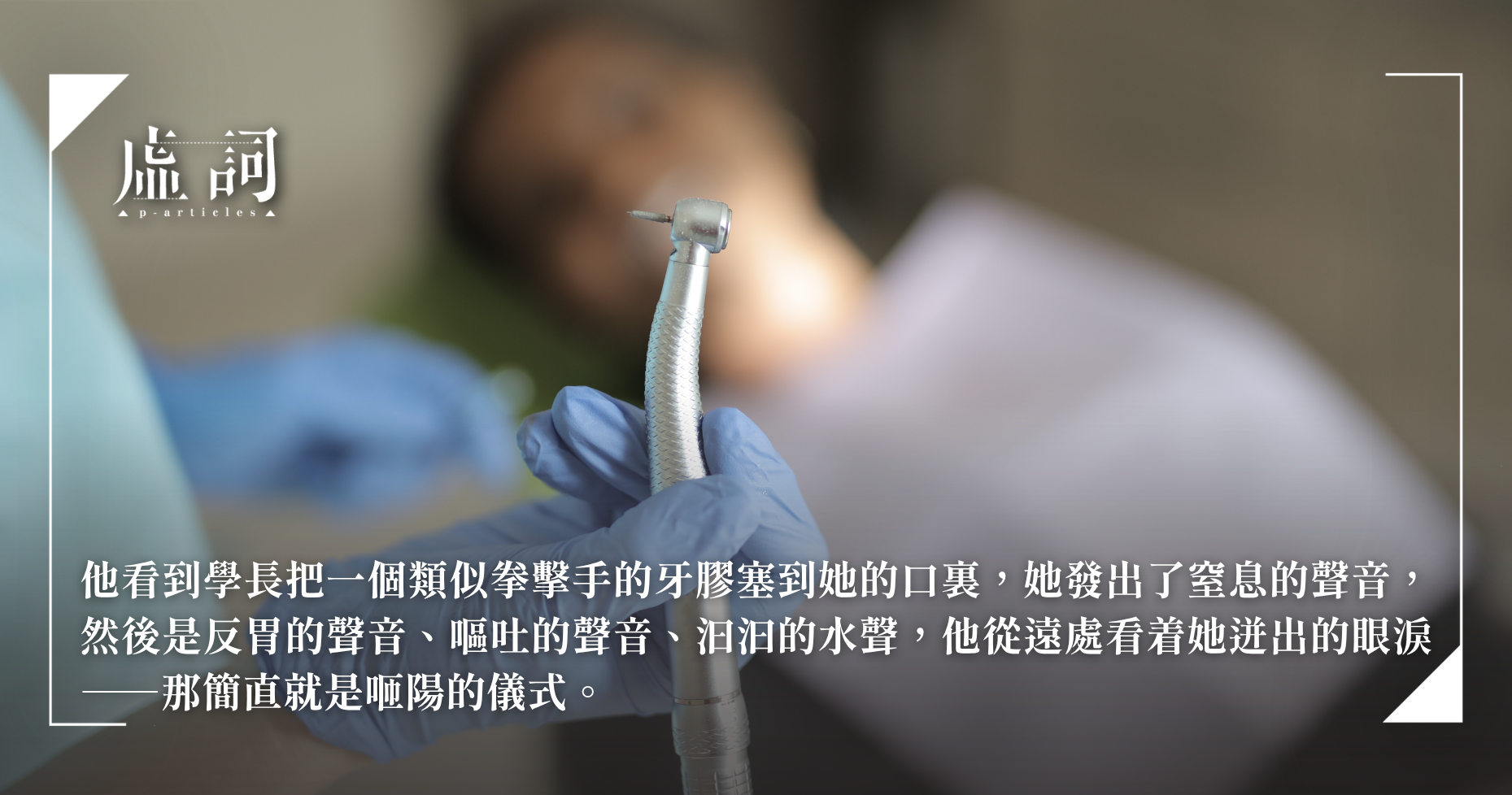【新書】溫泠《沒有女人的女人們》摘錄——〈香水〉
小說 | by 溫泠 | 2025-07-25
溫泠新作《沒有女人的女人們》短篇小說集,試圖在文學場域中為女性和酷兒創造出空間,透過女性和酷兒在文本當中的主體性,重新檢視當代不同個體的實際處境。在〈香水〉一文中,書寫了調香師湘文與妻子向瑋在結婚週年之際,向瑋提出嘗試開放式關係,讓彼此尋求更多的自由與探索。湘文邂逅年輕的念榕,並被其獨特體香深深吸引,進而發展出親密聯繫,令她對自我慾望與婚姻承諾產生動搖。 (閱讀更多)
Mackapär
徐竟勛傳來短篇小說,講述阿諦為虔誠的穆斯林女傭,多年服侍一位著名作家。當作家去世後,阿諦決意踏上麥加朝聖之旅。然而,旅行社的連番欺詐讓她陷入無盡等待,她不明所以,便循着地址來到尖沙咀,整個舖位都是毛胚屋,只有一個黑色的「麥加伯」矗在房中。阿諦將其帶回家,視為對她信仰的考驗。有日她在鞋櫃中發現海螺殼,耳邊響起濤聲,幻境中彷彿置身麥加,卻在恐懼與迷失中沉淪,意識漸逝。 (閱讀更多)
執拾遺傳症
小說 | by 彭慧瑜 | 2025-07-07
彭慧瑜傳來小說,講述母親在整理女兒凌亂房間時,憶起童年與母親及姊姊的經歷。母親小時候生活在狹小空間,嚴厲的母親要求丟棄非必需品,甚至扔掉姊姊的日記,導致姊姊消失。多年後,母親在清理女兒的衣櫃、床鋪和桌面時,見到女兒對物品的執著,擔心她重蹈姊姊覆轍,便丟棄了女兒的物品,發現自己的心態和行為重疊了當年母親的影子。 (閱讀更多)
一天
小說 | by Rudee | 2025-06-30
Rudee傳來小說,書寫「我」從早上醒來時,酸痛漫延至四肢,身下隱隱作痛,其撕裂的感覺令「我」低吟幾聲。當房外忽然傳來「啪咯」一聲,他終於離去,「我」便睜眼坐起,準備上學。踏進課室後,同學們談笑著畢業禮的期待。他們眼中閃爍著陌生的光,而「我」則顯得格格不入。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