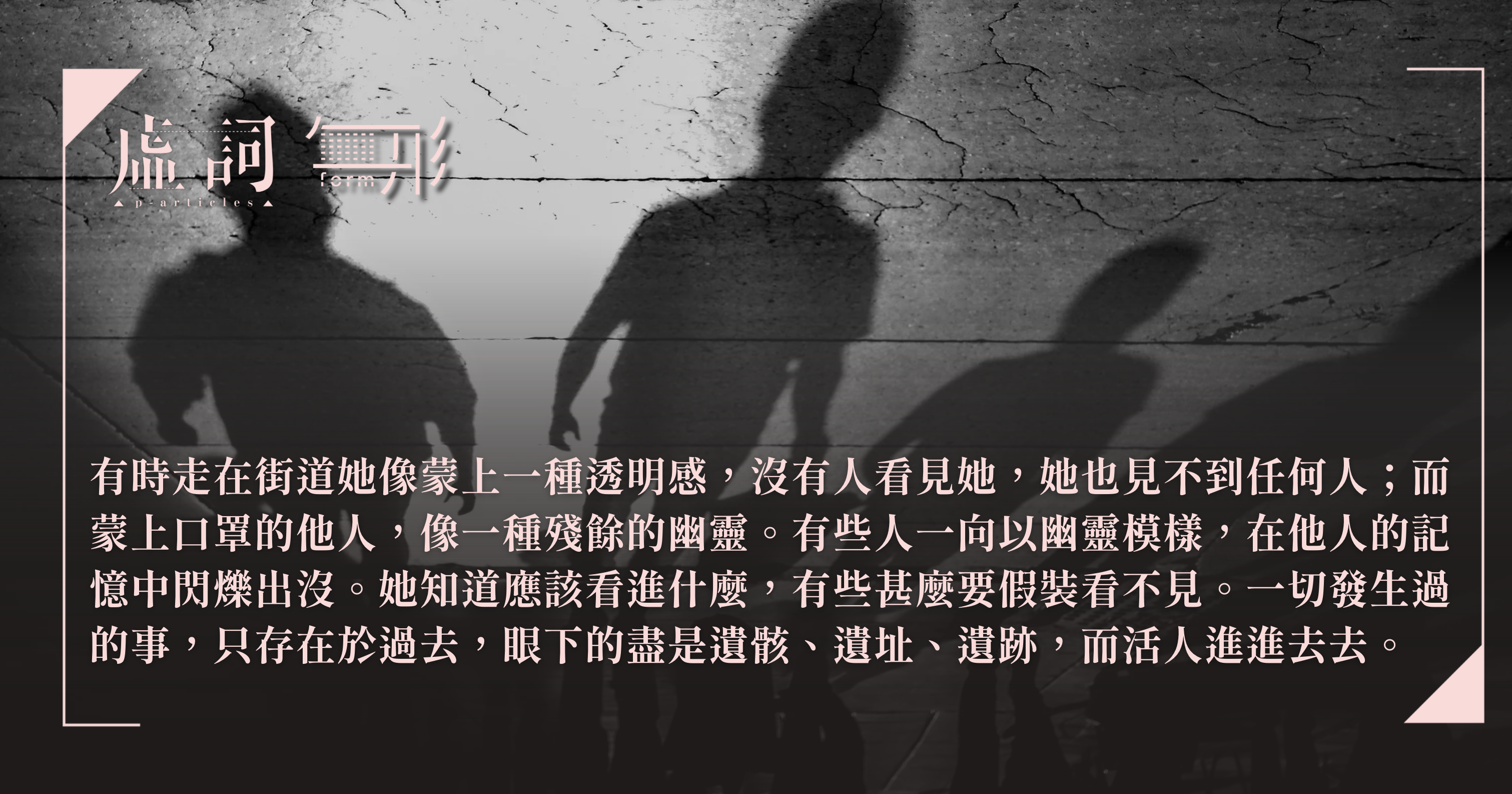【無形・◯】十二因緣
她記憶中,那夜他到了心的頂,就這樣走向沒餘地的盡頭。她拖著他的手在暗夜中散步,風暴剛過。餘風在原地盤旋,兜彎。雨粉撇得像細長的羅網。影子扁塌。髮絲如蛇。
萬物都在動中彎曲,變成圓。即使圓多次破滅。只有他的心不再迴轉、彎曲。
只有他的心從起處至末頂,直抵掘頭路,念像一枝箭穿心。
死念是如此來襲。 直不甩。 無彎轉,無彎轉。他只想到死。
她仍然記得,有種奇異而均衡的光,從不知哪來打在他臉龐,臉的陰影不知何時消失。有種石灰雕塑的靜定,同時死寂。他體內的魂魄像在,又不在。她不知道自己拖著個死人,她不知道他比出門前的那個他,稍微淡色了一點。
好像光不想反射他的瞳孔,他身體的顏色大概是在那時變淺的。她不敢盯著他的眼珠良久,為了不願看見他眼中詭異的平靜。
他說:「我要去一個地方,你再找不到我。」她仍然未明。他不想講一個死字,換了「消失」、「不見」、「不在」、「那件事」。她試過模仿他的句子,用一些字扮演另一些字:「如果你做嗰件事......」「如果你消失了......」 每個假裝的字後面,都有懸崖。那夜,每一個字眼、句子或者沉默之後,都是懸崖。有點像他腦海中想像的地點:
那臨海光滑而靜穆的石。 世上唯有那石有墜落的傾斜。只有那海能不留痕跡容身他。
她想像,只有飛躍的動作喧囂。其餘就是不曾有過喧囂的寂靜,如同平常的任何一個夜深。夜深至,甚至沒有一雙活物的眼睛曾經見證過。她不是不明,她只是不想估中。估中又無獎。
搵笨咩。
某一些時刻,某人無被察覺就這樣,離開了。他就想選擇這一種死,靜得如此,最好母也忘記曾經生過他的那種靜。沒有人哭,沒有人思念的那種靜。生命本屬的靜。
他挨向欄杆,朝漆黑湍急的河道,找一種死的靜。
這夜他有過很多次從這種嚮往中,回過頭,看她。很多次。多得她以為每次是最後一次,然後他就消失。她每次都想到孤零零的鬼魂,因失去了生,漸而失去臉,失去記憶以及失去死。
因此,她沒有可能尋到一副孤零零地漂浮在海腹的屍首。她只想到他孤零零,卻沒有想到自己孤零零。她因著他心的荒土,一毛不拔,而以為自己豐饒大能。她的確如此,她想用她的豐饒假裝成春天,像一席風臨到他裂口的大地。
「明明有我,你何需死?」
「不,有你才必須死,不然就成為你的負累。」
然而此時,只有兩個面如死灰的人,你眼望我眼。她問:「為甚麼是這一晚?」偏偏是這一晚,生或者死都像命定了般:為何偏偏要在這夜?
出生或者死亡之前,為何都毫無預兆?
八號風球剛過。故此,風是末端的風,尾聲的風。無由來地狠狠刮過,又無由來的靜如死水。彷彿空中有著眾多漩渦。像他腦海中的念頭漩流,沒由來地想到生命終點的樣貌,每個念頭都要帶他遠離她。
因而他變得稀淡。
她逐漸看不見他。
像這夜末端而躁動的風,卻把一切連同她吹到像要折枝了。
唯有此時,整個世界把他兩人排除開,世界與他們無關。好像他人的生命,重複地劃行前進,只有他們頓足在原地。沒有前路,也沒有退路。夜半的途人有了歸途,但他倆人可能沒有。歸途上,他多次往黑暗的河道望進去,想像那一片湍急的漆黑裡,是否甚麼也不存在?
水將一切沉潛的流向哪方?
最終還是剩餘一點甚麼,在水中不滅,隨無明漂流麼?
他停止了歸家的腳步,想像自己跳下去的情景。
他問,你曾經也想過死嗎?
想過,但現在再也不想了。從前創造過的地獄都成了空廢。你呢?
我想到我這些時日,原來都是賺回來的。我很久以前就應該不在人世。
他想到,所有的生之前,都是死亡。同樣所有的生之後,都是死亡。
那一陣急雨,驅促他們離開了樹,走進大廈的背面,那裡有兩張老人家打躉時坐的空椅。雨水滴落斗大,把某處敲響,啪啪啪,打破一些沉默的時刻。後來才知道是渠蓋因水多湧出來而晃動,那是鐵的聲音,而不是水的聲音。那夜,一切的驚動通通代表了凶兆。她故作淡然,把椅子壓住地下水的吞吐,壓住想上竄的遊魂。那夜,行經他們的人都無異樣,好似他們是透明般穿過他們。
旁人沒有意料到這一夜,有些人徹底地改變一生,有些甚麼注定扳不回來。
安靜屏息到一個極點,臉會冷白得像月。他的情緒與記憶彷彿沒有了實體,只餘影子的倒映與遮蔽,一切顯得隔膜。
他對著她無動於衷。說,你的說話像水,無效也無染著,充滿了漏洞般流過我。我幾乎不心痛,不悲苦,我甚麼感覺也沒有。你說的每一粒字,我都聽不見。
看著你的眼淚,我只感到無聊。
她看著他的眼瞳,並沒有映著她的身影。他的眼瞳無情,幾乎甚麼也沒有看進去:「生命不過如是,生命原來是這樣淡薄、無用。」
大概此時比平時更像佛教說的,如夢幻泡影。我們都是虛像,都是心的投影。她仍苦苦地叫他望清楚,尚有肉身的他倆,在戰慄般的心跳聲中、依然對著生命謙卑,低微,並且,並且共同凝視頭頂一枚不動也不散的浮雲......
彷彿連時間也失效。
生命像夢,但毋須把肉身的你我也一同像幻象般摧毀、消融。
我們從來不是泡影,不是夢。
對嗎?
她再度從他的眼瞳看到了盡頭,他走進他的黑暗之中,坦露如此之深的絕望感。一個人對著生命是可能抱有這般的棄絕。他以為誠實便等於真實。他這一刻絲毫沒有想像力的誠實,帶他走進假想、死的空中樓閣。
他說,我所見到我的未來,並沒有你。我看不見你。
她幾乎就要追溯一個人的沉落海底的姿態,生命就這樣草草埋葬。她覺得他愚蠢至極,她沒有對他有任何同情、憐憫。對於他黑暗裡的臆想、墮落,她只感到無稽(如同他對著她的淚水,感到無聊一樣。)她無法理解一個人的絕望,並且要以這種方式扒開自己的無望。然而明明她也曾經歷過別異的絕望:
「我正要死去了,而你無法阻攔我。」他想把自己埋回墓穴,假裝不曾出生。
此刻,眾多的自我成了他的鬼,一時上身,一時離身,時哭時笑。她熟悉這些鬼佔據時,他的神色。
他並沒有固守著自己真正的樣貌。
頃刻,他竟變回個幼童被遺落般,神色無辜而悲哀。
夜裡萬物的影子都在風暴的餘波,搖晃,示現幾重,影子脫離藉著倒映而來的事物真身。影子此刻是眾多生靈,伏卧在路燈所透光不入的大片暗潮中。她不知道此時的世界,有超過一半她不敢踏足的土地,彷彿影子比真身還要早誕生。
她不曾見過這樣的他。好像他被附魔,魔把他的神色定義,她認不出他那雙眼睛。
我們等到天亮好嗎?天一亮就不會想死。好像人不過因為天色昏暗、大地蒼茫而失常。人總是在午夜沾染一些甚麼。天一亮了,魔就退散。
「請你把這一晚當作小說寫下,這是我唯一能為你做。」他比之前一刻更冰冷,說他的死亡,唯一的價值便是衍生書寫。她聽到小說人物在她面前說,你寫我吧,寫下這一夜你親睹我,如何從一個活人變為死人。以及寫下他所沒有提及的:寫下往後你的人生如何陷災、失序,因你曾親睹一個愛人變為死人。
那一刻她的確閃念:這是一個絕佳的小說題材。
那從哪裡寫起才好?從未死的前一刻寫起?寫夜半他在床上翻覆,腦裡的念頭像齒輪滾筒,整夜像台機器轟鳴,只為了應驗自己曾經構想過的末日圖像:「一切必衰敗,一切必困阨。」人如何能承受終局必然的不幸與苦果?
他猛然地在心中挖坟,蔓溢著他此生的怖畏,並且化現了一頭赤裸且漆黑的小獸,正小口小口地吞噬他的心。
他低下頭見那頭小獸,不過是自己佈滿不明線路掌紋的掌心。
掌心捂著心,疼痛、顫凜。她背向他,正準備入眠。她看不見他的眼睛一直閉不上,像一雙死去的鳥眼,帶有死寂的烏亮,不曾安眠。唯有即將入眠的她正思量:明早醒來,是如常的一天。夜不過將我們的意識,沉至深海安放,好好地沉放,消散匿跡。好好地如死般睡去。大地上意識的邊界即將模糊,然而過去、現在與未來總是攪和含糊,她和他各自纏結在不同的時空,醒著。身體越緊靠,兩人的意識越分離。
那夜時間像洞,無止盡通向另一個洞。她不知道她所背向的他,在那時,已奄奄一息,因躺著而死著。
或從這裡寫起?他憂鬱症誘發於他們計劃移民開始。過去他們討論過多遍,也想像過多遍,每次他都說,時間不夠,我未夠。他未有重頭再來的本錢:因未有成就,未有財富,尚未成名。她說:我也覺得來不及,周遭墜落得太快,我也感覺自己緊隨墜落。
她曾夢到,邊界另一邊的霓虹燈及招牌,延伸至這邊,錯落有致,自唐樓揮發的光是她所熟悉的,光把眾人的臉照出了別種鄉愁。她認得那種殘缺的字體,夢中她像個異鄉人。
此城正在倒向暗寂,而人造光重新把此城照得不明不白。
「不走來不及了。」移民顧問說。只要你是香港人,幾乎都可以輕易移民到加國,還在躊躇些甚麼?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
「快追上來,好嗎?」她回頭。「快!我在這裡。」她向他招手。
別人在走,催迫著他們不得不走。
他始終想像不了,加國的天氣、大屋,稅收或者醫療。「我對它一無所知,然後拋棄一切,在那邊重頭再來。」他的畏佈大門在那時打開。自此,她親睹他一說話,嘴唇微顫,臉扎了刺般歪扭,血在心胸霍霍地貫流。
她不知道,那是他尋死的初兆。
不,應該從更早之前寫起,沒有任何預兆來臨之前。他的顏臉沒有後來的破裂,也沒有後來的顫抖。只是她再無從回憶起的一張無事、舒坦的臉,好像他的臉在更早時已死去。
後來他回憶時說通通忘了。「活下來的我,仍未嚐過真正的苦難,失魂時好似連死也未曾觸碰。」他反問,我真的是個重生的人?
「當然是。因為你沒有真正地檢視那夜,那夜你的靈魂只剩餘一半。」記憶在盜竊過去,削平過去,有些甚麼,憑空消失。只有目睹那夜的她記住。
同樣她不知道自己的記憶,同樣在粉飾過去,誘餌過去。她不知不覺間模塑一個新的時空,為了寫成一個驚慄的故事。那夜成了謎般,任他與她各執一詞。
沒有人是故事的真正主人。 「有男子也在八號風球,即我的前夜,在寶鄉橋跳下來,漁民在河道口撈他上岸。然後我們在精神病院相遇。」死不去的男子M醒來,一睜眼就看到差佬,只好謊報,自己散心時失足掉河。
「另一男子E報警時,刀捅進他左肩胛,滴著血,男子說真相是妻捅的,但他謊報是自殺。」「我不想妻被捉入精神病院。」後來他出院,換妻關了入來。
「另一男子L結實精幹,送入來時五花大綁,撞邪般掙扎大叫,整夜頌唱《心經》,鬼附身一樣,《心經》幾乎於我,由佛經變調為詛咒。」
他與另一個男人P曾在病床前,靜靜地共同背誦一遍《心經》,彷彿是石像與石像通靈,他們相視而笑。
「也有個男子H,幻覺周圍都是沙子,床舖有,食物有,衣服裡有。醫生每天巡房問他,沙子還在嗎?他拜托醫生幫他,將幻覺中的沙子除走。沙子一直在,可能有時少一點,但醫生懊惱,不知道開甚麼藥,才能把他幻象中的沙子弄走。」
沙子無孔不入,在故事內,也走出故事外,此時也填進她的臆想的縫隙之中,揮之不去。
他笑著形容:「一室是自殺不遂的痛苦的男子。」醫生每天在辦別,誰在說謊,誰無藥可救,只餘沉淪。不少病人返復多次地出入醫院,開始每人都懂得謊報:沒有自殺念頭,並且籌謀下次的計劃。她再一次見他時,他剛從自己的惡夢中,醒來不久。夜裡他持續地為從來不下床、一直昏睡的老人蓋被,蓋得密不透風,像在夜裡無聲色地造山。山微攏,唯蓋著山的人靜待死亡。他憐憫,因而獲取些微的生存意義。
後來他出院。
保住條命。
她把一朵馬櫻丹別在他的左耳渦,好像世界是從那時開始重生的。她一邊尋找,午後日的光源,一個月來,他不曾曬過的日的光源。光源剛好把他生而為人的輪廓,素描一圈,鍍刻的光,如那朵馬櫻丹,也是重生的隱喻。
她記著此時,想把一切最美好的想像,饋贈予他。
但人不能與上一刻的過去,決然割裂。有時他像另外一個人,有時他好好的,蒙有一浸昔日的疊影。
連他身上的味道也改變了,她也不敢再提移民的事,彷彿觸發起原始的恐懼,把根從泥土拔起時有死的預感。無根就死,花是人也是。
不是所有人可直面凌空數秒的根,橫越故鄉,直抵別國。
他後來說,困在精神病院一個月後,期待走出監牢後,從心地嘆驚生命,自由真好,空氣真甜。卻不曾有過,他因落空而靜默。「我一直等,以為等個兩、三天就有。卻一直沒有等到,那個劫後餘生的快樂、狂喜,一直藏在無人知曉的深龕。我一直依稀認為它曾存在,直到今日,仍未能確認。」 他反問,我真的是個重生的人?
她看著他,有時他的眼睛無故地滲著淚水,淺淺不曾溢出,故此連他也不知道自己悲傷。
那些移民加國的人宣揚新生,人像倒水般外流,這裡是移民者口中的流陷地。一切像沒有變過,只是這裡黑夜新造的燈火更密簇,人潮也更早散去。夏夜水淹,冬末壓縮。影子被後來的更多影子踐踏。通緝的名單越來越長,牢獄中的人的年歲也漸長。他們如常在旗海下走過,如常在選舉宣傳街站走過。
這裡有多處與自己無關。沉默與言說像銀幣的兩面,尚有第三面是隱密的。
有時走在街道她像蒙上一種透明感,沒有人看見她,她也見不到任何人;而蒙上口罩的他人,像一種殘餘的幽靈。有些人一向以幽靈模樣,在他人的記憶中閃爍出沒。她知道應該看進什麼,有些甚麼要假裝看不見。一切發生過的事,只存在於過去,眼下的盡是遺骸、遺址、遺跡,而活人進進去去。忽爾,屍體扁軟地蠕動起來。
像擁有新生的覺知般。
爬了出來。
世上從此有活人及活的死人。
她已忘記他出院後,他們第一場性愛是怎樣。只記得他一直緊張安全套究竟安不安全,後半場他無法勃起。
很多事的確毋須在對方的體內圓滿。她感覺,雙方之間有道直抵的力,不再強行,也不必強行。它會在兩人赤裸的肉身中間,攤軟下來。她也樂得攤軟其中。彷彿一切事物的制高點,不必抵至,不必仰望。
雙雙躺平。
她想想自己,一生也未曾勃起。那些勃起後射出的精液,總令她想起,多像宿醉時嘴邊的沫液;有時她甚至想到,那原來可能成為生命的穢物。正如排卵的清晨,她抹去帶有像血絲、未受精的粉紅色卵沫,也想到它可能成胎的模樣。
這種隱藏的殺意,有著攤軟下來、萎靡的意態,就留在各自的身體內罷。她壓根兒不想懷孕,卻一再想像胎的生滅始於此。
「你想過生仔嗎?」
「你想?」他問。
「不想。」她知道他不想。他聽著她這樣問,你想過生仔嗎?竟像雷嗚打進來,充滿試探的餘韻。移民、生子或者再多的變動,都像撼動著他此刻的危險想像。他靜默。
她也靜默。兩人在此時都只想著自己,沒有想及對方,甚至意圖成形的胎。
「真好。原來我們都不想。」她近乎耳語說。不想未來的女兒或者兒子聽到,此刻的愛欲男女,在密謀殺死他們。
性欲像潮退散,他睡去。
她也睡去。
終將未能出生的兒女,藏在穢物中。
更巨大的變動,憾動著安穩的危機,在寢室以外。只是此刻,如同眾多的深夜,他們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