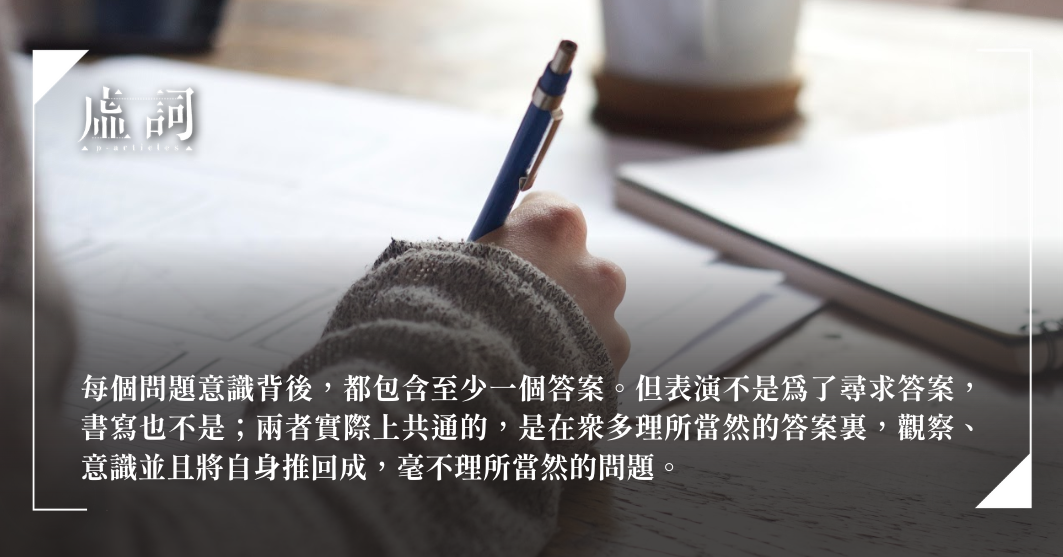關於表演書寫,三種可能的意圖
(在書寫前,我嘗試思考本文的意圖,亦即「關於表演書寫,三種可能的意圖」的意圖。但只要我把它書寫下來,這就成為書寫本身。所以我無法告訴你,所謂書寫的意圖,因為它可能並不存在。不過你可以想像,假如我們並不活在地上,而是時間之上,時間因而將我們載往遠方,使一切發生過的事都變得零碎和模糊;那麼作為觀者,書寫非關表演的可能,又是否存在?譬如在記憶裏,蒐集計劃過程中產生的每段書寫,重現表演或表演以外的,也許有一絲可能,得以講述一切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第一種意圖:暗中躺平,抛光日常
由是我在學習觀看前,不自覺身陷一場表演。身體會不自覺被喚醒,就在它未沉睡之前。連同平常被忽略的部位和關節,一一被喚醒。由是我察覺到,我們活着的本能是趨向簡易,尋求深邃是依靠意識。具意識的一幅圖畫,移動或更多時候——靜止——成為姿勢,像我們一樣在漆黑中躺下,卸除生活或生存。那是一種日曆的姿勢,但為了改變本來的形狀,我把「本來」誤讀為「未來」。然而誤讀並非表演的意圖,表演者和觀者的出發點,到底未必一樣。已死的作者行走,在水上,或者沒有。具意識的一幅圖畫,許是一幅拼貼畫:
「我在風景拼貼你們的心事,秘密是風景,聲音被握在線條,互不抵觸。互不抵觸地盛着,我們的心。紊亂是所有事情的互相抵觸。」
當我把文字精簡成「互不抵觸的抵觸」,文字提供了特定的音樂性,節奏、速度及其他。填歌詞的人,不難明白「重複」可產生「音樂性」,如此廉價卻無堅不摧。創作的幾道板斧,好比姿勢之間的過渡不過三點:一步到位、慢動作和定格。三幅被,互換交疊,透過人數、性別、年齡、時長、場地等,被建構出某段敘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情節,全由觀者想像——哪怕表演者的意圖,可能只是由一個動作,過渡至另一個動作,意識在於「如何/點」,並非「為何/點解」。無解。眼前無一物,何來塵埃飛舞。
第二種意圖:點、點、點
「想像起初是民主的。沒有中心。沒有權力。任何地方,任何人,任何一瞬,手臂揮動如擊落一個想像。點、點、點。點樣左右協調,點解要協調,如果想像起初是民主的。點、點、點。
表演也是民主的。除非它在眾目睽睽下,假裝擁抱每一位觀眾,擁抱自己。沒有人能拯救自己趨於俗套的目光。如果有眼淚,恐怕已經一輩子。生與死,愛和恨,(聽)見或不(聽)見,那些潛藏於舞蹈及言語之間的,解釋性對話。再也無法掩飾的事實是,我們終究沒有界線。
歸於平靜,歸於漆黑,像起初一樣。想像/表演起初是民主的。一個人。兩個人。五個人。十一個人。人。如果我們不再行走、站立、躺下、說話。坐着,然後對望,然後把時間還給想像,把想像還給民主。借來的時間,借來的想像,借不來的民主。當我們在黑暗中慢舞,時間就不再是資本,沒有資本,沒有權力,沒有中心。哪一剎那,當我們感覺得到,觸碰的手肘與腰間,有愛,有恨,有生,有死,有界線,有抵觸,直至沒有。
點、點、點。」
任何書寫也只能在確實的經驗下存活,更別談作者欠缺前提語境和基礎美學訓練;所有事後補充都是蹩腳的沙石。然而我們又憑何說可能,正如我們憑何說不可能。每個問題意識背後,都包含至少一個答案。但表演不是為了尋求答案,書寫也不是;兩者實際上共通的,是在眾多理所當然的答案裏,觀察、意識並且將自身推回成,毫不理所當然的問題。
第三種意圖:為了一首詩
為了一首詩
我們必須問對的問題
為了問對的問題
我們必須拒絕回答
對的真確性
但記憶於我們是怎樣的一場舞蹈
最接近舞蹈的身體是寂靜
形式的定義:內容無法盛載
講述為了活着
死亡為了觀看生命的盲目
跳舞為了活着
遺忘為了想起我們曾經記得
用回憶塗鴉日子
以身體碰撞涵義而留下
幾張圓桌提供討論
我們在各自的地面
各人有各人的事實
另類是另類的主流
是故語言失效於每場表演背後
而路仍漫漫,漫漫慘成兩齣
無關詩意的電影
馬奎斯、李屏賓、寄藤文平、里爾克⋯⋯
要記住這些名字
記住隨意的問題和回答
不為了一首詩
不為了電影
不為了表演或因其衍生的書寫
也許為了經驗本身,
以觀看來參與尤關經驗的記憶
除此以外,主體只能透過刪減呈現
不為一首詩
不為舞蹈和舞蹈的當代
為了接近
那被稱為意圖的
活着
罕有的時刻
最後一個可能的字: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