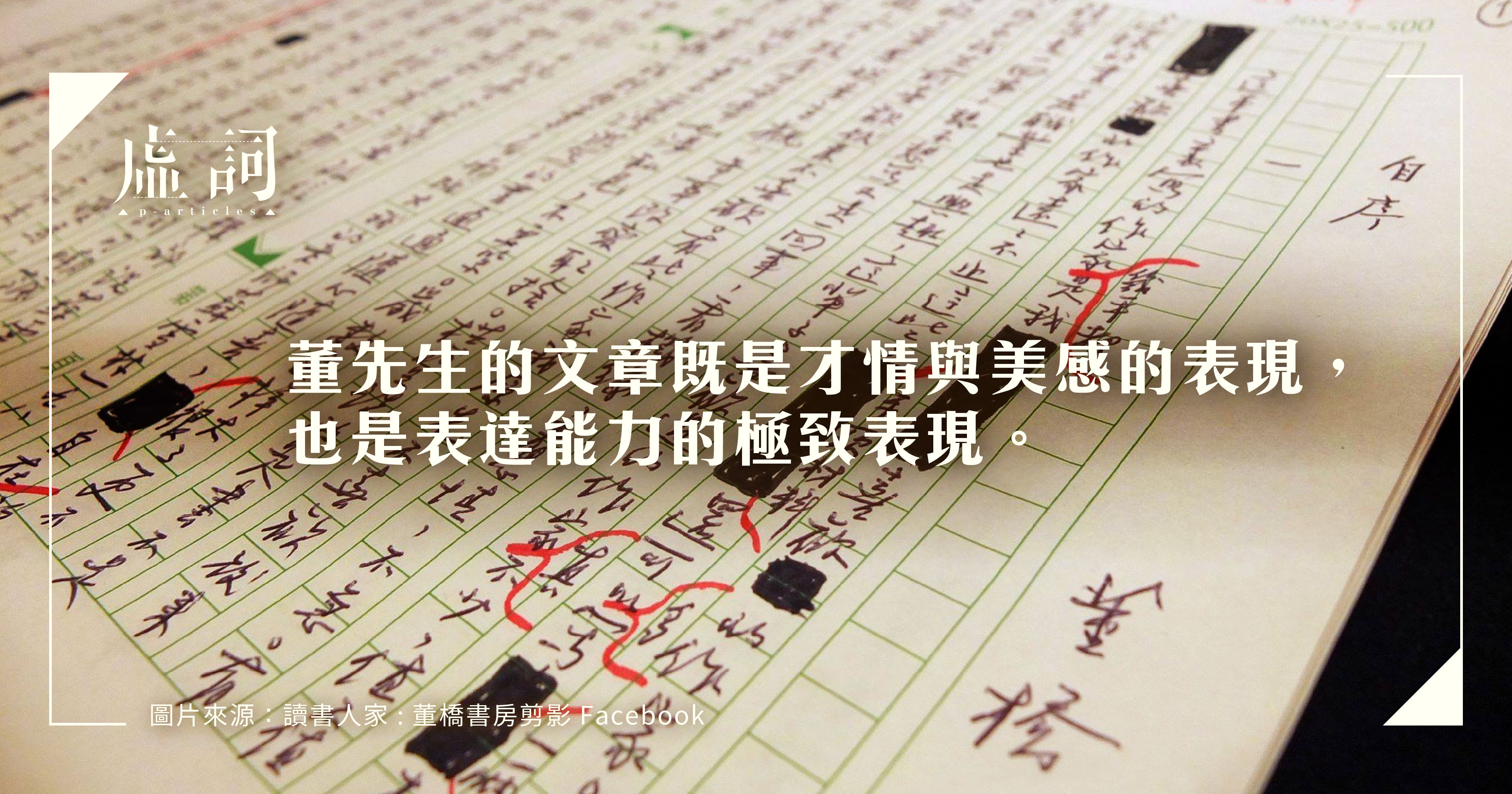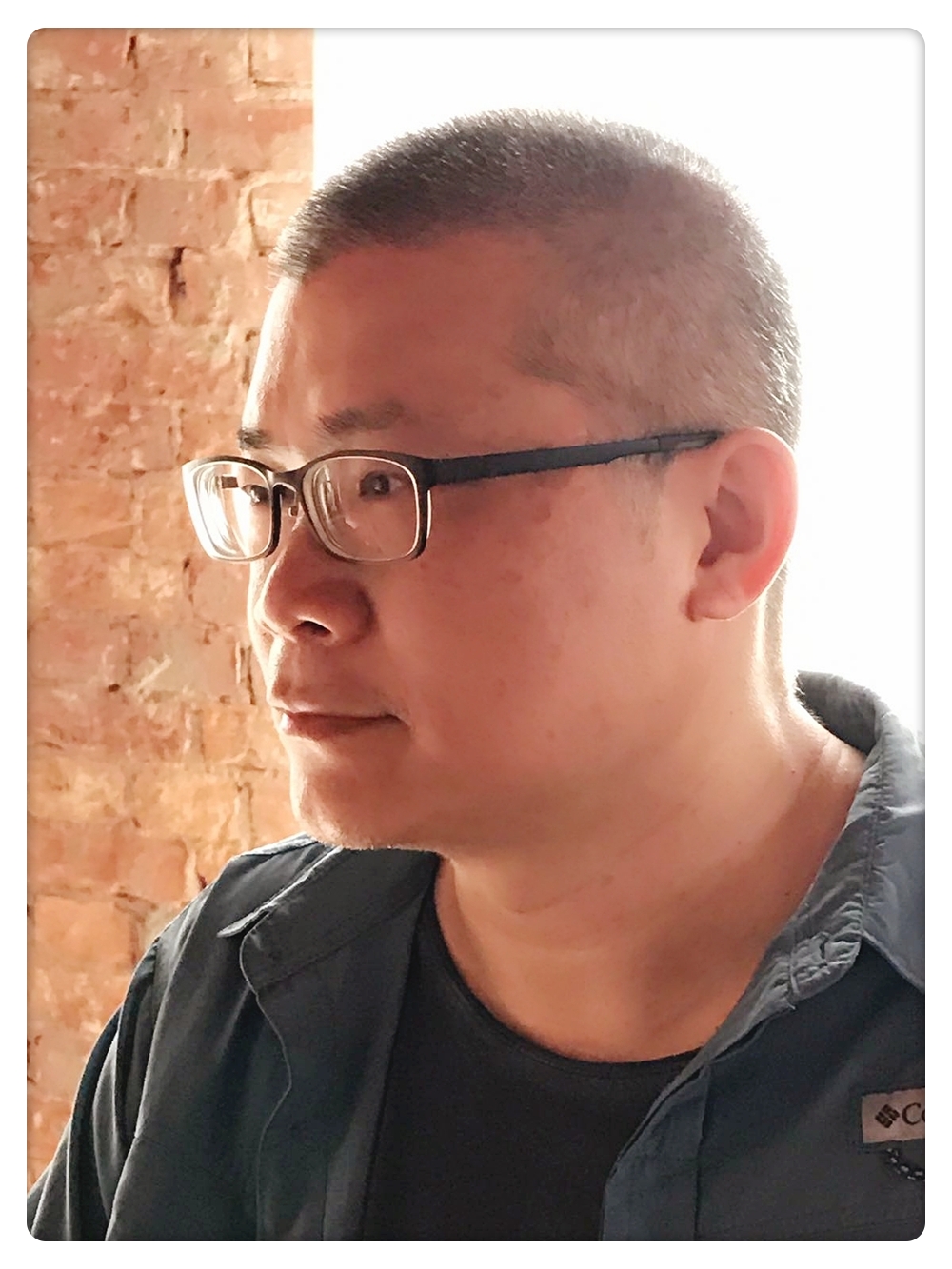「董粉」之言
知道董橋榮獲馬來西亞花踪文學最重要獎項「世界華文文學獎」,身為「董粉」的我,高興萬分——終於獲獎了。說「終於」,並非薄怨主辦單位授獎太遲。事實上,董先生得此榮譽固然實至名歸,而主辦單位授獎不授獎,也實在無改董先生是文章大家的事實。我說「終於」,是指董先生所擅長的文學體裁——散文。
「小說」是現當代文學中的「顯學」,很多人都重視;「新詩」也向來是文學體裁中的貴冑驕子,萬千寵愛集一身;「戲劇」則容易與小說詩歌或電影交融滲透,跨媒體成品既有讀者又有觀眾。只有「散文」歷來都是斯文獨憔悴,部分作家出其餘事固然也可以寫出若干優秀散文,但終難成家。今天是「小說家」「詩人」「劇作家」當道,專治散文而能稱「家」者,屈指可數,而獲國際大獎肯定與認可者,更是少之又少。
主觀感覺,小說、新詩或戲劇的作者,在成「家」這回事上,似乎不太需要經過「公認」的洗禮,習慣上,幾乎是發表過或出版過相關作品的,都可以稱「家」,至於算不算僭稱,是另一回事。但習慣上,人們又極少稱專門寫散文的人為「散文家」,僭稱者少,公認者就更少。當然,這也可以視為優勢:踏實平凡,與世無爭。
董先生是少數給公認為散文家的作家。
也實在難得,董先生多年以來筆下甘於寂寞,始終專治散文,心不旁騖。他的文章,修辭則細密而認真,內容則深邃而實在,結構則跳躍拈連斷續自如,風格則兼具中國傳統之儒雅與西方紳士之高華,表達則吞吐仰揚各得其妙。讀其文章,如讀大痴道人長卷,尺幅千里而無一敗筆。董先生的文章既是才情與美感的表現,也是表達能力的極致表現。
我常跟有志於寫作的年輕人說,無論將來要專攻哪一種體裁,都一定要先把「筆」練好——我的口頭禪是「先練好支筆」。「筆」,我將之看成是文學創作中最基本又最重要的表達能力。「筆」,就是不花巧不取巧,卻能窮形盡相,把信息或感情交代清楚。散文就是最能體現「筆」的文學體裁,學生的寫作訓練實在都應該從散文習作開始,雖未必吸引,卻終身受用。董先生親赴吉隆坡接受獎項並主持演講,他認為文章要寫得實在,風花雪月追求文字美,卻沒有實際內容,就沒甚麼意思。而「實在」兩字,知易行難,在在與「筆」的功夫有關。
董先生在吉隆坡演講的講題恰與1960年胡適在成功大學畢業禮上的講題遙相呼應:胡適當年講「一個防身藥方的三味藥」;董先生講的是「寫作的三帖補藥」。董先生為寫作處方,三帖補藥分別是博讀、膽識和冷靜,相信這三劑藥對任何創作都有補益,不寒不燥,多吃無妨,而「博讀」對散文創作尤為對症。詩、小說、戲劇或可偏重「別才」,非關書也;但散文如果缺了「博讀」,基本上無法成篇,即便勉強成篇,亦無足觀。讀董先生的文章,就最能體會由「博讀」鋪墊的清貴底氣。
先生在演講中提及一件對他影響非常深遠的往事:話說當年任職報館時,金庸曾經要求修改他文章中一個字。我看當年到底改了哪一個字已不是重點,重點是董先生說「我不會告訴你們那是什麼字。這是我的秘密」。都幾十年前的陳舊回憶了,人前一點隱瞞、一點吞吐,留白處卻依然逗得起與初戀相關的錯覺——董先生這句話講得又靦腆又矜持。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