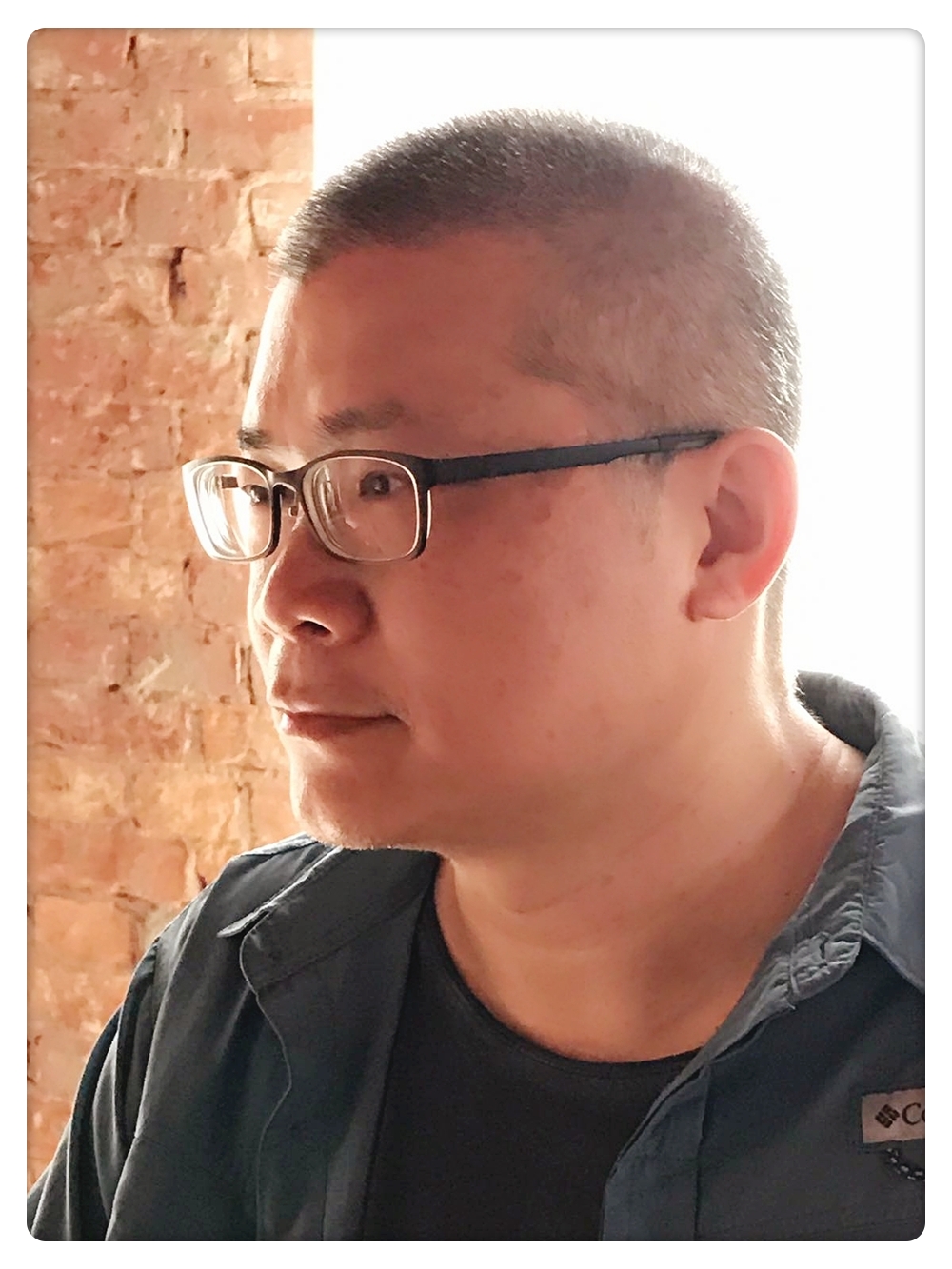笨蛋
做飯時份,母親又打「笨蛋」。小時候倚在灶旁看母親做飯,印象最深刻者,莫如母親的「笨蛋」習慣。比如做一盤蒸水蛋,母親會先直接在蒸盤內打入第一隻雞蛋,但接着無論加多少隻蛋,都會先逐一打在小碗內,然後才倒進蒸盤。當然,分量少打兩三隻笨蛋畢竟事小,也就算了;但遇上煎蛋餅或做奄列,蛋漿分量多,打七八隻蛋若效母親這般「多此一舉」,那自畫蛇足的一點點固執與愚蠢,就會漸次放大擴大甚至發脹。我終於按捺不住語帶譏諷地問:「所有雞蛋都直接打到蒸盤去不是更省事嗎?」母親笑說我不懂事:「你識乜吖,你淨係識食!」
為了證明母親的笨,我特別留意其他人的打蛋習慣。事實上,打從熒幕前的中外名廚李太方太以至左鄰右里資深人妻甚或初歸新婦,都沒有如此「笨蛋」的。打蛋,是一門很專業的學問。比如在鍋邊或碗邊敲蛋容易把碎殼推到蛋液裏,專家都建議在硬平面上磕蛋。此外,瀟灑地單手打蛋就更講究技巧:食指中指扶夾住雞蛋較圓的一邊,無名指尾指扶托着略尖的一頭,大拇指放在中部,手掌墊著雞蛋,然後在平面上輕磕蛋的中間位置,再用暗勁半扭半拉,打開蛋殼。可是,母親打蛋既毫不專業,而且程序無一不笨:既敲碗邊,又用雙手開蛋殼,還要外加那改不掉的「笨蛋」習慣。難怪父親經常數落母親,但母親回應也絕妙:「係呀,我係笨,唔笨又點會嫁你。」攻中有守,以退為進,算是平生得意之「駁」。
九十年代我初為人夫,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少不免裝腔效顰以單手打蛋入鍋,結果卻總是捏爆蛋殼弄得蛋液四濺。此後雖無奈地接受左右開弓,但始終堅持不打笨蛋。那一次,我把第三隻蛋直接打進蒸盤內,雙手掰開半裂的蛋殼時,隱約瞥見蛋液像久漚濃痰般灰灰綠綠,混濁稠滑中又夾雜些暗黃;一股近似硫磺的刺鼻異味自蛋殼內湧出。我心知不妙但手眼卻來不及協調,說時遲那時快,濃痰已跟蒸盤內的蛋液混在一起——欲辨茫然,回天乏術。看着蒸盤內金黃與灰綠相混交融,正是食之無益棄之可惜。
其實,做菜向來講究心思。刀功精細在瓜菜上雕龍塑鳳,是看得見的具體心思。至如調味精準鹽糖互濟,箇中心思雖然抽象,卻一定可以嚐得出。母親「逢蛋必笨」,在成品的造型和味道上雖完全不着一點痕跡,但過程中卻隱含豐富的人生哲理——既是「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以及「作最壞打算做最好準備」;又同時引申得出「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甚至「人不知而不慍」的意思。
母親婚後全職主持中饋,大半生為一家五口管吃管喝,責之所在,無論在刀俎魚肉之畔或灶下爐前之間,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當年在灶旁母親只薄責兒子不懂事,卻始終不肯當面道出「笨蛋」的層層深意。也許,母親不得不承認,遇上壞蛋的機會其實微乎其微;自己長期堅持打「笨蛋」只屬個人的杞憂,卑之無甚高論,不說也罷——倒不如容讓兒子在成家立室後,才把當年打在小碗中的笨蛋加到兒子的蒸盤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