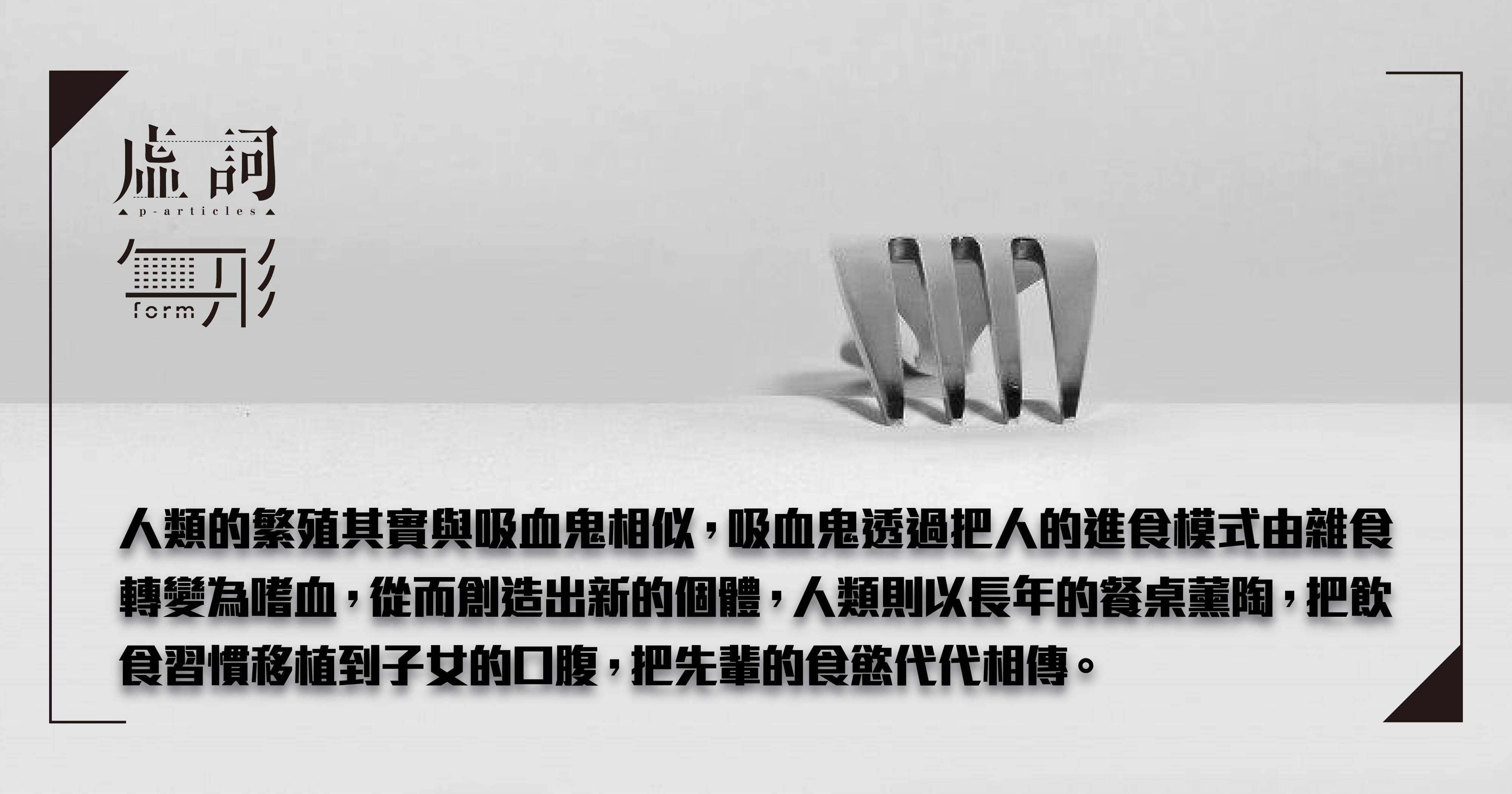【無形.和你親】飲食戰爭
我經常在蒸籠一般悶熱焗促的交通工具裡把被擠壓至變形的乘客想像成塌陷的糕點。細菌分解糖與麵粉產生的複雜氣味充斥滿室,芬芳與酸臭同席,幾乎誤以為落入了某隻怪物的消化系統,畢竟在危機四伏的都巿,出門就必須面對在不經意間被捕食的風險。有時候,我會在對面的席位上發現一個腹大便便的孕婦,好像一個烤箱,烘焙着未知的糕點,使整個場景變得更奇異費解。我總是無法在離開前鼓足勇氣,向對方索取製作配方,至今仍未揭開當中的秘密。
人類的繁殖似乎是類於烘焙的創造,把所需的材料置入,然後等待,最後取出成品,過程中無法控制麵團的生成發展。這種想像的局限在於把分娩的完成等同繁殖的全部意義,殊不知道這只是一切的起點,還須通過餵養來完成。人類的繁殖其實與吸血鬼相似,吸血鬼透過把人的進食模式由雜食轉變為嗜血,從而創造出新的個體,人類則以長年的餐桌薰陶,把飲食習慣移植到子女的口腹,把先輩的食慾代代相傳。母親把食物放進子女的嘴裏,便是利用新生命來創造世界。在門的另一面,麵條會變為河流、米飯會變為沙丘、餅乾會變為城廓,而肉體是那個豐饒世界不忠實的投影,再壯實或柔弱的體態都不足以體現它的全貌。有血緣關係的身體都通往同一個世界,每一個新生個體之誕生均會拓展其版圖,容納更多的風景。衰敗之物經腸道排出,新鮮的素材經食道補充。擁有相似面孔的小集團在共同經營着一個隱密的王國,雖然鮮少有人能夠窺探它的真面目。
母親從外祖母處繼承了濃油赤醬的烹煮技法,尤其愛以鹽份充沛的湯羹滋養年幼子女的肚腹。油膩的肉湯在冷凍後會在表面結上奶白色的脂膏,好像埋藏着動物骸骨的雪地。每當旺盛的食慾隨着湯羹的灌溉而暫時消退,一片油花花的海洋便進駐到內在的世界。有一段時間,我總是夢見穿過自己的身體,到達那個世界,卻因無處不在的廣闊水域而難有立足之地。我不敢涉水前進,一方面是懼怕迷失方向。若果血脈相連者的屬土相連而且相似,一不小心便很容易誤進母親或逝去的外祖母的領域,又或是在醒來時發現錯誤進入了一具陌生先祖的身體。另一方面,水中可能存在各式由古怪食物變種而成的可怕生物。母親嚴謹地遵照她兒時被馴養出來的口味來馴養我,即使某些食物明顯為我的身體帶來強烈的反應,也固執而橫蠻地把它們一再送上餐桌。例如那種呈彎月狀的半透明甲殼類節肢動物,在煮熟後肉質變紅,會讓我的嘴唇長出癢痛的瘡。每次我拒絶進食,總會被她冠以揀飲擇食的罪名責難,並且把過敏的成因歸咎於其他莫名奇妙的事情。還有一種把魚子炸成金黃色的脆物,母親多次把它當成一種新的發明送到我的碗裏,威逼利誘一定要我品嘗,而我每次吃罷必嘔吐大作,即使多番抗拒,此物至今仍不時以不同的名字轉生到我飯菜裡頭。我的肚腹也是一個烘培實驗失敗製品的堆填區,支撐着母親熾熱的創新精神,舌尖探勘到卷蛋夾層裏的甜味馬鈴薯泥時的震撼,至今難忘。成長中與母親的角力,在口舌之爭以外,便是口腹的抵抗與馴服。
成長後在外地生活一年,母親對此行最大的擔憂莫過於我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執行在港時的飲食模式。她的心情大概相當複雜,在關愛之情以外,也必然意識到這是一個檢驗其培育效果的好機會,若果在擺脫母親操控的情況下,仍然遵從其指示自發維持既有的飲食方式,那便宣告了她的成功。即使我無法複製她所烹調的食物,但只要我表現出絲毫對異國食物的抱怨,也足以證明她的不可或缺。然而,她的訓練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我非但沒有展露出半分思鄉的愁緒,反而在自由選擇廉價而隨便的飲食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閒適。每當我通過網上通訊軟件向母親得意洋洋地匯報每天的飲食情況,例如興奮地描繪在接近零度的氣溫下把結冰的白蘿蔔置於熱水中兩小時仍未完全解凍,以致做出來的菜餚帶有雪水的味道,她除了焦急地隔着螢幕以文字咆哮便無計可施。母親的反應刺激我更偏離她的指揮,愈發起勁地分享其他在她眼中極其大逆不道的飲食,比方說在超巿大量購入冷掉的生炸洋葱切塊或一日只吃兩餐,並持續進食同一款過期麵包。我可以想像這些透過我的嘴巴引進的大軍,與母親的食物兵團在那個世界裏交戰的盛況。一年苦戰下來,我的體型劇烈的變化,宣告了我的勝利。
母親把我從機場上迎接回來,一路上咶咶噪噪,不斷發表對我體型變化的不滿,多次發誓絕不容許我把外地的不良飲食習慣帶到家中來。回港後的第一頓飯,我便在她目光灼灼的監督下嚥下了超出我胃口的大量飯菜,從她上揚的嘴角流露的快意,我預視了我的失敗。果然,我很快又重新習得了一度失落的飲食習慣,一切的掙扎都是徒然,我的腸胃終究逃不過母親的掌控,只得無可奈何地接受,如同接受一切先輩的特質在身體上的彰顯:那油脂旺盛的皮膚、理不順的卷髮,粗硬的骨骼……在某年參與半馬拉松賽事的前夕,母親在預言我可能猝死後端出一盤肉質堅韌的貝殼類海鮮,我默默地吞下了這些難以消化的蛋白質。在翌日的賽事上我的胃部成了一個住滿青蛙的池塘,道旁觀眾的吶喊助威都被「蟈!蟈!」的蛙群大合唱掩蓋,在如同鼻涕蟲般緩慢地滑行至終點的一刻,我像一隻因逃避捕獵而失去全部力氣的軟體動物,安靜地在陽光下化成一灘漿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