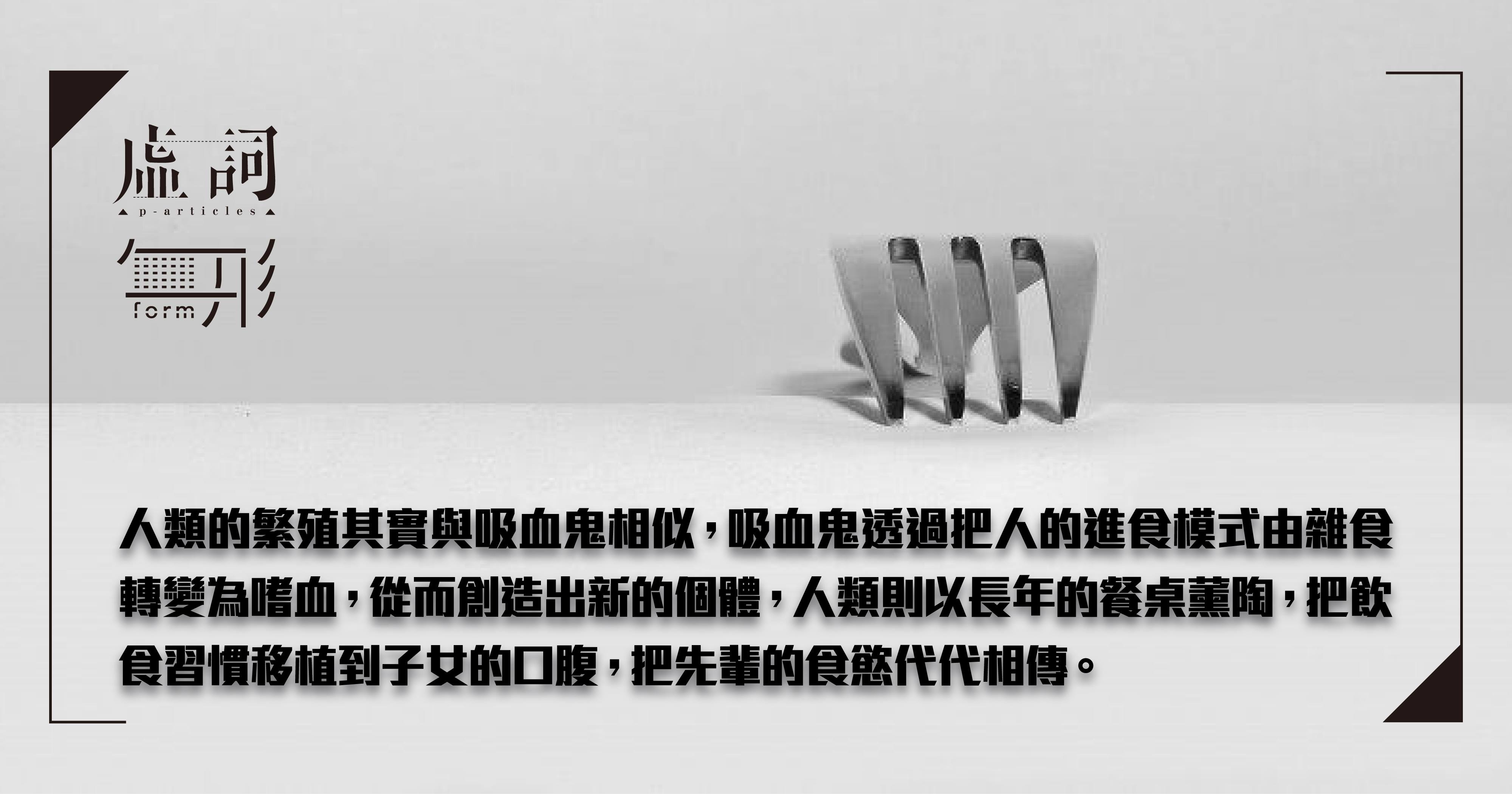SEARCH RESULTS FOR "親子關係"

《兒子》:冰冷房間裡的大象
劇評 | by 李浩華 | 2025-11-13
李浩華傳來香港話劇團《兒子》劇評,指出繪了親子間因溝通失效而生的隔膜,認為劇中父母並非不愛兒子Nicolas,而是用了錯誤的方法,使關懷變得冰冷。李浩華讚揚導演邱廷輝營造的冷漠氛圍,以及眾演員對華人家庭內斂情感的細緻演繹,突顯出語言之外的情感表達重要性。悲劇源於「子承父孳」的宿命,父親Pierre不自覺地複製了上一代的溝通盲點唯有超越「理」的束縛,用「情」與藝術去接住彼此,才能找到出口。

【虛詞.和你親】殺人犯的兒子
小說 | by 康爾 | 2021-09-23
我一直想知道,刀刃割在人身上有何感覺?跟屠宰家畜一樣嗎?滿手鮮血的妳,晚上能睡得安好嗎?會浮現被無辜濫殺人類的痛苦樣貌嗎?我確切為你擔憂。
團團圓圓缺缺
其他 | by 何潔泓 | 2021-09-23
開飯前還以為可以談談,對坐後愛恨情仇湧到飯桌上,阿言氣她不理解自己追求的理想,是一個活在舊時代的阿媽,跟這一代年輕人隔了七大洲;阿媽氣他不知感恩,何以會以為自己能夠改變世界,而她根本就不認同這個新世界。結果誰也沒碰過那幾碟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