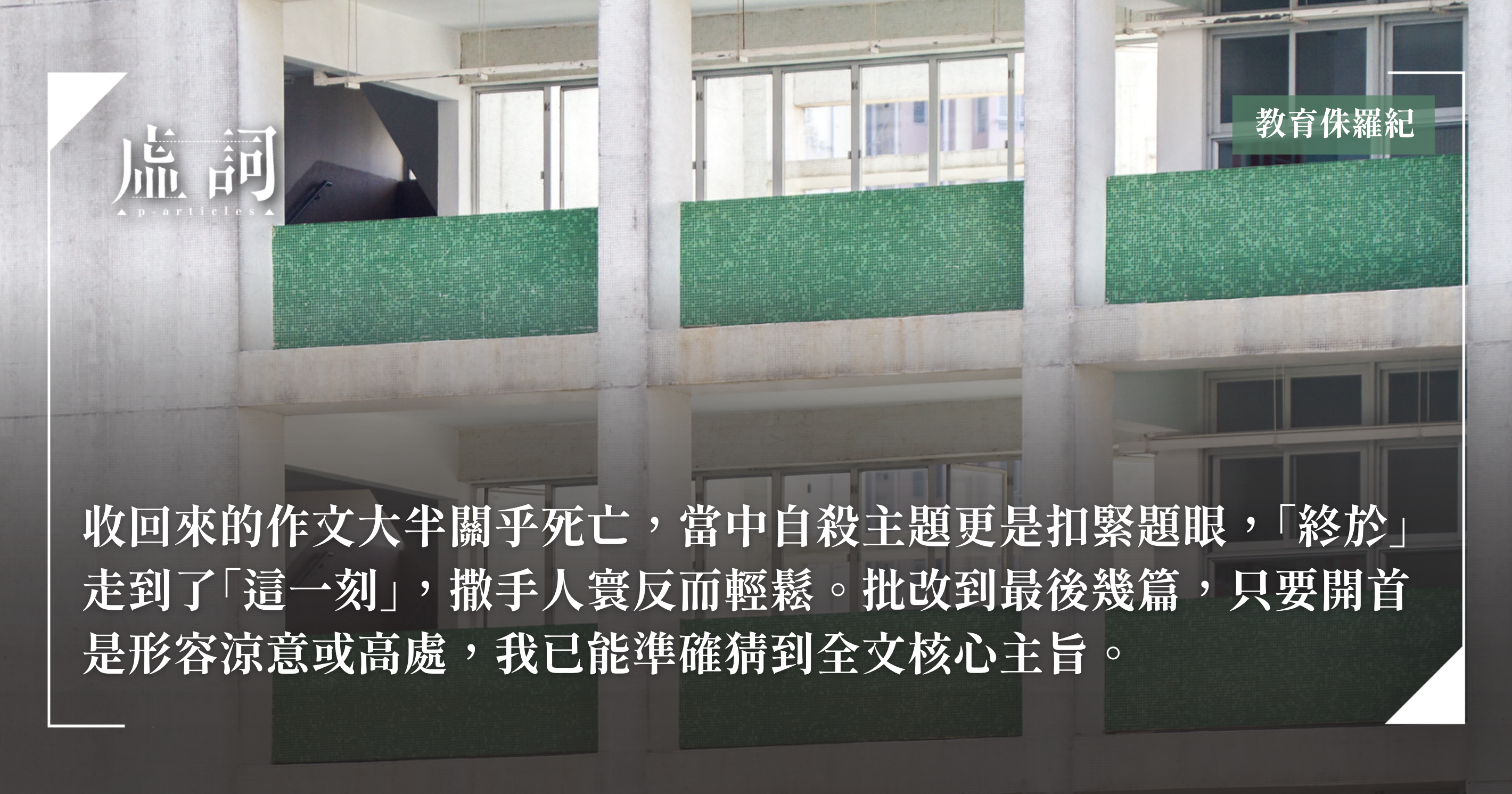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思想實驗
「十年後我都唔知係咪在生。」學生回答說,當我笑著分享我們家附近將興建地鐵站。對了,十年後,太遙遠了,我會在哪裡?此刻一列建設工人於黑洞探勘,頭燈搖晃,幽暗和潮濕,走到一個又一個給堵住的盡頭,失卻張無忌的神功便無法打出希望,只得迷惘,只得嘆息。或許是職責,工人願意繼續查找,往更深處走,但若然可以隨時離隊呢?問題重點不在於「離隊」,而是落在「隨時」,任何時間皆容讓放棄。
第一次目睹有人「企跳」,是中二體育課後。那是一個還有電話亭、酒樓會宣布誰人有來電、要駁連電話線上網、傳訊息需時、下載前要搜索種子的年代,簡單來說,是習慣等待的千禧年代初。我和一位同學到小食部買了「孖條」,便投進人群,抬頭欣賞幾個老師和校工在五樓追逐著一位高中女生,校園真人版Tom and Jerry。後來才發現更要是恐怖版本。長連式的教學大樓設計,讓女生很快就進退失據,幾位大人慢慢夾擊之下,女生決定放手一搏,推開看似緊閉的鐵閘。操場上抬頭的眾生一同嘩然——原來我們都被規範蒙騙多年——那警告不在於視覺,是埋在我們不敢躁動的心裡,形同虛設。女生很快便闖入禁地,攀上天台。我已不記得「孖條」味道,每次憶起這場驚慄,指頭都有些微涼意,那時我應沒空去攝取任何糖粉,任由它融化,在我緊張小手上流去,滴於地上等待蒸發。
一星期後的週會,是甚麼觀鳥講座,鼾聲大作,此起彼落如叢林,一幀幀雀鳥相片飛走以後,專家自台的左邊步下,一名藝術老師同步在另一邊上台,說是應校方要求,解釋「企跳」事件始末。全校師生瞬間學懂觀鳥技巧,聚精會神、不發一語地肆意偷窺一名不在場女生的情緒和人生:相信是因為交際和留級——這是校方以及社工推測;女生曾在美術課割脈,旋開門逃走——這是老師的目擊證供;門柄和走廊全是血跡——我分不清這是事實還是誇張。所以你們有事可找我們——因果推論不如課本定義。如果是現在,老師下台前或要投映一串電話和機構名字,但縮小了的我仍活在充滿「等待」的時空,藝術老師自左邊下台,領袖生長便在右台上來,宣佈週會結束,逐一解散班級。
原因重要嗎?我生平第一次,叩問死亡時間,以及放棄的可能。那時我並不知道,無數條回家路上都走著一名學生,他們全都和我一樣思索著相同問題,我們回到家,擲下書包,鬆開喉鈕和領帶,讓雪櫃的黃燈照射,電視播放著《數碼暴龍》,吮著可樂的我們被提醒自己是「被選中嘅細路」,但為何選中我們、選中我們做甚麼?得不到解答。
三年後的某英文課我舉起手,跟老師報告對面教學樓有一初中女生「危坐」生物室外,平常上課放空、睡覺的我起初得不到信任,老師親自證實後,立即拋下咪高峰往下跑,對,往相反方向跑。後來我才知道她是到校長室傳話,女生卻一直「危坐」在上,與死亡多辯論數分鐘。一切都變成形式和規矩,而會考班的我們繼續在時限內完成Pastpaper。時間計不住倒數,校長在聖經課上說:我們一秒接一秒地死亡,唯有到天家才真正存在。
現在三十多歲,幾乎可以斷定我沒有被選中,匍匐一般生存在秒鐘之中。我當然有試過EMO,一直哭著回家,但不知為何總覺得還有明天,洞穴之中一直聽到潺潺水流,又或許暗暗中看到亮光。有出路吧?若十數年前班主任告知我家門外將開通地鐵,再不開心的我,都只會回應:「十年後我都唔知係邊。」沒有語意以外的意思,真的是指肉體和地理的定位,即使身邊縈迴著「離席」氛圍,也和我有一點距離,說到為甚麼又沒有多深究,驀地回頭一看,好像當年的師長、氣氛、說話、壓力都帶點可怕甚至鼓勵氣息。可能我習慣了等待,想看看以後的世界和自己是甚麼模樣。極致一點,是想看看世界末日和自己有多狼狽。
最近和中四級文學班操練寫作題目,選了2014 Pastpaper的「終於到了這一刻」。整個審題教學都是抓住「時間點」如何設計,以及「終於到了」的情緒刻劃作主軸,舉出例子包括畢業、結婚、生子。感受昇華方面,我選了陳奕迅〈最後今晚 〉探討好友結婚前的祝福、婉惜、懷緬,最後播放五月天的〈乾杯〉去了解生命完結時的無悔。那MV最後一幕是旋開一道門,門外就是藍天白雲。
收回來的作文大半關乎死亡,當中自殺主題更是扣緊題眼,「終於」走到了「這一刻」,撒手人寰反而輕鬆。批改到最後幾篇,只要開首是形容涼意或高處,我已能準確猜到全文核心主旨。站在文學和教學層面,我為未來感到無比興奮,但之於他們個體情緒,身為師長卻對於他們繪聲繪影,情感細膩感到無比擔憂,對,是為他們的未來憂心。所以我為中五級選了2023剛出爐的「快樂的形狀」,嘗試以「逼迫」的方法讓他們正面思考,再以具象的形態描畫「快樂」的輪廓,奈何我做錯了,最後竟全組學生遲交,直到考試這一刻我還未收妥整級作文。
原因重要嗎?我盯著網上新聞,專家們執著折線圖和呼籲口號拍照,好幾個不慎展露歡顏。文字羅列著種種原因,也教導長輩如何辨識危機,防範未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無助。尤其面對過教學初年空出的桌子,加上長年累月被外界質疑工作輕鬆,他人言談間覺得教師不知所謂,那些可怕的思想實驗早就扎根於我們這群成年人之中,有小孩懂得求救已不知所措,還要在事後被追究為何沒有及早辨別。以結果追溯原因,再推敲所有的「if」,可算是比腦海中思前想後跳下升起的思想實驗還要幼稚無稽的思想實驗。
蹲在這行業多年的我,早就明白了,一切都是形式和規矩。
幾年前收到一通電話,雙方花了一段時間才認清當下狀況:對方無意找我,只是紀念冊或電話簿在開始時已給錯置。我認得對方是預科時期休學的同學,有傳他加入邪教,浴室裡哭著灌下化學清潔液。事過境遷,我們聊了大半小時,才終於談到我們失聯前的一刻。他堅強地說自中二開始就給欺凌,情緒長期不穩,最後因軟弱被歪曲的道理攻陷。「原來人在最脆弱時,是不能不依賴宗教的。」讀了十多年教會學校,第一次聽到比教義和得救見證還要實在的說辭。中二。追逐。企跳。我半夜醒來,迷糊間瞥見當年跟我分吃「孖條」的臉,滲出一身冷汗。原因是甚麼、會不會求救、察不察覺得到他人憂傷等,已是十年後地鐵站建成般的後話了。
【緊急求助熱線】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線:23892222
醫院管理局精神健康專線:24667350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18281
撒瑪利亞會熱線︰28960000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2255
生命熱線:23820000
利民會《即時通》:35122626
明愛向晴熱線﹕18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