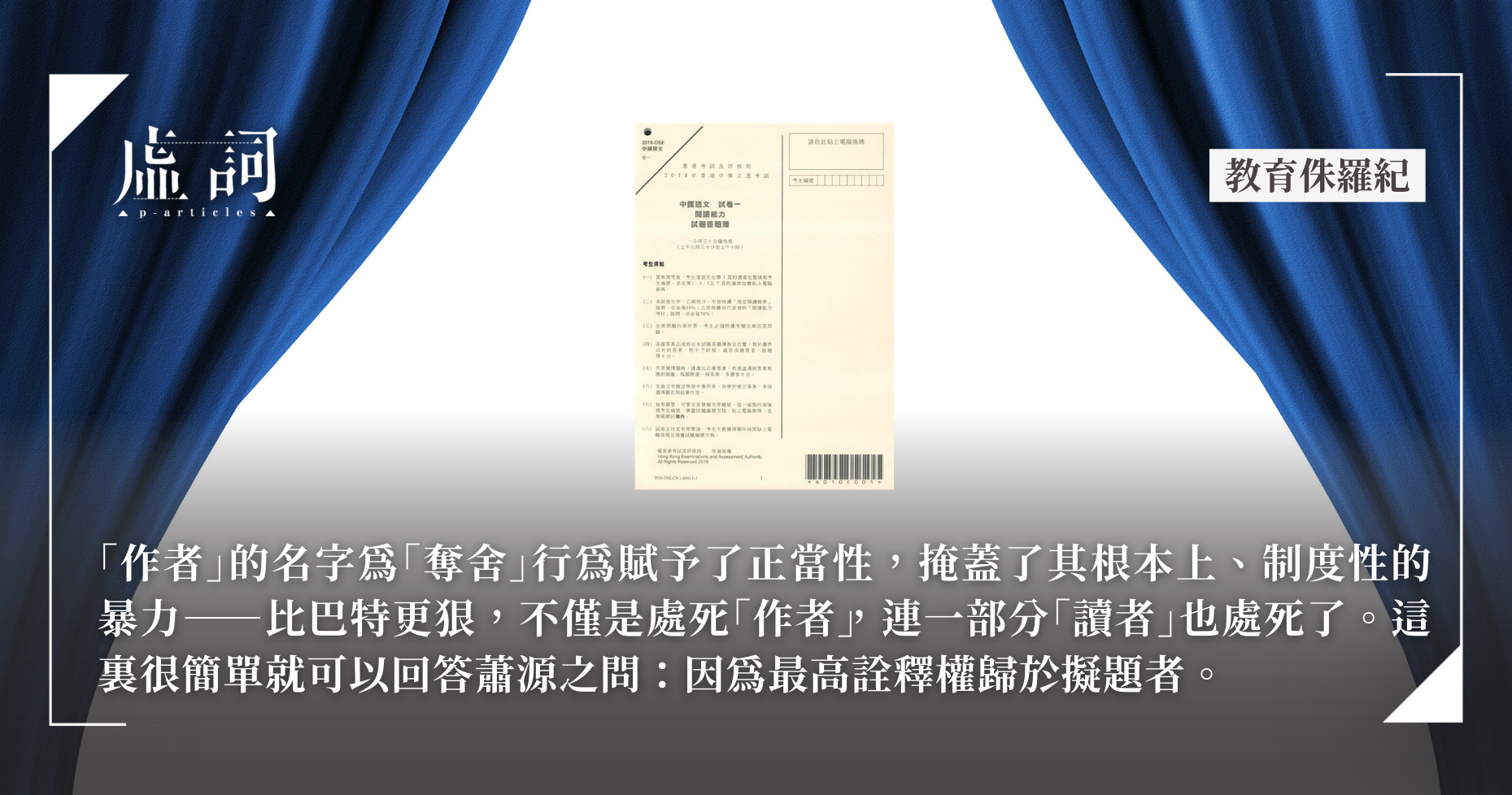「作者」的復活
教育侏羅紀 | by 任弘毅 | 2025-01-07
羅蘭巴特一早在1967年處死了「作者」[1],這是眾所周知的。作為代價,死去的巴特大概也不得安息,後世論及詮釋學時大多還要借他說話(並且也不見得人們把他當作一位「作者」般看待),某程度上,巴特在當代是被復活的一個神話——幾乎成為他本人口中的Author-God [2]。
然而復活的可不止巴特。據說耶穌在死後第三日復活,而我最近重思DSE中文閱讀卷的諸多爭議時,竟從天海的一篇文章,看到了「作者」的復活。按下身份的歷時同一性(diachronic identity)詭辯不談,這裏要說的,並不是那個有名有姓的作者的復活,而是一種奪舍——一種偷梁換柱式的復活,甚至應該說,那真正的Author-God從未死去,只是在考試中借屍還魂。
1. 復活的場景
這是「作者」得以「復活」的根本原因,也是促使我有此體悟的契機。話還要說回2018年DSE,卷一閱讀白話文部份選用的是林黛嫚〈孤獨的理由〉一文。當時作者林黛嫚本人在社交平台回應「出題很靈活,很多題我自己都不知如何答」,引起一陣熱話,甚至激起了延續討論好幾年的「藍色窗簾」之辯[3]。從記者到學者、從老師到學生都對大小論戰饒有興致。作者本人的試答詳載於HK01胡家欣的報導[4],後不少回應指連作者都未能取得完整分數(「答對 / 答到」)。後蕭源撰文,指出「客觀題」和「主觀題」的建議,直言題目本身「出得衰」[5]。對於蕭源此番論述的反駁幾乎沒有,也許是「出題」這種技術性問題太過燒腦,討論不多,而考評局發言人亦一如既往地維持「言之成理即可接受」的官方回答[6]。
類似的爭議在關於2013年DSE黃國彬〈說誓〉、2014年DSE徐國能〈第九味〉的討論[7]中已經略見端倪,現在看來,2018年的事件不過是引爆考生不滿的一個契機。在蕭源撰文批評考評局「出得衰」後,針對此單一事件的討論熱度逐漸降低,但「藍色窗簾」的論爭卻時不時在考試季中復現,不少論者(包括我當年的中文科老師)也搬出了羅蘭巴特這一大殺器,直接以知識層面的差距平息掉爭議——我本亦如此認為。直到近日重讀署名「天海」的一篇文章,才發現我當年漏掉的一個重要細節,倘若沒有這個細節,那麼一切論爭都只是兒戲,但假如將其明言之,便是對教育哲學的一點啟示。
2. 從藍色窗簾到羅蘭巴特
在「藍色窗簾」幾乎成為套語的今日(可見考生之怨氣),仔細解釋一下這個詞語還是有必要的,這關係到許多論者如何應用巴特的理論。「藍色窗簾」一詞,源於一個假想的場景[8]:文章中出現「藍色的窗簾」,國文老師解釋為「透露作者內心巨大的憂鬱」、「喪失朝未來前進的動力」的暗示,而作者說「這(只)是面(他媽的)藍色窗簾」。言下之意,即批評「國文老師」過度解讀、曲解甚至是自行腦補作者的意思。
高國裕解說此一概念的文章發佈於2019年,他亦自言「藍色窗簾」的批評存在已久,按推測,這一說法應遠早於2018年的DSE。面對此等批評,本就頂著「教畜」[9]罵名的一眾「國文老師」們自然不爽,當中有自稱「新手中文系教書仔」的「天海」在〈孤獨的理由〉被廣泛報導的同時發文反擊,標題「藍色窗簾不是保護傘,好嗎?」[10],有種指學生動用「藍色窗簾」這一名目為錯誤解讀作「保護傘」的意味。他說:
「作為中學時同樣厭惡閱讀理解,結果現在每天都在做此事的人,我想說,藍色窗簾才不是你們否定閱讀與解釋文本的理由!」[11]
他如此解釋巴特的「作者已死」論:
「其中有一點特別需要注意,就是法國哲學家及作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的『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這個後結構主義的觀清楚點告訴我們,作者的意圖對我們手上的文本毫無關係,剝奪作者對自己作品的發言權。很暴力嗎?抱歉,『死了』的作者真的不許說話。」[12]
這種論調在當年(指2018後)實際影響力如何,我不得而知。「以羅蘭巴特反駁藍色窗簾」這一思路,也是我當年受教於的一位資深中文科老師介紹的。而今重讀巴特等人的著作,天海這段概述,大致上正確,但並不能完全反駁「藍色窗簾」的說法。邏輯上而言,巴特處死「作者」,意味著解構Author-God的崇拜,詮釋權面向所有讀者而開放(”the birth of the reader must be at the cost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13])。這確實能反駁諸多記者以原作者的評價來否定題目及標準(參考)答案的行為,但這對「藍色窗簾」卻是無效的攻擊。原因在蕭源一文中已一目瞭然:
「雙方既然不是作者,那麼地位是平等的,為甚麼擬題者的看法是對,我作為考生的看法是錯?」[14]
擬題者,包括擬定答案者,與考生同為讀者,在巴特的論述中並沒有任何權重之差,但凡讀者,皆能有凌駕於創作意圖(author’s intention)的詮釋權。要為某一方的詮釋辯護,其「解釋力」(朱宥勳語[15])是關鍵——兩方解釋皆可合理、有效,但若有一方的解釋力勝於另一方,能夠解釋對方所不能解釋的現象,便應取為更優之解。可惜這一點並沒有在天海文中出現。繼續讀下去,天海甚至以「作者已死」的字面含義解構了考卷中的「作者」二字。
3. 復活的作者
天海緊接著說:
「因此,在這一原則下,考卷上所寫的那個作者名字,其實只是一個簡單的符號,極其量只是保障版權,以及表明文章是出於人類手筆罷了。問李白的詩句有何含義,你說怎知李白當時在想甚麼?這在考卷是不成立的質詢,因為這個『李白』並不是那個曾經活在唐朝,終日發酒癲的傻佬。他僅是文本的敘述者而已。」[16]
這就相當之有趣了。「考卷上所寫的那個作者名字」充其量只是「保障版權」、「表明文章出於人類手筆」的符號,與作者本人(person[17])完全無關。那麼這時再動用巴特等人的反意圖主義,豈不是無的放矢?考題中的「作者」僅僅是一張面具,有人藉不在場的作者之聲敘述文本——這難道不是「作者」的奪舍重生嗎?
天海之言指向了一個被掩蓋的事實:假如我們思考是誰藉作者之名敘述文本,而這位奪舍重生的「作者」同時擁有了文本的至高詮釋權,以致於可以否定本應(若按羅蘭巴特)與之平起平坐的眾多「讀者」——那麼結論就很可怕了。這位「復活的作者」,事實上就是擬定題目與答案之人。考卷上所謂「作者」二字,不過是虛幻的符號,擬題者的靈魂早已佔據了「作者」那虛晃的肉身。這也是為什麼「考試」是「作者」能夠復活的唯一場景——除了在「考試」這一場域中被賦權的設卷人以外,沒有任何人能夠如此肯定地替作者代言、斷言。
假如這個推測成立,那麼詮釋問題就不再是「文學之爭」,而是「權力之爭」了。這裏我無意引用任何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論。但只要設想,考卷上「試就『xxxx』一句,說明作者對生與死有何覺悟[18]」一句變成「試就『xxxx』一句,說明本擬題者如何理解作者對於生與死的領悟」——考生定必茅塞頓開,而「藍色窗簾」論不費吹灰之力亦自然會告吹——因為整個詮釋過程中根本不涉及那個真正不在場的作者(person),不論其人,抑或其意圖。
為何不這麼做?不過是欲蓋彌彰而已。「作者」的名字為「奪舍」行為賦予了正當性,掩蓋了其根本上、制度性的暴力——比巴特更狠,不僅是處死「作者」,連一部分「讀者」也處死了。這裏很簡單就可以回答蕭源之問:因為最高詮釋權歸於擬題者。這就是「遊戲規則」[19]。
4. 來自遊戲規則的詰問
這個結論使我自己也不寒而慄。明明是眾所周知、心照不宣的事,將其明言之竟難堪如此。我重思自己的推論是否有什麼紕漏。原作者與設卷機構的矛盾,無法歸因於原作者一家獨大的話語權(巴特之論已駁),而歸因於設卷機構的過度詮釋,則面臨符號「作者」對於文本的預設界定(天海之論)。假如天海「符號『作者』」一說為偽,文本依舊代表著原作者的意志,那麼眾多考生落第的原因,就只能是其「解釋力不足」了。
——因為某人(即使不是設卷機構)提出的解釋優勝於絕大部份人,能夠解釋大部分人所忽略的文本現象、能夠捕捉大部分人的論述漏洞,因此我們取其為標準答案,並將不符合此答案的,統統降分。這與考評局發言人「言之成理」的精神豈不是背道而馳?仔細觀之,原來是「言之成理,即可接受」。「接受」而已,一題中只要不打零分也算是「接受」,扣分只因論述未完備,「解釋力」不足。考生的回答並沒有因此而被「拒納」。
這正是坊間眾口中的「遊戲規則」精髓所在。既然知此,考生同學又復何怨呢?只要取得合格分數就行,畢竟是「接受」了。只是,在這遊戲規則之下,考驗的真的是學生的「中國語文能力」嗎?語文能力和文學造詣優秀如原作者的學生,或許只能取得等級4,而無條件服從「遊戲規則」的學生,反而能取得等級5或以上。制度是方便了評核機構,但這有使我們距離教育的本質更近嗎?
是結語也是祝福語
反過來問,一眾教師仍願意接受此「遊戲規則」,並視之為課程的一部分內容嗎?我們應該明言這種暴力,還是應該掩蓋這殘酷的現實,以免傷害到他們?
坦白說,我不知道。我沒有那樣放出豪言、讓四海之內皆遵從某一法則的信心。但我選擇相信我的學生。我相信他們不會終生陷在「自己是否真的如此無能」的疑問裡,我相信他們不會因為未能升讀大學而自殺,我堅信在龐然的權力體制下,存在逃逸的路線。
註釋
[1] 有指〈作者之死〉一文最早刊登於美國雜誌Aspen 1967年第5+6期;從網絡封存頁可見,該文由Richard Howard翻譯。亦有指其文最早出現於1968年法國雜誌Manteia第5期。目前流通的Stephen Heath英譯本採用後者為原文。詳細爭議見John Logie, 1967: The Birth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College English 75(5), May 2013.
[2] 見Stephen Heath英譯本:Roland Barthes: Image-Music-Text, Essay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Stephen Heath. (Glasgow: Williams Collins sons & Co. Ltd., 1977), p.142-148.
[3] 高國裕:〈國文考試的藍色窗簾〉,Medium,2019年1月27日。網址:https://medium.com/greg的學習筆記/國文考試的藍色窗簾-與原作者心心相印還是與出題者心心相印-2997e8b9d4c9。
[4] 胡家欣報導:〈【DSE】《孤獨的理由》作者親剖拿低分原因:考試分對錯惟文學無〉,《香港01》,2018年4月10日。網址: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76687/dse-孤獨的理由-作者親剖拿低分原因-考試分對錯惟文學無,最後更新於2018年4月13日。
[5] 蕭源撰:〈【熱評】DSE考材《孤獨的理由》 作者林黛嫚答題也得低分的真相〉,《香港01》,2018年4月12日。網址: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176948/熱評-dse考材-孤獨的理由-作者林黛嫚答題也得低分的真相,最後更新於2019年1月4日。
[6] 同註4,見胡家欣報導。
[7] Alvin:〈DSE中文科考核文章台灣原作者:「分數會過去,讓文學留下來吧!」〉,《關鍵評論》,2018年4月11日。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3430。
[8] 同前註3,續見高國裕文。
[9] 羊格著有小說《教畜》一書(香港:有種文化,2015年),詳細形容可參考之。
[10] 天海:〈藍色窗簾不是保護傘,好嗎?〉,Medium,2018年4月11日。網址:https://kenlingcw.medium.com/藍色窗簾不是保護傘-好嗎-308fc27fc91b。
[11] 同上。
[12] 同上。
[13] 見Stephen Heath英譯本,頁148。
[14] 同前註5,蕭源:〈【熱評】DSE考材《孤獨的理由》 作者林黛嫚答題也得低分的真相〉。
[15] 朱宥勳:〈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藍色窗簾——詮釋與過度詮釋的分寸〉,《文訊》2015年4月號。見朱宥勳個人網頁:https://chuckchu.com.tw/article/131。
[16] 同前註10,見天海〈藍色窗簾不是保護傘,好嗎?〉。
[17] 可參Stephen Heath英譯本,與Richard Howard的翻譯一致。
[18] 摘錄自2023年DSE卷一,原卷可下載於DSE Life網站:https://dse.life/static/pp/chi/dse/2023/p1.pdf。
[19] 蕭源語。見前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