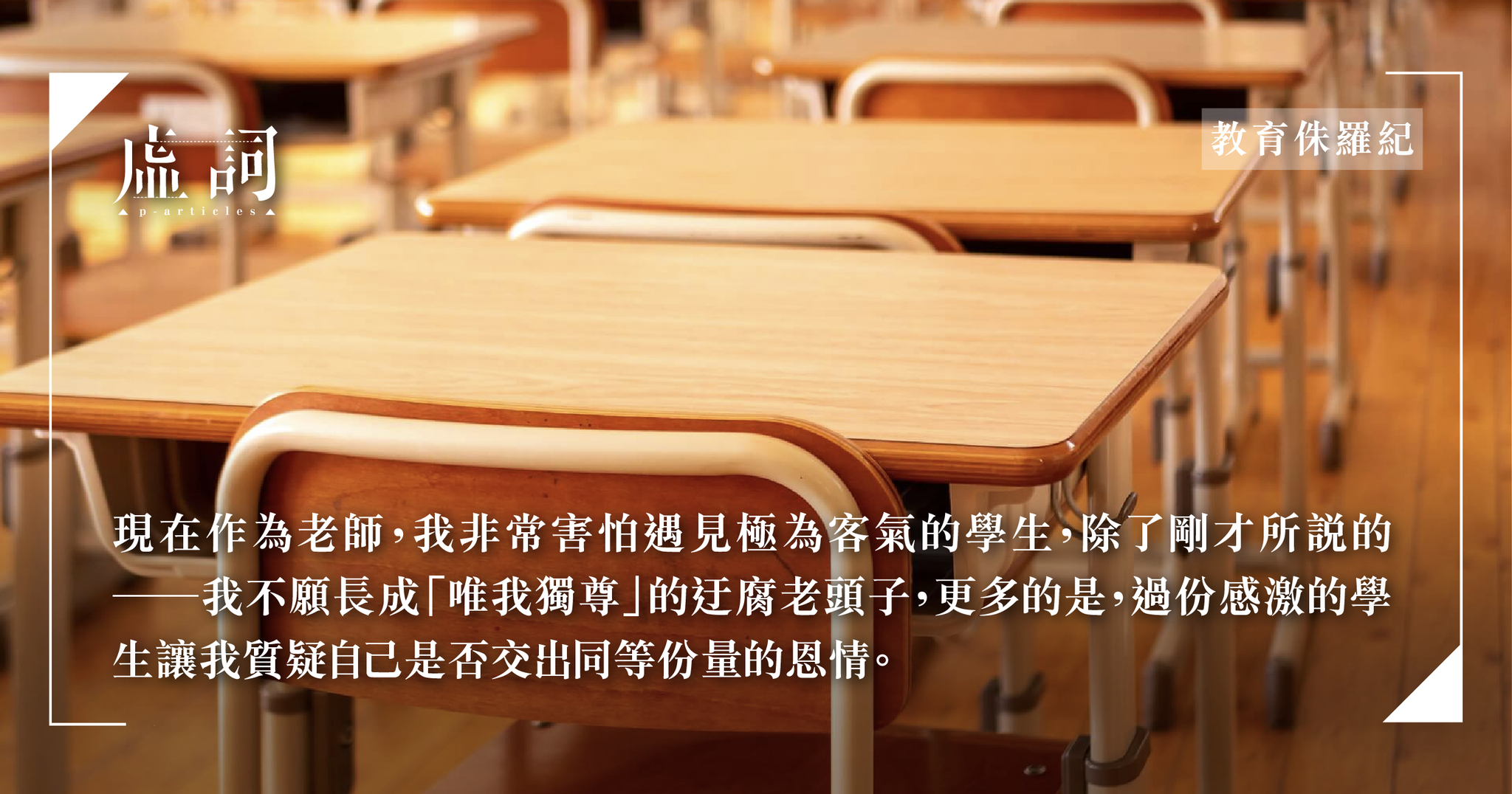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水槽生物學
《咒術迴戰》前期故事中,引介了一名輟學的中學生吉野順平,這角色及後會長成某關卡的大魔頭,主角打倒了他,才會反思、蛻變,擺脫典型平面的熱血少年。在順平成形、游走善惡矛盾之間,班主任突然出現他家門口,以其職權請他回校上課,重新做人。言談間,學生發現班主任不僅對校園欺凌視若無睹,甚至以為那些只是小孩子的玩笑,而不上學就是孩子鬧情緒而已——誠心道歉,學校是會原諒的。學生頓時覺悟,急速成長,對著矮胖老師大聲呵責:「教師只不過是從學校畢業,又回到學校工作一輩子,在社會根本毫無經驗的大孩子。」
反派在任何形式創作裡,都起了極為重要的推進元素。這尋常中學生任由邪惡咒力吞噬,縱然手段激進,卻讓他人動容和理解。動畫版片頭曲裡,作者刻意誤導觀眾:順平終究會與主角群在大樹下聊天野餐,人性本善如我,不免期待他會在某集反轉,改邪歸正,和鍾愛的角色並肩作戰,不如現實般無奈。反正他逆轉的契機甚多,諸如其母對逃學給予極大寬容:「學校不過是個小小的水槽,還有大海和別的水槽呢。」對了,我們何必為著一個淤塞的水槽,一頭栽進去尋找出路呢?
所以我很怕,很怕成為只活於單一水槽,卻自以為是的老師——這個行業太輕易把一個人捧起,投進「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口號前,特別是教室的數十分鐘,我們完全擁有那數十對雙眼,從敬禮開始,學生便注定要比老師卑微數十倍,聽著老師吹噓,稍一分神,還要聽數十句責罵、給懲罰數十遍。那片宇宙只屬於一個人,老師停下來、喝水,學生眼眸都必須注視,哪怕課堂結束後,這名佝僂、言不及義、領口破損的庸人,潛進地鐵車廂內不過是一名孕婦站在跟前便立即假寐的上班族,學生也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細心聆聽他此刻講得頭頭是道的仁義禮智。
三島由己夫曾提倡「應打從心底瞧不起老師」,他的理據是「身為學生,非超越學校裡的老師不可。老師並不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全才。而且最麻煩的是,老師已經離自己的青春期很遙遠,早把當年的苦澀煩惱忘了大半,若要他重拾彼時的心境,實在很困難。」為方便一眾似懂非懂的同業者,我簡單翻譯如下:一、社會、文明須進步,學生就要抱著超越老師的決心,青出於藍,不可妄自菲薄。二、教師只是販賣知識的人,而且是販賣只得自己擅長卻偏門的知識,誠如《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所言,學生十年後連log是什麼都不知道,「還可以活得好好的」。三、老師不會理解學生——即使我們曾經是學生——少年人的煩惱我們已然失去,而我們卻用上成年人的批判,去扭曲他們的內儉和掙扎。
大學第一年,我們這屆新生無故被指責不懂禮貌,沒有向前輩或老師表達敬意,更有趣的是其中一位較內向的同學的FACEBOOK 頁面,被其「組姨」貼上一篇《禮記》,大義滅親,以示死諫。如斯耐人尋味的指控,源於在學不足兩個月的我們,根本無法認識所有同系師生,打招呼的手伸了出來,又好像不是,卡在羞怯中陸沉。當然我們沒有深究對方明明認得我們,卻又為何靜待我們犯錯才責難……我們早已沉淪於鬱悶與百口莫辯之中,沒有力氣探討惡意。於是某次我在新校遇到常常丟難我們、自詡「訓導主任」的教授,立即自馬路一方大呼其尊稱,用力揮手,綠燈甫亮即跑過去,躬身探問對方到哪個課室,課本教具(即USB手指)需要我代勞嗎?接著又不住提問:學術的、非學術的、學校制度、選科策略,甚至學費資助,一盡問題學生之道。沿金城道球場,經體育中心,進入舊校校園,走上扶手電梯,我都緊跟老師,寸步不離,反之老師腳步越走越快,違禮地在電梯行走,或許上課時間將至,好老師便忍不住關心,著我若有課可先拋棄老師,下次再談。萬萬不可!我回答說雖然有課,但遇到老師便打算「SIT堂」,好好學習,對方指現在上的是高年級必修課,將來我也會讀到,如此關愛我的學術生涯,我只好堅持護送老師到課室,為對方打開大門,目送對方走上講堂方安心離去。呼!世途險惡,現在甚麼都能吃人了。
「老師這個族群,是你們這輩子會遇見的大人當中,最容易應付的對手。在往後的人生中,你們要遇到的其他成年人,通通都比最惡質的教師還要難纏好幾萬倍。」三島續說。這樣的說辭,又正如呼應他另一想法:「應當要忘恩」。現在作為老師,我非常害怕遇見極為客氣的學生,除了剛才所說的——我不願長成「唯我獨尊」的迂腐老頭子,更多的是,過份感激的學生讓我質疑自己是否交出同等份量的恩情。在仇師普世價值裡,我們都是朝八晚五的上班族,差點連我都以為自己是教具,像USB手指,隨意安置不同空間,下課鐘聲響起便可「安全地移除軀體」,人海中消失。過去兩年,我經常以「作家」身份到訪大學、中學演講,平常完成了日常課擔,便到他校分享,他校師生每每客氣有禮,為我張羅一切,佈置展板,放好著作,介紹我出場時附有一大段「作者生平」和「文學地位」,掌聲如雷,講座後更安排簽名會,請我與來賓簽名拍照。然而熱鬧過後,回到熟悉的工作環境,我便要擔起最卑劣的追收工作、學生遲遲不肯回到課室、在我講到精彩之處肆意打呵欠、悉心準備的堂課呢?當然不會按時完成、提醒了數千遍仍重複犯錯。我曾帶同文學科學生到他校交流,據知我登上講台後,一名學生聽到後方有人說「嘩好靚仔呀」後,還在台上搜索討論對象。真氣人。
落差太大,我納悶如蝙蝠俠,不適應分裂身份,逐漸模糊了界線,斷定自己理應接受更大的尊重和答謝。直到我讀到「應當要忘恩」,思索自己不過是知識小販之餘,還感受到對方每天道謝帶來的無形壓力。三島認為如果在千鈞一髮之際救了你命的人,恰巧住在你家對面,長期需要感恩和口頭道謝之情況下,你只會萌生厭惡、逃避,更甚的是會上演恩將仇報的戲碼。自那天起,我在眾多笑臉下感覺得到刀鋒冰冷,抗拒學生敬禮,尤其是學習生涯殘留的記憶裡,我沒有一次是真誠向姍姍來遲的老師說早安,又或是對言之無物的課堂管理員道多謝教導。我甚至抗拒出席謝師宴,自我得到應有薪水以後,仍苛求學生動用暑期工的薪水宴請我吃自助餐。
約十年前聽網上直播,達哥富有哲思地討論,時下歌手常說「這首歌送給你們」此說當否,有趣的是台下真金白銀購買門票的歌迷總會起哄,激動地拍掌享受。達哥說這句話應修正為「這首歌是你們應得的」,這才叫名正言順。同樣想法下,我已得到自己應得的報酬,突然收到別人多加付出的道謝,天秤座的我便寧可他們「忘恩負義」,不必多送。反正我是販賣冷門知識,又不能完全理解對方的上班族而已,幾年過去,GPT、AI或可取代我這毫無經驗的大孩子,完成「傳道」、「授業」、「解惑」的普世既定職能。
自嘈雜教員室下筆至此,我終於狠下決心,稍後觀課依從一貫作風,不用突兀地邀請學生向副校長和觀課老師敬禮,那份多出來的感恩,大可省下來泅泳大海,掙扎求存。至於那些我沒有收回應得禮貌的學生,我亦不會多言,猶如多年前某年輕女星被前輩指責無禮時,歌神的簡單回應:「如果真有其事,我不會當面責難她,但會記在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