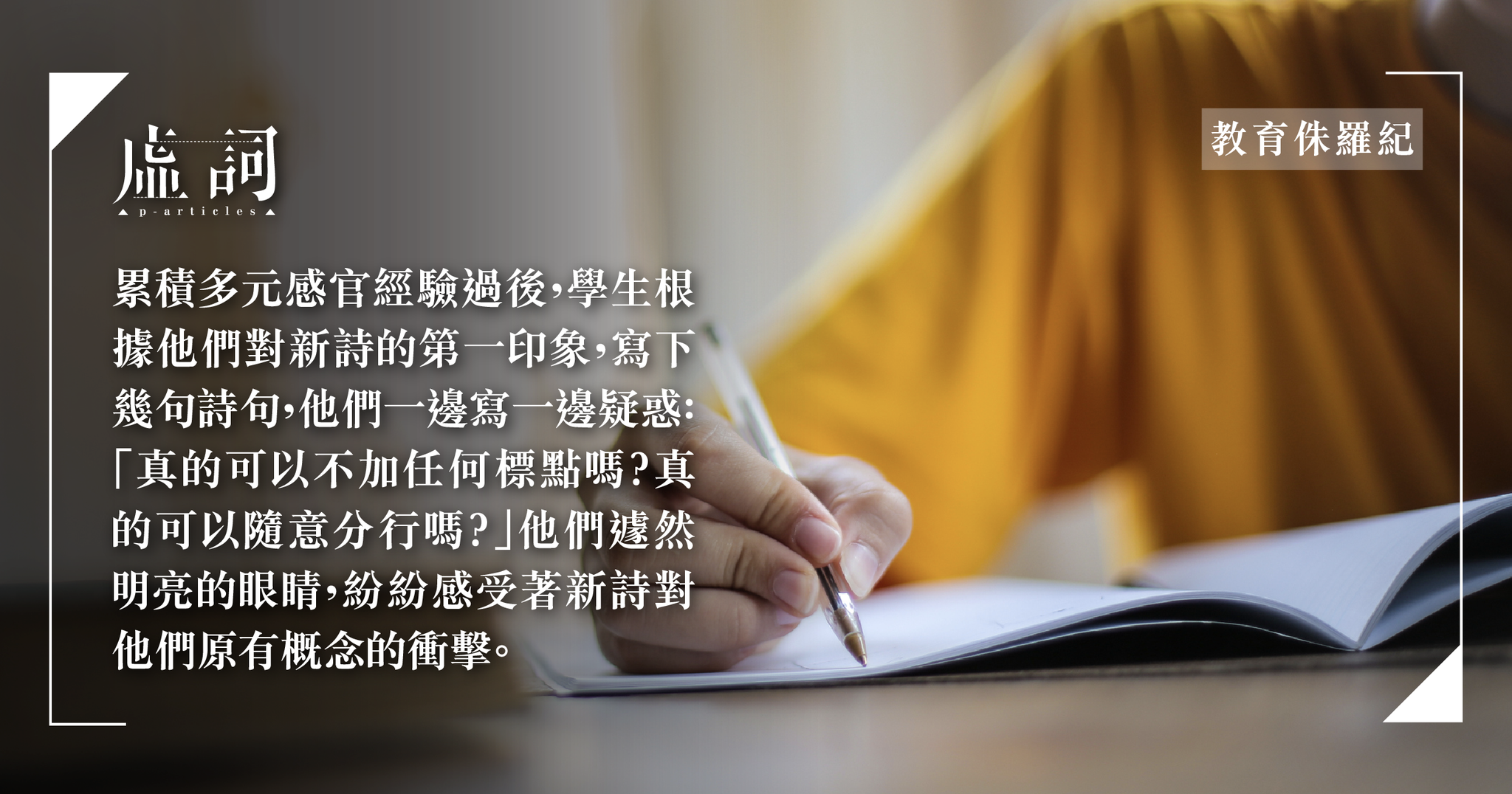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暖在心間
「當他軟柔的手握著我的小手,我彷彿感到一股暖流……」這是幾位寫作班學生對「溫暖」當下的聯想。
今年,在葵青區的中學指導幾位中三學生創作新詩,對我和學生而言,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來,我較少面授新詩創作或分享我的創作經驗;二來,學生也甚少機會接觸新詩。當我問及學生對新詩的第一印象時,他們答:「靜夜思」,這是意料中事。
第一課,我帶了幾本設計特別的詩集讓學生隨手翻翻,感受詩集的質感。他們對夏宇《脊椎之軸》深感興趣,一邊傳閱,一邊提出一連串的提問:「這是要給盲人看的嗎?出版社是不是沒有錢印書了?為甚麼有些書頁又用墨水印刷呢?」我心裡暗自高興,因為往往誘出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慾是成功的第一步,只有這樣,往後的教學才能事半功倍。接著,我與學生分享我即將出版(現已出版)的詩集——《行走的姿態》(The posture of walking)的幾個設計方案,學生參照上一環節的經驗,迅速指出不同設計的特點:模糊的主體、像雨一樣的斜線、亂畫的曲線等等,展現了他們敏銳的觀察力。
接著,我鼓勵學生從詩作感受生活的「詩意」並從中擷取意象。於是,我建議學生放鬆他們的身心靈、放下他們的情緒、「打開」他們的所有感官,播放了詩人池荒懸所讀的〈中午在鰂魚涌〉(而大多學生對「鰂魚涌」缺乏認識)。於是,某些學生閉目,透過池荒懸溫柔的聲線,代入情境,跟隨梁秉鈞的一字一句遊覽昔日的鰂魚涌。
「煙草、鹹水草、花、汽車、海、鐵錨、船、風暴、浪、軌道、剪刀、路、傘、紙屑、鐵枝、雲、石……」噠噠的粉筆上在黑板留下人造的意象。聽畢全詩,我嘗試尋找我寫下的與學生腦海裡意象的共通點。〈中午在鰂魚涌〉對我有重要的意義,在中文系畢業晚會,教授把這首詩送給全體應屆畢業生,為這首詩賦予另一層含意。畢業後,我把全首詩印下來,釘在我座位旁的軟木板,以此自勵,而令我印象深刻且引起共鳴的是以下幾句:
//有時工作使我疲倦
有時那只是情緒//
//有時我走到山邊看石
學習像石一般堅硬
生活是連綿的敲鑿
太多阻擋 太多粉碎
而我總是一塊不稱職的石
有時想軟化
有時奢想飛翔//
但他們感興趣的部分反而是:
//在籃球場
有人躍起投一個球//
或許,年輕的他們對生活還沒有太多顧慮,玩樂於他們而言才是正經且重要的事。以後他們也會感念自己在學生時期,「享受過」在球場上與兄弟們投籃的日子。俱往矣,身為師長,大概只能留下無盡的羨慕。自然,這就是孩子與成人生活經驗的不同,導致我們在欣賞詩作之時,產生了不一樣的感悟。
累積多元感官經驗過後,學生根據他們對新詩的第一印象,寫下幾句詩句,他們一邊寫一邊疑惑:「真的可以不加任何標點嗎?真的可以隨意分行嗎?」他們遽然明亮的眼睛,紛紛感受著新詩對他們原有概念的衝擊。我認為這些詩作正是我們(至少像我這樣習詩五、六年的創作者)所追求(或「回不去」的)新詩的「原初狀態」——稚嫩但純真。
在前往中大進修的夜車裡,我一字一句的細味學生們人生裡的第一首詩,在晃盪的高速列車裡傻傻地笑著,彷彿有一股暖流流進心間。
2023.03.29
〈燒〉——贈寫作班學生/驚雷
點燃一根木條,火焰明明滅滅——
氧氣救活了一座火堆
在鐵屋子裡悶燒
廢棄的字紙被重新拾起
被燜煮的文字思考
如何續寫一份不存在的悔過書
試著兌水注進滾燙的情感——
高溫會自行濾出久經歷練的湯汁
剩餘的濃煙熏不醒半個裝睡的人
把虛幻的自畫像通通隱去,鑄成字粒
回憶都被鎖在方格裡
填塞火縫
〈熱朱〉/佚名
我回到家中,浮想
桌上有一杯熱朱
我拿起熱朱,走到露台
直面凜風的怒憤
凝望黃昏的太陽
想起那厚重的被窩
在溫暖的家
我喝著熱朱,細味它的香甜
躺進柔軟的被窩
〈別離〉/甘都
在建築中,兩人佇立著——
心裡已想著在
某個轉角處
與她相遇
潔白的珍珠橫空飛著——
化為一個個紅點,卻
只有一顆走出
〈暖〉/甘都
冬日的陽光灑在地上
寒風似乎就此消逝——
忽而,友人遞來一杯熱可可
唇舌觸及——
撲面的香氣和暖意
多麼幸福、多麼舒暢
〈被窩〉/銀鎮
冬天晚上,我寂寂
步出浴室
寒流向我伸出利刀——
躲進被窩吧
把我捲進無盡的暖流
天花板一度劇烈,搖晃
而我緩緩入睡
〈竹蜻蜓〉/佚名
颱風怒衝衝地闖來
在家中我們打開電視機
看多啦A夢
想像戴上竹蜻蜓
飛到窗外去
教訓到處作惡的風暴
又想像在空中飛來飛去
像小鳥一樣
自由自在
〈跳飛機〉/力糕
有人在公園
跳啊跳啊跳——
單腳跳雙腳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到達終點以後
我們再來一遍